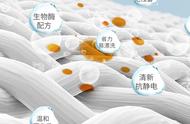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丝绵袄是江南过冬富有特色的御寒衣服,与棉袄相比,手感柔软,透气性好,尤以轻薄、保暖性强而使得穿着舒适。
但与北宋诗人张俞《蚕妇》所言“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样,饲蚕的江南人舍不得自己享用好的茧子,而是把它们卖给茧站,换取一些经济收益,只留一些双宫茧用于剥丝绵。
一件绵袄需丝绵半斤左右,往往要积累多期蚕才能制成。一件丝绵袄价值不菲,但养蚕人家生有女儿的,都会提早准备一件,作为出嫁时的新娘用衣。在我的家乡,姑娘在父母口中都被亲昵地称为“小绵袄”。
小学毕业那年,母亲为我翻过一件丝绵袄,外壳用的不是布料,而是一件绛紫色的双层棉毛衫。我很奇怪母亲为何会经常选偏女性化颜色的衣服给我穿——我的很多新年衣服也都是绛紫色的。
母亲说,怕我长不大,所以当女孩养,小时候还给我的左耳穿过耳洞。这种双层棉毛衫是专门为做丝绵袄而想出来的发明创造,制作起来比对襟棉布外壳方便许多,且轻便保暖,可以免去大冬天穿厚衣服的累赘。喜欢时髦的人还可以把它穿在衬衫里面,外加西装革履,看不出来。
这种丝绵袄,我从小学毕业开始,一直穿到大学毕业,穿到工作多年,只不过因个子的长高而换了棉毛衫外壳的大小。
上高中前,母亲终于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外壳衣,从此我的衣着彻底告别了女性化的色彩。
后来我就没长什么个头,这件蓝色的丝绵袄一直陪伴我到大学。同寝室的人没有一个来自杭嘉湖平原的,他们对我的这件丝绵袄投来羡慕的目光,这让我意识到它可能和嘉兴粽子一样,是我家乡的特产。
大学第一年寒假结束回校,我给两个同学各代买了一件丝绵袄,把它们和几袋“五芳斋”粽子一起带上火车。
那年的春运挤得有点夸张,过道上全是人,连厕所里也被人占了空间。等到我终于摆脱火车回到学校,在寝室里打开旅行包时,发现粽子都被挤成了饼,而丝绵袄在空气里又恢复了原样。
那年暑假,我在学校里勤工俭学没有回家,母亲嘱咐我要把丝绵袄拆了——丝绵曝晒,外面的棉毛衫套清洗后晾干收起来。等到下半年秋风又一次扫落树叶时,母亲又打电话来让我自己动手把丝绵袄翻起来。
这可难倒我了,我去找管楼阿姨帮忙。她从未见过这种丝绵袄,但她有作为母亲的经验,摸索一阵后竟然帮我翻成功了。她用针线一边帮我缝纳,一边啧啧称赞,这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点来自“丝绸之府”的骄傲。
本文来自【嘉兴日报-嘉兴在线】,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