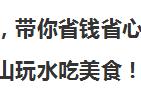在浩瀚的戈壁高原,没有什么树木比红柳更普通、更常见了。它没有江南垂柳那样的风姿绰约,也比不上鄂州陶公柳那样声名远播,更没有西子湖畔“六桥烟柳”那样的美丽传说,它那鳞状的小叶子,也无法用来形容女子的秀眉。然而,就是这有着紫红色枝*红柳,将根深深地扎进干旱的荒漠戈壁,任凭狂风肆虐、飞沙走石,它依然枝叶婆娑,随风而舞。
刚到青海时,同宿舍的一名老兵说,在高原,躺着睡觉就是奉献。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连吸氧都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时,我和一起分来的同学不禁困惑:难道军校四年的苦读,就是为了来高原睡大觉?难道青春的迷彩,只能在高原渐渐地黯淡?
有一天,我们出公差来到某装检团工区九号哨所,在这个“抬头一线天,百里无人烟”的地方,看到了一种似柳非柳的灌木,淡红色的小花开得正火。哨所的战友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柳。它不怕严寒不畏风蚀不惧沙害,在风雪弥漫的生命禁区,它最先报告春天的消息,是哨所官兵无言而忠实的伙伴。凝视着在风中起伏的柳浪,不知道是不是高原的严寒风沙磨砺了红柳的坚韧,但我们知道,是高原的罡风吹黑了战士们的皮肤,是强烈的阳光给战士们的脸颊涂上了两坨“高原红”。年轻的小伙子谁不爱美?谁愿意远离繁华走进孤寂?那一刻我们都明白,高原军旅该如何去走。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这支驻守在祖国西北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走过了48年的发展历程。48年,对一个人来说,已经进入不惑,但对这支部队来说,却依然年轻。
怀着朝圣般的景仰,我们走进部队军史馆。一张张发黄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仿佛带我们穿越了时光隧道,重温那难忘的峥嵘岁月。艰苦的创业初期,那是怎样的情形啊:吃的是萝卜、土豆、白菜“老三样”,喝的是河沟水、雪化水,穿的是土布工装,补丁摞补丁,住的是干打垒、地窝子、茅草屋。就像王昌龄在《塞下曲》里描述的那样——“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然而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前辈们却始终无怨无悔,从不言苦叫屈,硬是在大漠深处打造出一支坚强的雄师劲旅。
“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氧气少,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更要苦干不苦熬。”简单的话语虽直白,可我们知道它的重量,它早已融入了高原火箭兵的血脉。姚念学、贺先觉、屈明富、顾勤俊、高国骞、黎昌和、盛德华……每一个名字后面都可以写出一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又像红柳一样普通平凡,他们将对祖国的忠诚深深地植根于高原,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巍巍昆仑茫茫雪山作证,一枚枚划破长空的神剑作证,天安门前滚滚驶过的导弹方阵作证,玉树地震的废墟作证——在古老荒凉的高原上,年轻的火箭兵们创造了怎样壮烈华彩的军旅人生!
也许,矮矮的红柳很难让人生出“春思春愁一万枝,远村遥岸寄相思”(唐·唐彦谦《柳》)的诗意,它紧绷绷的树皮也无法做成柳笛吹出动听的旋律,但它不仅是抵御风沙侵袭的屏障,它的嫩枝和绿叶还是治疗高原人风湿病的良药,藏族老百姓称它为“观音柳”“菩萨树”。上高原,下高原的艰辛轮回,难道仅仅是企求留下些许聊以自慰的美好回忆?不,我和我曾经的同学现在的战友都愿如红柳一样站立成树,摇曳出满树葱绿的叶,绽放出蓬勃火红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