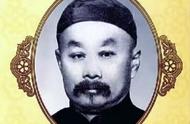作者与叶盛长第一次见面纪念。
他晚年的工作,可以分成这样的三个部分。第一是为京剧大声疾呼。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只要政协开会,他必定到会,必定发言,一发言就停不下来,发言的唯一主题就是吁请政府对京剧加以抢救,保护这一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有次政协全会,他因过于激动乃至当场昏厥,还是舒乙等年轻委员把他抬上担架,推上救护车。哪知他在救护车上苏醒,坚决不肯就医,硬要回到会场把话说完。众人拗不过他,只好用担架把他推回到会场,他在担架上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他的名言“谁爱京剧,我就爱谁”,直喊得自己老泪纵横。政协之外,他与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筠、市政协党组副*兼秘书长李天绶等同志组织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通过多方渠道为京剧呐喊。
盛长先生的第二项工作是传承京剧艺术。他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拉来学生就为其说戏,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分文不取。他说:“老师教学生演戏,如果学生演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那就说明老师没有教到家;如果学生演得不如自己,那是做老师的犯罪;如果学生演得比自己还好,那是做老师的最大幸福。我从事京剧艺术五十余年,如今年老有病,不便登台,但是,我能坐在台下看到亲手教的学生比自己演得还要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欣慰。我的精力没有白费。”
我在与他相识的时候,对于京剧的认知,只限于人人都知道的那些常识。他却看到我的年轻,很快就开始给我说戏,第一出戏是《二进宫》,一板一眼,旦角、生角、净角,三大行当齐头并进,记得他教我净角的“怀抱铜锤”,那个铜锤在不同场次有不同的抱法,如何能融入到戏剧之中,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他无数次为我示范,我总也学不会,他也不恼,非要教会我不可。有时我们一同外出,走在街上,他说着说着就示范起来,我也要跟着他做,惹得路旁行人侧目,以为我们这一老一少精神不正常。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学习京剧,坐科是在“马路富连成”——那也是富连成科班最后的一科了吧。说到后来,叶盛长先生终于醒悟了,说我真不是唱戏的材料,他嘿嘿地笑着说“咱俩都上不了台”,这才彻底放弃了为我说戏。时至今日,我可以做一些关于京剧的研究工作,我的基础却是他为我打下的,尤其是他以他丰富的舞台经验为我开蒙,从而使我的研究不是书上来书上去,而是能够与舞台实践紧密结合,这就不能不感念老先生的盛德。说句更为实在的话,我之所以能以京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项专业,尽皆是拜老先生之所赐。
盛长先生的第三项工作,是四处奔走,传播京剧。那时的北京,旧时的“票房”有所恢复,出现了一批京剧的业余活动场所,如北新桥草园京剧剧场、朝阳文化馆、西城文化馆、前门老舍茶馆、三里屯穆斯林餐厅、什刹海汇通同人票社,等等。昔人曾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叶盛长先生则是凡有胡琴处必有他的身影,他要我陪同他一处一处地走访票房——有时就是街头公园,他为联络京剧观众,培养京剧爱好者,不计时间,不辞劳苦。通常的情况是,我先到和平里他家,他多是已经穿好中山装皮鞋坐在沙发上等我。我们一起出门,乘坐公共汽车,有时还要换乘两次,到达目的地后,我替他通名报姓,叶五爷来也,他便去为人说戏,我就可以闪到一旁找人抽烟聊天;到了大家都要散去时,我再搀扶他乘公共汽车回家。也正是因为有频繁的这样的活动,我往往被众人误认为是他的孙辈,连溥杰先生、李洪春先生、程玉菁先生等老前辈都是如此看待我。有一部根据陈建功小说改编的电影《找乐》(宁瀛导演),就是我们彼时生活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向陈建功确认过,但我固执地以为,剧中那位认真辅导业余票友唱戏的京剧老艺术家“杨先生”,其原型就是叶盛长先生,因为很多情节都是我亲历的。这部电影,每当我怀念起盛长先生,还有电影的两位主演黄宗洛、韩善续先生,我都要看一看,至今已经放坏了两张碟片。
关于叶盛长先生,我的怀念,是说也说不完的,不能再如此说下去了。今逢先生百年诞辰,我作有小诗纪念老人,诗云:我是新花正旺开,新花俱是旧人栽。绝怜无有斑衣处,千载风流隔世哀。
诗有未能尽意处,盛长先生哲嗣、著名的京剧文武老生艺术家叶金援先生来与我商量,说他也已年过七旬,我也是五十朝上年纪,总要在这一特殊的年份里说一些关于老先生的话。我就想了这样的几句话:
伟大的中国京剧艺术,是红如谭鑫培梅兰芳、不红如叶盛长等代代艺术家付出毕生心血创造的,是生命的连接,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歌。
叶盛长先生没有站立在舞台中央,但是他的事例足以证明,我们的京剧舞台,要求舞台上所有角色都要无比优秀,都要闪闪发光,光芒四射。
叶盛长先生命运多舛,自强不息,将自己的生命最大程度与京剧的生命相融合,悲欢同在,荣辱与共,一生相托,不离不弃。更扩大范围说,此即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正是因为切身感受到这种苦痛,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着无数如叶盛长先生一般,但存一息,亦必将其付诸我们的文化,鼓舞后来,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本性的文化精神。有此种文化精神存在,中国文化终将生生不息,长远光大。
即以此为哀祭,安盛长先生于幽冥。(作者:靳飞 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