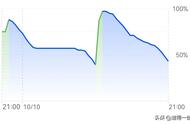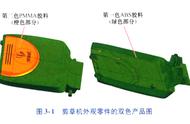序

外面突然嘈杂起来时,静言正陪着徐老太太说话。凌乱的脚步声仿佛踏在静言的心口,她突然就心律不齐了,感觉心脏的部位有个兔子急于冲破阻力要蹦出来。
静言刚从红酸枝太师椅上站起来,丫鬟浣衣就闯了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她急促的叫声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看了一眼静言放低声音说,"新太太从书房的楼梯上摔下来了!"
静言一惊,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住心口,仿佛要把衣服里藏着的快要蹦出来的心脏按住,一只脚急急地往外走,那双紫缎装饰着喜鹊的绣花鞋里藏着的小脚并不听她指挥,颤巍巍半天才来到书房。
静言看到下人们正七手八脚地在曼丽身边忙乎。曼丽俊俏的脸庞此刻扭曲到变形,汗珠混杂着泪水把瀑布般的长发粘在一起,纠缠在脸上,一袭青蓝色的改良过的旗袍上有一滩清晰的血迹。
静言一时惶急,不知怎么处理眼前的事情,突然二楼传来哭声。顺着楼梯看去,一个小女孩站在楼梯最上面,手里攥着几条裹脚布闭着眼睛大哭……

(一)
这是静言嫁到溪镇徐家的第九个年头了。她感觉今年溪镇的秋天格外地长。江南的秋天就是这样缓缓地拖沓着,久久不愿离开。草木的叶子不像夏天那样顶着太阳,活泼泼地生长着,但也不凋零,就那么懒洋洋地挂着,无精打采的。
桂花凋零得彻底,连同香气也带走了,几棵桂树各自站在自己的地方,耷拉着叶片,仿佛连相望都懒得了。徐家大院的几棵梧桐树树皮斑斑驳驳,叶子倒是相连着,静言站在这两棵大树间总会想起刘兰芝这个女子,这里有一棵是她吗?
对于刘兰芝,静言是羡慕的,毕竟她爱过,静言觉得为爱而死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她摸着一棵梧桐树上的疤痕有时候会想,这棵就是焦仲卿吧?这个伤疤是他"自挂东南枝"时留下的吗?如果轰轰烈烈爱过了就算死去,也无怨无悔吧?
可是她嫁人九年却不知道爱情的样子。他的丈夫,原名叫徐家麒,现在叫徐慕素的男人,在她嫁过来的第十天离开了这个家,之后只在四年前他的父亲病重和去世的时候,在溪镇呆过一段时间,即使她生蓝月时,他也没有回来看一眼。中间只是零零星星地来信中提到她,让她再嫁人。
徐老太太每次读到这样的信总会生气,捻着手里的檀香木嵌寿字的佛珠念叨很久。有时候会拉着静言的手说:"他不认你这个妻子,我认你做女儿。"静言就这样尴尬地在徐家一住九年。

(二)
徐家是江南溪镇的望族,诗书传家,清朝时祖上多人考取功名。乾隆年间,在京为官的徐守业为留在江南的家人和仆人沿着南溪盖了几十间房子,当地人称"百间楼",房屋雕梁画栋,沿河而筑,出门小桥流水,四周绿树掩映,曾经辉煌一时。后几经分家,静言嫁过来时,徐家还有十几间房屋和一个大大的院落。
当年的徐家麒,现在的徐慕素九年前正在北平上学,徐老太太以病重为名把他骗了回来和静言成婚。那时静言刚刚十九岁,父亲是清末秀才,考举人先是没中后来就没机会了,所以他把全部精力用在教育两个女儿的身上。
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静言踏进徐家大门那一刻,她的悲剧人生便开始了。徐家麒在她嫁过来的前五天,一直睡在书房,后来终于拗不过徐老太太,在第六日进了婚房,就那四个晚上的其中一个,静言在撕裂和疼痛中做了徐家的媳妇,徐家麒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离开了溪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