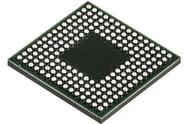摘 要
随着数字游戏成为当今全球的流行文化和新兴媒体,游戏中的劳动成为越发重要的议题。除了围绕游戏生产、销售和运营的游戏产业雇员的劳动外,游戏玩家实际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了与游戏相关的劳动。这些劳动可从三个层面上展开分析:将游戏视为媒介,最普遍意义上的“玩游戏”这种媒介使用行为中即蕴含了多种劳动;将游戏视为文化,部分积极玩家基于情感、认同和爱好展开的文化实践或曰“生产性游玩”实际也是劳动,如攻略创作、粉丝创作、模组创作等,玩家自身作为“产消者”“玩工”嵌入游戏产业生产模式;将游戏视为场域,以游戏为业的玩家群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通过游戏中各种形式的劳动来获取报酬,成为自觉的劳动者。
数字游戏,是依托于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设备开展的数字化的游戏活动,包含街机游戏、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等。游戏是当今青年中最流行的文化消费,也是媒体融合与互动叙事的前沿形态。目前,全球游戏玩家人数接近30亿。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已经稳居全球前列。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约2800亿元,其中自主研发游戏占据了86%以上;而中国自研游戏2020年在海外市场销售收入也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25%。
巨大的市场规模,由日渐成熟的产业来供给。游戏产业将新的生产过程、劳动方式和工作岗位带入我们的视线。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游戏产业包含如下主要环节:硬件生产、游戏研发、游戏出版、分发销售,以及日常维护与运营。每个环节都包含着不同的劳动,且从业者人数众多。
如麻省理工学院的Taylor(2009)教授所言,游戏既是一种可分析的系统和人造物(artifact),也是一种叙事结构和故事世界,而在更广义层面它可以被看成一种“组合”(assemblage),包含了行动者、系统、技术、身体、社区、法规、文化、实践等要素。那么,除了游戏产业中雇员的劳动外,玩家作为关键行动者,围绕游戏从事的劳动也已经非常丰富多元。本文将从“游戏作为媒介”“游戏作为文化”和“游戏作为场域”三个层面来分析游戏中的劳动行为并述评主要的学术观点。

在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受众/用户的媒介使用与内容消费,被普遍认为具有劳动的成分。较早揭示媒介产业这一运作规律的,是达拉斯·斯迈思(Smythe,1977)。他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经典论述认为,大规模制造、受广告商支持的大众传播的商品形态是受众;观众观看商业广播电视的免费内容,其实是一种劳动。这一论述引发了长久而热烈的学术讨论。Meeham(1984)将之修订为“收视率商品论”,莫斯可(2000)认为收视率测量及售卖是控制论(cybernetic)意义上的商品,代表了媒介商品化过程的进步。笔者在讨论网络视频的观看时提出,“注意力作为商品”或许是更清晰严谨的表述(曹书乐,2020:90)。总之,这一理论视角将受众对媒介内容的阅听视为一种劳动。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最普遍意义上的“玩游戏”何以成为一种劳动。
一方面,大量免费游戏产品中放置了广告,需要玩家每过一段时间观看广告以获取继续游戏的机会或游戏道具装备,这种模式无异于商业电视广告盈利的模式,也可以由“受众/数据/注意力商品论”来阐释。
另一方面,玩家玩游戏、讨论游戏的行为,虽然主观目的通常不是为了游戏厂商的利益,也没有自发的“劳动”意识,但客观上使该游戏更知名、更有吸引力、带来更多的玩家,促进了游戏的销售。从Terranova(2000)提出的理论视角来看,这是被资本所剥削的“无酬劳动”(free labor),即一种不基于资本主义薪酬体系的自觉行为。
首先,不依赖广告盈利的大多数免费游戏,其收入来源主要是游戏内购(in-game purchase),即“氪金”。在可以免费玩的前提下,玩家们为什么要氪金?这背后有竞争、情感和社交三层面的动机驱使,如果没有其他玩家的参与和互动,这些动机都将大为削弱。那么,“玩游戏”是不是也意味着帮助公司向其他玩家营销?更有意思的是,游戏厂商会通过精心设计,努力制造稀缺和差异,刺激玩家们消费;而氪金玩家购买的虚拟物品价格,其实又往往由那些不花钱“埋头苦玩”的玩家的“无差别劳动”所锚定——“如果普通玩家平均要‘肝’100 小时才可能得到某个式神或培养出某个极品御魂,那么为它氪金1000元,是不是就显得非常合理了呢?”(曹书乐、许馨仪,2020)
其次,大量游戏是需要玩家付费购买的。除了传统的营销、评测等促销方式外,影响新玩家购买的重要因素是数据和口碑。在各种应用商店里的下载、付费、活跃人数等排行,都在告诉玩家们,哪些是“好游戏”“热门游戏”,值得尝试。而这些排行所依据的数据,都是玩家们“玩游戏”的劳动所产生的。玩家们线上线下的评价推荐行为成为推动游戏热销的“口碑”。此外,这些数据和口碑还将影响游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价起落。

随着数字游戏日渐深入当代青年日常生活,游戏不仅仅意味着在特定硬件设备上打开的某个娱乐软件,而是一种熟悉喜爱的文化,一个可以投注情感(affect)、产生身份认同(identity)和意义的无形对象。因此,围绕游戏而发生的文化实践,往往因情动而富于创意,因认同而不计报酬,但又因为资本强大的*与力量而被收编、征用与剥削。
在数字内容产业框架中,生产与消费这两个似乎应当泾渭分明的领域,其边界越发模糊。商品的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身份的交织与模糊,形成了所谓“产消者”(prosumer)的身份。在游戏领域内,Pearce(2006)颇具洞察力地提出了“生产性游玩”(productive play)的概念,以指称为了游戏本身、而非受雇进行的创造性生产,并认为这是游戏活动中活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Wirman(2009)将玩家在游戏中的生产性(productivity)分为两大类:工具性的和表达性的。具有目标并追求高效实现目标的电竞选手更偏向工具性,而角色扮演类游戏的玩家更倾向表达性。Wirman认为,创作攻略、游戏路线、物品/地点数据库、作弊代码属于工具性生产;粉丝小说、引擎电影、诗歌、皮肤属于表达性生产;而制作模组、补丁处于两者的交叉地带。
Kücklich(2005)提出的“玩工”(playbor)概念更为流行。他通过分析游戏模组经济提出这一概念,并由此来讨论“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他认为,玩家的热爱为游戏开发者和发行商节约了游戏的推广费;游戏模组的创作与出现,有效地延长了游戏的生命期;游戏模组培养了玩家的忠诚度,促进了游戏销售;模组的创作带来游戏创新,也是一种无报酬劳动。这种将玩(play)与劳动(labor)结合起来的“玩工”,既非雇佣劳动,又非完全的娱乐休闲。“玩”的表象遮蔽了资本对模组爱好者的剥削。
上述种种理论概念试图揭示的,是比普遍意义上“玩游戏”更进一步的游戏文化实践,是玩家群体中更为积极的那部分人,如何通过劳动,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与游戏相关的文化、社群及无形资产。最常见的是互联网上的各种游戏主题虚拟社区,如《魔兽世界》中国玩家创建的“艾泽拉斯国家地理”论坛(nga.cn),多年来已经从单个游戏的粉丝社群演变为庞大的游戏主题社区;还有豆瓣小组、贴吧、微信群、QQ群,以及围绕专业游戏公号、微博大V、B站UP主等形成的互动群体。在社群中,玩家除了分享关于游戏的信息、讨论玩法、提供攻略、答疑解惑、分享游戏经验,还会创造出该游戏特有的文化和俚语(slang),增强了玩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基于这些社群,玩家们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文化实践。
(一)攻略创作
游戏通常会设置一定数量的关卡、谜题、障碍或者需击败的boss,提供不同难度选择,但并不会附上一份产品说明书或者通关手册。以经典游戏《古墓丽影》系列为例,在每一小关卡内都有特定的谜题需要解决,例如通过转动轮轴,使箱子停留在特定的地方,主角方可在箱子之间顺利跳跃,进入通往下一关卡的通道。如果玩家始终无法解开这样的谜题,游戏就无法进展下去。此外,打boss也需要一定战斗技巧,例如有效利用环境,以及寻找boss的弱点。对于新手玩家来说,熟练玩家制作的攻略有助于自己更轻松愉快地完成游戏。
在广泛流行的大型多人在线网游(MMORPG)或者战术竞技游戏(MOBA)等类型中,攻略的意义在于帮助玩家更有效率地探索庞大的世界、完成各种任务、积累数字资产、提升等级,或者熟悉各种角色、增强对战技巧等。
还有很多游戏攻略为百科图书式或图鉴式,并不具有帮助玩家打通游戏的功能,而是能丰富玩家的游戏体验。
编写这些攻略,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也并非每个玩家都能胜任。能写出攻略的玩家,要么具有高超的游戏素养,在解谜、策略、战术、技巧、反应等方面能力突出;要么付出大量时间,一边打游戏,一边记录下过程中的关键点,整理成清晰易懂的文本。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攻略创作者往往成为其他玩家心中的“大神”。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游戏攻略开始以短视频方式出现,比传统的图文攻略更直观生动和碎片化。甚至很多人自己不玩游戏,而是沉迷于看主播通关,被戏称为“云玩家”。
总之,长期以来,创作攻略是一项没有即刻经济回报的利他主义的分享,其回报主要是精神层面上来自其他玩家的肯定和赞美。近来,基于视频的攻略创作则增加了带来经济回报的可能。
(二)粉丝创作
一些足够喜爱所玩游戏的玩家,可能会逐渐形成粉丝身份,有意愿和能力基于游戏的世界架构、角色和主要剧情进行粉丝创作(fan creation),如同人小说、同人绘画以及基于游戏角色的条漫等。
学界此前已开始关注基于网络文学IP或影视IP的粉丝创作,即詹金斯(2016)所谓的“文本盗猎”行为。类似现象近年也出现在游戏领域中。笔者与合作者研究《恋与制作人》时,发现这款低竞争性、高体验性的“乙女向”国产卡牌游戏,是能激发同人创作的典型游戏。随着游戏的流行,大量同人文、同人漫画、同人音视频和同人实体产品开始出现。这些粉丝创作基于游戏人物的人设,在剧情上进行了改写、扩写和续写,增加了诸多细节,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很多游戏粉丝觉得“太太们”(即同人创作者)比游戏开发者更懂用户;一些玩家首先是迷上了同人创作作品,才开始接触游戏。无独有偶,笔者在研究《阴阳师》游戏时也发现,很多玩家先是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著名画师、写手创作的《阴阳师》同人作品,“在开始玩游戏之前已经对不少角色,比如茨木、大天狗等耳熟能详了”,才开始接触这个游戏(曹书乐、许馨仪,2020)。这生动说明了“为爱发电”的粉丝创作如何成为免费的劳动,为游戏公司的利润添砖加瓦。
还有一种游戏玩家特有的粉丝创作,即引擎电影(machinima)。引擎电影是利用游戏引擎实时渲染生成的动画作品,创作者在现成的游戏中“扮演”特定角色,录制游戏画面,再进行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完成作品。基于《魔兽世界》创作的引擎电影《网瘾战争》,由百余位玩家通过互联网组成团队,业余时间免费参演制作,并于2010年初发布于多个视频网站。两周之内,该作品仅在优酷网就播放了超过百万次,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后来还获得了当年“土豆映像节”的最重要奖项。它涉及网游规制、网瘾治疗等玩家热议的话题,还诙谐再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时事热点,征用了大量其他流行文化文本,是一次成功的亚文化叙事(何威,2011:236-244)。
(三)模组创作
“模组”是“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的音译。Steam游戏平台将“模组”定义为“玩家对游戏或软件的修改。其修改程度可能是仅对游戏内一件物品的编辑(例如武器的样式),也可能是全新的人物、关卡、地图和任务,乃至彻底成为另一款新游戏。”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FPS)是最早鼓励玩家创造的游戏类型。Valve公司发布单人射击游戏《半条命》(Half-Life)以后,主动邀请模组社群中的玩家开展创作。在此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模组,将《半条命》中“人人为己”的死亡战斗模式,转变为军事小分队协同作战,设计了新的地图和场景,并在1999年演变为至今仍风靡全球的游戏《反恐精英》(Counter Strike)。尽管能够创作模组的人只是玩家中的少数,但他们出于热爱的无偿劳动,积少成多,被公司所收编,成为一支无需支付报酬的研发大军。(赫茨,2007)当然,创作游戏模组有时能给“硬核玩家”带来职业发展机会。如ID软件公司早年发布的著名游戏《雷神之锤II》(Quake II)中,由一位玩家波尔格编写的人工智能插件在玩家中广泛传播,并得到更多玩家的修订完善,波尔格因此被游戏公司Epic看中并获得工作。
在当前几乎所有国内外热门游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组。这样的大环境使得模组创作有更多得到经济回报的机会。如Steam平台的创意工坊鼓励各种游戏的玩家上传相应的模组,并且可以收费;又如《我的世界》中国版提供各种开发工具和教程,鼓励玩家成为模组开发者,宣称“让兴趣享有丰厚收益回报,成为优秀开发者轻松实现月入破万”。

除了轻度休闲玩家、重度粉丝玩家,还有很多在游戏中废寝忘食的人,其首要目的并非休闲娱乐,而是从中获取经济报酬,甚至是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他们与前述的“生产性游玩”“产消者”“玩工”之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界线:他们清醒意识到自己在以劳动换取报酬,游戏是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像农场、工厂或写字楼;游戏同时也是其生产工具,如同锄头、车床或打字机。这正是“以游戏为业”的劳动者的自觉。这种劳动更倾向于边缘化、临时性、“不稳定”,包括电竞选手、游戏主播、金币农夫和代练陪玩等。
(一)电竞选手
游戏产业的发展和细分,让游戏出现了体育赛事化和职业化的趋势。通过信息网络与设备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高度竞技性的游戏,被称为电子竞技。它是娱乐、体育与文化的交汇。
2003年,电子竞技成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承认的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2008年批改为第78个)。2016年,教育部新增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如今,全球流行的竞技游戏《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每年总决赛有数以亿计的全球观众,单场观赛数据不逊于NBA等传统体育盛事。电子竞技如同其他职业化的体育项目,与国家荣誉密切关联。电竞选手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也得到主流媒体和主管部门的肯定与支持(何威、曹书乐,2017)。
目前电竞选手的收入待遇呈现金字塔式两极分化趋势。根据人社部(2019)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国电竞职业选手约10万人,加上半职业和业余选手以及从事教练、分析等工作的从业者,整体从业规模约50万人。其中,顶尖电竞选手的年薪达到百万元及以上,另外还有商业代言收入,而近四成电竞从业者薪资水平等于甚至低于当地平均薪资。一线选手、二线选手和青训队员的工资水平差距明显。同时,电竞要求选手反应快、状态好,是公认的“吃青春饭”行业。所以电竞选手普遍低龄,半数以上电竞从业者不到22岁。一方面,早早投身电竞训练可能会影响学业发展;另一方面,电竞选手通常不到30岁就退役,退役后的职业发展尚无成熟的路径可循。
此外,高强度的训练及比赛压力极大地影响着选手的身心健康。长期久坐不动,腱鞘炎、网球肘、颈椎病、下背疼痛等职业损伤十分常见,还伴随着进食不规律和饮食结构的单一,这样的工作状态竟与加班文化中的“996”办公室白领形成了共鸣。曾带队夺取全球总冠军的中国电竞名将Uzi于2020年6月因伤退役,他身上集中体现出电竞训练与比赛带来的“工伤”——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训练、熬夜、饮食不规律和压力,导致肥胖,引发II型糖尿病,再加上手伤,最终无法继续这份工作,退役时年仅23岁。
(二)游戏主播
游戏主播涵盖了通过视频直播游戏过程或录制编辑游戏相关视频上传网络,并从中获取报酬的劳动者。观众通过弹幕、评论、赠礼、打赏等方式,与游戏主播展开互动。
游戏直播是我国近年兴起的网络直播的最主要形态之一,用户规模已达2.6亿,占到了网民整体的22.9%。真正促使网络直播脱离传统视频网站,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产制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正是游戏直播的兴起。2014年,从游戏语音辅助软件起家的YY和弹幕网站AcFun中,诞生了游戏直播行业两大巨头虎牙和斗鱼,使得一大批游戏主播脱颖而出。(曹书乐,2020,57-58)国际知名的游戏直播平台则以2011年成立的Twitch网站为代表。2017年,Twitch上已有超过200万个独立主播,日活用户达一千万(Taylor,2018)。
从规模对比可见,国内游戏直播热度高、用户基数大,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速度及游戏玩家与“云玩家”规模的庞大。鉴于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网民都在消费游戏直播,游戏主播们的劳动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游戏直播平台,而是遍布各种社交媒体,以触达更广泛的用户群体。B站、抖音、甚至小红书这种美妆社区,都有博主进行游戏直播、上传的游戏短视频,从介绍推广游戏、趣味自制视频,到过关演示、攻略发布、展示战利品,各种内容应有尽有。
游戏主播通常只要有一台电脑或手机,加上摄像头等外设,客厅或者卧室就能转换成劳动的场所,主播也因此获得灵活就业的可能。高超的游戏技艺能助力主播获得大量粉丝;如果社交能力、表达能力或视频制作能力出色,即使游戏水平一般,主播也能广受欢迎。游戏主播通过提供内容累积粉丝,粉丝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主播的劳动回报,有足够流量后游戏主播再通过植入或口播广告、打赏、代言等多种方式实现变现。游戏主播们每日花费大量时间打游戏、直播、与观众互动和制作游戏视频,因此同样深受宅家久坐、睡眠不足等健康困扰。
对于游戏主播而言,劳动过程也带来自身视频制作能力的提升和社交圈的丰富,或曰社会资本的提升。不少创作者靠自学掌握了各种视频制作技术。同时与一些核心粉丝成为了线上或者现实世界中的朋友,能对主播的内容选题甚至生活提供种种建议和帮助。(曹书乐,2020:190-191)即使他们将来不再从事主播劳动,这些能力和资本依然可以为其所用。
(三)金币农夫
游戏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存在大量虚拟物品,或用于提升玩家的作战能力,如装备、药剂等;或用于改变玩家的虚拟形象,如坐骑、皮肤等;或可以丰富玩家的物品收藏,满足收集欲。这些虚拟物品一般被设计为,需要玩家在游戏中各处采集搜罗,或通过不断对战、升级而获得的战利品,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玩家渴望获得这些虚拟物品,但未必都愿意或能够在游戏中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一些玩家愿意付出真实货币去购买虚拟世界中的物品,这就成为一种市场,并因此出现了在游戏世界中劳动、获取虚拟物品并出售获利的人。这种人在英语媒体上通常被称为“金币农夫”(gold farmer),他们的劳动过程被称作“打金”。
Dibbell(2007)在《Play Money》一书中,描绘了在MMORPG中玩家们对魔剑、魔法胸甲和特殊药剂这些虚拟世界战利品的渴望如何催生出一个产业。在虚拟世界类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华裔女子Anshe Chung成为第一个从买卖虚拟房地产赚取到百万美元的人,并因此登上了2006年的《商业周刊》封面。耐人寻味的是,她在湖北开设了工作室,雇佣一批中国劳动者创造虚拟物品并向西方玩家售卖。
个人“打金”的行为在市场规模扩大后,逐渐演变为工作室制度。游戏工作室规模化地雇佣打金人员,并将其劳动组织化、规范化,以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向市场大量提供虚拟物品和虚拟货币。在全球化语境下,一些热门网络游戏向跨国玩家提供服务。这使得西方传统产业中利用第三世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外包部分工作以缩减成本的做法,在游戏领域被广泛应用。
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打金”现象早有报道。2006至2011年间西方媒体对中国游戏的报道,更倾向于各种负面、偏离的个案,如网瘾患者和网瘾治疗中心,也包括“金币农夫”。一些报道认为,“富裕的西方人”在购买中国制造的“便宜货”之后,又开始购买中国“金币农夫”生产出来的虚拟货币,将打金视作“血汗工厂”般的实践。(Wirman,2016)
Nardi与Kow(2010)认为,包含主流媒体、博客、引擎电影及电影在内的关于中国“金币农夫”的媒体话语,是一种自以为了解中国的“数字想象”,这种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漫长历史挂钩。他们认为真实的打金还采用了脚本挂机等多种方法,并非西方想象中生活条件极差的血汗工厂。Liboriussen(2016)则研究了过着舒适小日子的中产阶级“业余金币农夫”,指出这种劳动者在中国的不同形象。胡与邰(Hu & Tai,2017)则对中国5个城市的13个打金工作室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调研,探讨了打金的理由、动机和认知,并将其视作中国青年主导的游戏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粉丝劳动”,通过变革性的游戏玩法嵌入到全球游戏资本主义市场中。
上述研究颇具启发,但仍留给我们思考空间。“金币农夫”虽非西方媒体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劳工,但也并非都是业余时间玩票的中产阶级;打金未必都是在对游戏的爱与热情中的附带工作,它更多时候或许还是没有感情的“搵一份工”。有市场、有需求,就进行供应。哪个游戏热门,需求激增,工作室就拓展哪个游戏的业务。工作室和金币农夫需要在劳动过程中研究,怎么升级装备、刷怪、下副本才能更高效地打金,甚至怎么使用灰色的技术手段来提升劳动效率。以游戏为业,注定了个人对游戏的爱好并不是劳动过程中的重点或决定因素。

四、结语
如前所述,除了游戏产业链条上内嵌于游戏商品生产、销售和运营过程中的劳动者,全球30亿游戏玩家同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游戏从事着极为复杂的劳动。
首先,最普遍意义上的“玩游戏”就可以被看作一种劳动。玩家们一方面遵从经典的“受众商品论”逻辑,另一方面也在为游戏厂商免费营销、提升股价,更以亲身劳动锚定虚拟物品价值。对这些劳动的学术探讨可以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广告营销等理论资源。
进而,那些更积极主动、更具创意和能力玩家,出于情感、认同、爱好等动机,开展各种“生产性游玩”,从社群建构、攻略创作到粉丝创作和模组创作。这些行为通常不以经济回报为目的,却极大地促进了游戏文化和产业,有利于游戏厂商;玩家也因此化身“产消者”或“玩工”。相关学术研究可以借鉴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Arvidsson和Sandvik(2007)认为资本占有的游戏玩家的劳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活化(activation),指大多数玩家的用户内容生产包括反馈分享,本质上是一种对游戏的免费推广;另一种是创新(innovation),指硬核玩家发现游戏程序中的故障或不足,并从程序、内容到效果去优化游戏的过程。游戏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玩家的非物质劳动,这也反映出信息资本主义的关键逻辑:借助生产外部性作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不难发现,这两种方式似乎恰好对应本文所述的前两个层面的玩家劳动。
更进一步,数字游戏拥有相对自洽自足的市场经济体系、运行规则、文化惯习,因而也构成了一种工作的场域。我们观察到,以游戏为业的玩家群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通过游戏中各种形式的劳动获取报酬。游戏产业的发展,也是新时代数字经济和创意经济的缩影。旧的工作岗位在消亡,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有机会在其中找到可以从事的劳动,获得基本的收入。这些劳动既包括相对稳定的组织内受雇职业,也包括大量自就业、自由职业、临时工作;牵涉到情感劳动、表演劳动、数字劳动、创意劳动、不稳定劳动等多种理论概念,相关研究可沿袭社会学、人类学对劳动的考察。
围绕游戏玩家的劳动,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以游戏为业的劳动分工情况如何?游戏主播与MCN机构的关系如何?从工作室老板到基层金农或代练,其角色不同带来的生产和分配差异如何?游戏世界中的劳动和真实世界中的劳动有何本质的区别?以数字游戏为生产工具与劳动场域,让劳动过程呈现哪些新特点?又能怎样促进我们对于虚拟经济、技术赋权、平台剥削、算法权力等重要概念的理解?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探究。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2期,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