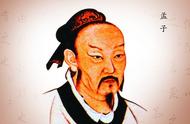孟子在梁惠王艰难的时刻前去游说,却遭到梁惠王、襄王父子的慢待,正面说明了梁惠王父子二人在求贤方面有着自己的傲慢,侧面则表明了孟子选择的时机不对。

梁惠王原称魏惠王,只因商鞅年轻之时在魏国寻求发展受到了魏惠王轻视,等到商鞅在秦国取得成绩之后,说服秦王前来攻打魏国。最终设计赢得了胜利,迫使魏惠王割让河西之地求和并迁都,这才有了梁惠王之称。
孟子在游说梁惠王的时候,魏惠王在于齐国的交战过程中损失了庞涓,同时太子申也被俘虏。多面受挫的魏惠王,正准备奋发图强,寻求各国人才前来大力发展国力,从而报仇雪恨。
孟子前去游说梁惠王的时机,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论学说并不适合那个时候魏国的情况。孟子的仁政主张,相信梁惠王早有耳闻。因此,在他们见面的时候,梁惠王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客气。

孟子没有遮遮掩掩把这种轻蔑进行修饰,而是直接在他的文章之中如实体现记录出来。梁惠王见面直接就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直接称呼孟子为“叟”。
这是孟子或者孟子弟子在《孟子》里的记述,而司马迁在写到梁惠王的时候,也记录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况。
司马迁是这样写的:“寡人不佞(我真是没有才能)打了三次败仗,儿子被齐国俘虏了,得力战将被*了,国家现在非常空虚,实在愧对祖宗与国人,我自己感觉 很愧疚。”
先做了一些自我介绍与放低姿态,然后开始询问孟子:“老先生,你千里迢迢辛苦来到我国,实在是我的荣幸,不知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国更加有利啊?”
从《孟子》与《史记》这两部作品的记载,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叙,更符合人之常情。如果仅看《孟子》里的介绍,可以发觉梁惠王是一个一点礼貌都不懂的人。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梁惠王在那个时候是极力希望得到人才的助力。

在孟子的记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惠王思想的变化,从对孟子仁政的难以接受到慢慢地可以接受,这正是游说的结果。
很不幸的事,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梁惠王即将按照孟子的思想进行变革时,他却去世了。
梁惠王的儿子继位,也召见了孟子。孟子的感受,同样很差,这在他的文章里也体现了出来。孟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这一句比喻,自古以来被很多人引用。这句话如果从普通老百姓嘴里说出来,可能会说“看他不是个好东西”、“看他不是个好人”,可以感受孟子当时的气愤有多强烈。

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在学识与威望方面有着独特的国际地位。而儒家一直主张“君君臣臣”的思想,孟子却说“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一位新国君,终于有了机会成为了一个王,那个时候必定是最为得意之时,怎么会有“畏”呢!难道见一位国际知名游说人员,就得表现出有所“畏”?
孟子记载说:“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因为有了见梁惠王的先例,孟子在形容这父子二人的文字,是否可信,真的要打个问号?
孟子在记载梁惠王时,还有个“叟”的称呼,虽然不知道这个“叟”在当时的确切意思,但无异乎“老头”、“老先生”这些意思。而到了儿子这里,直接没“叟”,上来就问“怎么定天下?”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学泰斗,在遇到初出茅庐的小王时,受到一些不尊重,发发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形容这父子二人,确实有些不着边际,不合情理。
既然小国王问了,孟泰斗就得回答,还不能不礼貌回答。一是因为自己前去求职,必须客气;二是因为自己在国际上是有威望的权威人士。因而孟子客气地告诉梁襄王,只有一个不喜欢*人的人才能定天下。
作为战国时代,之所以称为战国,就是因为战争,不*人就不会战争,也就不叫战国。自孟子说过这句话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历史证明这句话不仅是错的,而且没有实现过。也许自人类学会*人之后,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去定天下了。

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确实很完美,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不实用。特别在那个以战成名的时代,更何况当时梁惠王接连打了三次败仗、太子也曾被俘虏、战将被*。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处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之中,需要一位鼓舞人心的实战派,来带领大家一起向前继续奋斗。
孟子的理论学说没有错,孟子前去求职的时机也没有错,但他提出自己理论的时机不对。如果能够先富国强兵,待到报仇雪恨后,再提出仁政,梁惠王、襄王父子定当有不同的态度,孟子也不会如此气愤,用“叟”与“不似人君”来形容这父子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