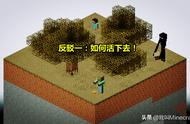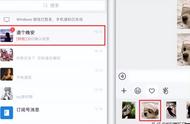“爱欲”是一个多变且繁复的概念。当我们在谈论“爱欲”时,本质是在谈论什么?在爱欲的范畴中,现代性是如何完成的?或者说,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断裂”“事件”与“变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在近期出版的新书《论爱欲》当中,细细考察了“爱欲”尤其是现代性语境中“爱欲”的变迁。
本文是作家胡赳赳对汪民安《论爱欲》一书的评论。在胡赳赳看来,汪民安对爱欲文明的现代性考察,始于情动、明于事件、终于奇遇。他发展了巴迪欧的“同一”、“事件”、“断裂”、“相遇”等概念。意图维护“爱欲”的统一性。而这些都表明了汪民安实实在在的雄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分析了汪民安如何富有洞见性地串联、整合关于爱欲的哲学思辨,同时还指出了他对于本书更深的期待,“作为一个可以写出原创思想的学人和思想评论者,不应总是躲在经典背后,缠绕于更为个人化的解读。”

《论爱欲》,作者:汪民安,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一
什么是“爱欲”?汪民安意图维护“爱欲”的统一性。与大多数人士将“爱”与“欲”分离的看法相反,汪民安在《论爱欲》一书中,将“爱欲”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在他看来,“爱欲”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统一于“一”。要形成事件,必然带来“奇遇”。爱欲的发生来自于一场又一场的奇遇,在奇遇中,爱与欲统一起来了。对身体的意欲即是对精神的热爱,爱他人即是自恋的移情。他从巴迪欧的看法引申出来,要想统一于“一”,要形成事件,必然意味着事物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不是自我重复。
喃喃自语形成不了爱欲,必须有一个倾诉对象,必然有某种意味的一见钟情,必然有两个人相处的亲密无间。爱欲意味着过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世界被轰然洞开。两个人的亲密行为也同样是求知的行为。在“奇遇”中,一个原本不被认知的世界被打开了,亲密之爱可以走向知识之爱/真理之爱。同样的,真理之爱也可以导致亲密之爱。
在这里,汪民安将爱欲之“欲”处理成一种非*的关系,此处的“欲”可以理解为“指向”,爱欲即爱的动力与指向。或者可以说,爱欲是一个矢量:爱是一种作用力,而欲指引着方向。有了作用力和方向,爱欲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在汪民安所阐释的“爱欲”理念中,他考察了古典的爱欲观,又继而从现代性的爱欲形成中,发掘出他自己的某种爱欲考古的知识癖好。他完美地逃避了中世纪的骑士之爱、罗曼蒂克之爱。但却又从《十日谈》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考证出了爱欲之所以存在的精神背景,它是关乎“承认,事件与奇遇”的谱系。
在古典时期,爱欲更多的指向真理之爱与上帝之爱,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奥古斯丁,他们一心形而上,他们的爱欲表现为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受人尊敬之处亦在于此,他们处理情感与*的方式,显然只有通过高级的智慧和严于律己的苦修才能达到。这种抽象式的爱欲,在他人或普通人身上,是无法复制的,因此他们被反复地“高推圣境”,因为他们满足了普罗大众对完美主义者的形象进行空想的全部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人的“爱欲”是一种以空想的形式发生的理念,他们投射自己的意识状态到一锅“有机汤”或“混沌池”中,不停地搅拌,试图发明自己独特的口味与配方。这种爱欲理念,既是关乎求知,也是关乎创造,在历代知识人的反复搅拌之中,原始经典得到再次阐释,也得到了重新发现,它们获得了新的“灵韵”。如果要把每一个时代当作一个新的“事件”来看的话,必然会发现某些地方“断裂”了,回不去了,但同时,某些地方“焊接”得依然牢固,人性并没有长足的进步。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作者供图。
“焊接”不同于“禁锢”,焊接在生物基因的点位上产生,那些点位上标明了人性的共通与个性的不同。人性之所以强大无匹,进化缓慢,是因为个人在同类之中,被反复地拉扯,反复地矫正,直至均值回归——能离散或逃逸的,能克服这个时代的,毕竟是少数。
而“禁锢”则对应着“断裂”,我们说古典时期是“禁锢”的,而现代时期之所以迎来了身体的解放,是因为“断裂”发生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即中世纪后期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文艺复兴。这构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件”。无论上帝之爱/天堂之爱多么神圣,无论知识之爱/真理之爱多么伟大,但是,尘世之爱以及同性之爱,不正是事物的解放和理念的进步吗?
汪民安花了很多笔墨,描述了“同性之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虽然在当下称不上惊世骇俗,但依然给人带来深深的“战栗”。他隐约建立了一个爱欲动力学的坐标:横坐标为性取向,纵坐标为肉身到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的爱欲可以在此基础上滑行,这个坐标的尺度可以无限延展,前提是,你是否具有这种勇气,勇气即是动力,它能打破尺度与禁忌、界线与认知。所以我们看到,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既是思想的,也是身体的。这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互相缠绕,你不能说哪个更高级。在那一瞬间,坐标被压缩了,被等同了,变成了一个原点,这个世界最终呈现为一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爱欲的原点,也是世界呈现出来的原点。这是知识之爱与身体之爱的同构关系。
而在对“同性之爱”的描述中,汪民安注入了深深的凝视,爱同性对他而言,是一种可望可及的普遍事物,并不具备独特性和猎奇性,它本身是先验合理的。同性之爱本身是一种同类之爱,爱自己走向爱同性,爱同性走向爱同类。人的爱欲境界正是这样基于身体技术的反复发作,一直推向无限远处。生殖之爱固然伟大,同性之爱岂不是更为纯粹?也由此,爱欲的方向指向了全方位性。爱欲的动力呈现出一条激情与隐秘的曲线,汪民安在羞怯与雄辩中,完成了他的杰出考察。
二
当我们在谈论“爱欲”时,本质是在谈论什么?汪民安躲在经典序列背后,他将前台发言隐去,宁愿屈身于伟大经典的注脚之中,他不知疲倦地阐释,这正对应着某种理念:阐释经典将与经典获得同样重要的位置。他没有在“原创思想”或“理念发明”方面更进一步,这是由一个学者的严谨与规训决定的。汪民安不是那种类似于以赛亚·伯林式的观念史学家,他更多的方法论是基于细读经典所带来的“回响”。那种空谷幽兰式的回响久久回荡,成为汪民安心中抽象的元音。
汪民安展现出他的某种诗性,在对文化理论的梳理方面,他将诗性注入到一种理解之中,这种理解尽管可能是片面的、片段的,也可能是缠绕的、喋喋不休的,但他的确取得了某种成就:在对过往经典的打量时刻,他将他的原创思想,小心翼翼地隐藏在解读之中,隐匿在大师们的骨骼之中。他是那个不动声色却又声色俱佳的意会者,他意图阐明一种关系:一无所加而无所不加。
至少有两点,表明了汪民安实实在在的雄心。他提出了“爱欲动力学”,尽管指认出这样一个概念,是我强加给他的一个“术语”。他从未明确地提出来“爱欲动力学”,但他又洞晓般地书写了出来,在字里行间中,他的这种呼之欲出的理念无处不在。但他就是宁可隐忍,抱持热情而不捅破这样一层“保护膜”。这珍贵的膜性结构等待他的读者与知己们洞穿?
在一种整体式的结构中,汪民安处理“爱欲动力学”的母题。我们简单翻译成通俗的话:活着是为了爱。爱是活着的唯一动力。一个人如果没有爱过,那可以说他没有活过。爱欲体现的是生命力的能动,爱欲是生命力的展开。升华者,则接近真理,接近上帝。凝华者,则成为尘世的伟大颂歌、相互恩怨。汪民安则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可以将爱欲视作这种最大的善。因为只有爱欲,才可以让自己不死,爱欲是拒绝和战胜死亡的最有效的方式。”
尽管没有直接将“爱欲”与爱真理、爱美好、爱善行画上等号,但汪民安用一种比较遮蔽的方式,隐约传达出这样一种气息。因此他并不避讳对同性之爱的讨论。异性之爱创造了一个新的后代,而同性之爱创造了一个新的灵魂。汪民安提出了他的观点:“同性之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灵魂的孕育、培养和再生。”
尤其是在第一章节之中,汪民安叙述“真理之爱”,他明白晓畅地将古典式爱欲与文明进程的关系阐释得一览无余。他不无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爱欲看作一个基本的动力,它是人类文明持久延续的根源。”这也隐隐可以看作,他为后来的叙述,他为他的爱欲动力学的叙事,进行了一种基调性的铺陈。

《爱的多重奏》,作者: [法] 阿兰·巴迪欧,译者:邓刚,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除了对“爱欲动力学”的梳理、推导与反复叠加,另一点能体现汪民安雄心的是,他对“奇遇”这一章节的把控。“奇遇”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原创式的一个概念,他从阿兰·巴迪欧的“相遇”入手,提出了爱欲是一种特殊的相遇,这是爱的奇遇。危机和风险,与浪漫和激进共存。他区分了普通的相遇与奇异的相遇的不同:将不可能的相遇或相遇的不可能性实现,便构成了奇遇。由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登场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奇遇”。奇遇之爱,在汪民安看来是超越了社会编码的自主之爱,是充满风险的赴死之爱。
如同一个漫长的回环一样,汪民安以“奇遇”作为终章,在回顾了现代性的爱欲变迁之后,他又申明,只有奇遇之爱才是无限接近于古典的、真理性的。不管现代社会被如何形塑,不管持有如何的爱欲理念,只要我们具有奇遇的勇气,便最大限度地接近柏拉图意义上的真理之爱。
三
到底在爱欲的范畴中,现代性是如何完成的?或者说,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断裂”“事件”与“变形”?
从“爱欲”到“情动”这种概念的转换,可谓是爱欲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笛卡尔,他们在描述爱欲时,几乎都是带着一种生理式的激情,带着伦理的激情。他们既有对科学的爱,同时也残留有对上帝的爱。汪民安认为笛卡尔遵循的是情感动力学,而斯宾诺莎遵循的是情感几何学。只不过,笛卡尔的生物学解释停留于机械化,斯宾诺莎则更注重伦理。笛卡尔认为爱的动力来源于“动物精气”,而斯宾诺莎对*的解释导向了现代性,他说:“*是人的本质”。斯宾诺莎承认*把人性中一切努力总括在一起,但又因互相冲突与反对,“时而朝向这里,时而朝向那里”。
某种程度上,斯宾诺莎启发了德勒兹提出“情动”概念。汪民安解释说,情动(affect)乃是对人的本质的描述。“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的情感变化。”这种情动既是身体性的,也是心灵范式的。因为“人应该从他的冲动*,从他的情感活动去判定”,而不是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纳入更高一级、更抽象、更稳定的概念系统中”去判定。
这便是现代性的分野,对*的处理,是倾向于无欲还是各从其欲?古典学者立意虽高却趋于空想,他们寄希望于*能升腾为纯净的形而上,终至无欲之境。无论是处理烦恼、激情还是痛苦、欢乐,现代学者则从人本身、人自体出发,关注身体的情动,关注肉身此在的永恒。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要处理,因此没有一条所谓的“大道”,肉身成道是由无数条交叉小径构成的,这是迷人的真相,也是个人的人性解放。
汪民安发现了这条隐秘的分界线,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将*看作一种生命的动力,如何将这种动力的方向进行转归并列为谱系,最终他从“情动”这个角度,将古典与现代性进行了划分。与此同时,他也给予“爱欲”这个文明母题一种新的切入角度:曾经拥有的古典真理虽然崩塌了,但其卓绝之处依然卓绝,并不会因为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损伤半分。因为那是人性的最高处,永远激励着少数天才与大师攀缘。而对普罗大众而言,现代性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可能。他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情欲,可以大声表达热爱和赞美之意。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女权主义者亦如此。彼此的“情动”可以大到一个相互拮抗的分贝。
正视爱欲,予以承认。这便是爱欲文明的现代性开端。然而现代性要关照的是:在爱欲中谁是“主体”的问题。这个“主体”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主体”因为经常性的变化和移位,更多的只能用一种“关系”去描述。如果是过分浓烈的爱欲,在其不可名状的激情笼罩之下,可能面临的是主体的摧毁。正如汪民安的描述:“我们可以爱上不同的人,可以爱上爱自己的人,也可以爱上不爱自己的人。可以同时爱上不同的人,可以以不同的情欲爱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爱欲强度。”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黑格尔与拉康也登场了,他们代表着现代性的某种先声。黑格尔的爱欲是平等而利他的,拉康的爱欲是利己的、自我高拔的。这的确是爱欲动力的不同面向,他们当然同样整合在汪民安对爱欲论述的谱系之中。然而此时出现了一个声音,再次确认了爱欲之为动力的合理性。列维纳斯说:“爱欲的运动在于向着超越可能处前行。”另外,汪民安也揭示了叔本华之爱,是自爱与博爱的混合物,爱意味着深深的同情。

《爱的艺术》,作者: [美] 艾里希·弗洛姆,译者:刘福堂,版本: 99读书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
在这里,不可回避的是对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的探讨,这本书对一代知识人的影响太大了,当年懵懂无知的青涩年轻人,大多要靠这本书的阅读当作恋爱指南。弗洛姆认为,爱首先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付出,付出则意味着爱。也就是说爱使人进步,使人扩充自己的无限空间。弗洛姆说:“爱是一种能产生爱的力量;软弱无能是难于产生爱的。”
我们可以看到,爱与表达爱,将使人通向圆满之路,这也是至善之途。不爱者是残缺的,发展不出潜能的,这是一种孤兽的状态。而爱,则使人走向人性的实现与满足。
但是直到巴迪欧的出现,我们才对爱欲有了更为刷新的认知。这就是巴迪欧对“事件”这一概念的论述。巴迪欧认为,只有引发断裂的事情才称得上事件。汪民安对此解释说:“这种断裂是激进的,它意味着事件之前和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复发作的农民起义不是事件,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却可以称为事件。也就是说,那些具有根本性的变化才能称为事件。某些“断裂”与结构性的摧毁出现了,同时,事件导致新生。新生与旧有的形态有本质的不同。

《一个引诱者的手记》,作者: [丹麦] 克尔凯郭尔,译者:王才勇,版本:华夏出版社1992年8月
假如,你在爱中新生,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便是伟大的爱的事件。隐秘而伟大。这也是汪民安对现代性之爱描述的某种“战栗”式时刻。他使我们想到克尔凯郭尔的《一个引诱者的手记》,那种对于战栗的描述几乎导致作者个人作为一个主体,每天都在激情的状态中苏醒、死去、新生。这同样让我们联想到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偶遇一个送葬的美妇人,对那位“黑寡妇”的“最后一瞥”超越了“一见钟情”,诗人灵魂中同样爆发了一场性感而迷醉的革命,世界从此不一样了,爆裂为碎片,并酝酿着新的变形。
四
汪民安对爱欲文明的现代性考察,始于情动、明于事件、终于奇遇。他发展了巴迪欧的“同一”、“事件”、“断裂”、“相遇”等概念。他将作为事件的相遇称为“奇遇”。奇遇是某种辉煌时刻,奇遇使人联想到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奇遇正是这样冒险而使得个人探索世界的走向发生变化。命运不一样了,路径也有新的不同。在奇遇中,人可能会碰上自己的“泰坦尼克号”,也可能是如同“苦月亮”一样的非凡诱惑。
可以说,“奇遇”是汪民安书中最高潮的一个段落,它也是华丽的终章。奇遇使得事件成为可能,也使得“同于一”的爱欲成为可能。无论是上帝之爱、真理之爱还是情欲之爱,它们都整合在一个爱欲文明的光谱中,散发出唯美的颜色与光芒。正是由于爱欲的不朽,人性才可以得到拯救。那些貌似充满冲突、矛盾与困惑的局面,只不过是爱欲的不同层级,它们理应得到整合,各安其位,在一个超级枢纽般的立交桥上,每一种理念各行其是、自行其是、自是所是,通往“同于一”的真理。
爱与欲,其间或掺杂着性。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庞杂的“局面”。要想从中梳理出一条由古典而现代的爱欲文明的观念史,实在是一件难以胜任的事情。幸好,汪民安以其娴熟的方式,也以其骄傲的方式,用充满激情与诗意的写作证明了,爱欲是足可承认的事件。它每天都在“内向爆炸”,为杂多的世界,提供新生之机。
在对文本细读与思想阐述方面,汪民安既有着手术刀式的冷静与精确,又有着诗人般的优雅与洞察力。这实在是为本书的写作构建了一个难得的范本:隐匿于经典背后,将自己的思想移植于经典进行复原式建构,这可能是学者在规范内进行“再论述”的一条妥当路径。
但作为一个可以写出原创思想的学人和思想评论者,汪民安远远不应该止步于此,不应该在一种讨巧的范式中,对“写作风险”抱持一种毫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束缚。换句话说,他本来应该在关于理念的写作中,提出新的概念,提出原创性的思想,而不应该总是躲在经典背后,缠绕于更为个人化的解读。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学者的严谨,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甘于不冒险——也就是对奇遇的背叛。因此我对他的某种“犬儒化”持一点点不同的个人意见。
文/胡赳赳
编辑/走走、张进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