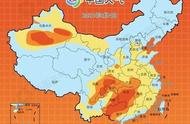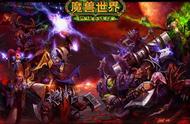从南到北,“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场者”
葛亮写过人物、写过城市、也写过动物,甚至将自己创作的过程写成了散文集《小山河》。
从南京到香港,从《谜鸦》到《浣熊》,从《七声》到《戏年》,再从《朱雀》到《北鸢》,他很注重对细节的描写。
比如,他写香港的时候,会写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像大澳的“侯王诞”、长洲的“太平清蘸”这样象征着传统的节庆。
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城市规划,在写《朱雀》、《北鸢》以及《浣熊》的时候,他会对城市做一番考究,营造在场感,还原时代的历史;也会采访相关的人,做很多准备工作。
他在港大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发表在《收获》上,这篇小说的录用,对葛亮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而后,因一部名叫《鸟》的电影,他写了《谜鸦》,并获“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写作之路“更上一层楼”。
在读博期间,为了还南京的感情债,他用了5年的时间写历史跨度极大的小说《朱雀》,于2009年出版。
继《朱雀》之后,葛亮又写了《北鸢》,以祖父、外祖父的经历作为蓝本,第一次直接讲述自己家族的过往。
故事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收于四十年代中叶,用卢文笙和冯仁桢(葛亮外公外婆的原型)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动荡历史。
除此之外,葛亮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回望自己的成长之路,写下“人间烟火”系列《七声》、《戏年》,将《北鸢》中主人公命运的留白,落定于《七声》。
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爱与恨、痛苦与别离,他们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有对生活的身不由己,有艰辛,也有对生活的执念,命运多舛,终逃不过老天的安排,好比《于叔叔传》。
感染力极为强大的《阿霞》,以一个“缺根筋”的女孩形象展现在众人眼前,她坚强、美丽、充满隐痛,被很多人排除在外,葛亮却把这样一个人物描写得细致入微,跃然纸面,用简练的语言精准地捕捉她的情绪变化,没有丑化弱者的阴冷,每一字每一句,透露出的都是人间的温度。
“一均之中,间有七声”,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里的声音。


“此心安处是吾乡”
评论家王德威曾说:“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
大风始于青萍之末,他深信,历史来自日常,最细微的东西,往往构建成表达、梳理、建筑历史的砖瓦。
在出版《七声》后,葛亮曾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信中说:
“到底历史与现代孰新孰旧,只有人真实存在过的时代才能承载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身边的万物也同他一起回到过去。”
当时,葛亮被这句话所触动,一时之间,所有关于这座城市的人和事,一涌而上。
气息,声音,影像,喜乐,都负荷着人的温度。记忆或许可以作为对抗的武器,在格式化的生活里,渗透,建构,强大,最终破茧而出。
有位出版人说:“这个时代太快了,葛亮却在写一种慢的东西,这个时代太新了,他的小说却把时代往旧里写。”
也有读者表示,读葛亮的文字,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会令人潸然泪下。
这种感动不是激烈的,是平缓的,似乎更像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记忆突然被唤醒。
葛亮说:“我并不是在和今天的节奏和立场对抗,只是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审视世界。”
无关乎快与慢、新与旧,内心向往一个怎样的境地便是怎样,时而回望,时而向前,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今,葛亮在香港已经度过了第17个年头,采访时,谈及“孤独感”一词,葛亮表示“从未想过要融入某个地方”。
每个人都是一个游走者,都是随着自身经历的迁徙发生转移的。
葛亮更在乎的,是所到之处,有没有一张书桌供他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