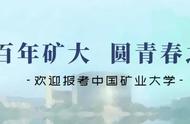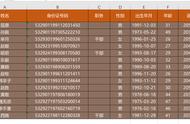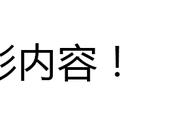作者 | 王铭玉 孟华
摘要
符号学是一门充满了西方色彩的现代显学,它历来被分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符中心符号学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实效主义符号学两条路径。时至今日,符号学有没有第三条路径?此问题是世界当代符号学关注的热点,更是中国符号学亟待回答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的属性、符号学研究的意指模式以及中国符号学在世界符号学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第三条路径是可以探究的,这就是基于中国学者“语象合治”符号观的语象合治之路。本文的思想观点有七:1) 提出“大符号”观来规约符号,对符号的界定标准做进一步完善;2) 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一种中性符号观,其主旨是对二元对立及语象分治关系的解除;3) 语象合治可分为移心型合治和执中型合治,前者跨界有痕,后者整合浑成;4) 语象合治观无论在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中还是在当代西方符号学思想中均具有理论根底和基础;5) 语象分治是西方符号学所遵循的主要路径,但其对符号认识的偏狭和对符号边界的固守已经形成符号学发展新的瓶颈;6) 中国符号学研究者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是非常有益的,充分说明了“语象合治”思想的正确性;7) 中国是一个长于符号思维的国度,其独特、丰富的符号学学术资源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重要依归,语象合治思想的提出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符号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关键词
符号学;大符号观;语象合治;语象分治;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萌芽于西欧与北美,成于法国,兴于苏俄,盛于美国,是一门充满了西方色彩的现代显学。虽然早在1926年赵元任先生就曾发表过《符号学大纲》,但中国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全面接触并研究符号学理论,还是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到了21世纪,随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步伐加快,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后来居上,引起了世界学界的高度关注。伴随中国符号学的崛起,一些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主要观点有二:1) 虽然中国的传统符号资源丰富,但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大部分属于类符号或西方符号学范畴中的非典型符号现象;2) 除了以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符号学路径之外,中国符号学难以提出具有本土色彩的理论。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本文尝试提出“合治符号”的概念,力图为探索世界符号学的东方之路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1 狭义符号观与广义符号观
给“符号”下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但准确、周遍地来界定“符号”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符号概念,我们不妨征引一些符号学家关于符号的定义(王铭玉 2004:12-13)。
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Augustine,S.)说:“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上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h.)说:“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Ch.)说:“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Eco,U.)说:“我建议将以下每种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它们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从而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法国符号学家巴特(Barthes,R.)对符号的看法较为特殊:“自有社会以来,对实物的任何使用都会变为这种使用的符号。”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Ikegami,Y.)说:“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之为‘符号’。”苏联语言符号学家齐诺维耶夫(Зиновьев,А.)认为:“符号是处于特殊关系中的事物,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思想的东西……符号的意义因而并不表现在它本身上,而是在符号之外。”苏联心理学家列昂节耶夫(Леонтьев,А.)说:“符号既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现实的形象,它是概括了该事物的功能特征的一种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索绪尔(SaussureF,de.)另辟蹊径,把符号看作是一个由能指(表达面,语音印象)和所指(内容面,概念印象)构成的两面体,其所指绝不先于能指而独立存在,符号是由一系列差异关系的语音印象和概念印象结合而成,而与外部世界无关。显然,从上述征引中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符号定义,因为思想基础不一样,出发点不同就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从现有的有关符号的定义来分析,可以大致分出三种类型的定义:第一,实体论符号观,以现象学思想为基础。持这种符号观的学者认为:人只能认知现象,而实质或是不可知的,或是人类创造能力的结果。因此,任何一种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事物,如果它发出关于其他不能直接观察的形象的信息,那么这一事物就被认为是符号。简言之,符号指的就是关于事物和现实内容的信息。第二,形式论符号观,以逻辑心理学思想为基础。持这种符号观的学者认为符号是针对意念的或功能的结构而言的,这种结构对于其物质方面是漠不关心的。真正的符号被理解为具体的、起符号作用的因素,符号本身并不存在,它是符号情境的一部分。换言之,符号是指认识主体的模式行为的直观形象方面的信息。第三,双兼论符号观,即兼顾上述两种思想,形式论与实体论相结合。许多符号学家以此为出发点来界定符号,他们既看到符号的物质性、实体性,又承认它的思想性、形式性。由于前两种定义过于严苛,常被看作“狭义符号观”,本文称为“分治观”:将实体和形式对立起来分而论之。而第三种定义由于可以接受更多的符号入列,常被看作“广义符号观”。
基于广义符号观,王铭玉(2004:14)也曾给出过一个对符号的尝试性界定:“所谓符号,是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这里,阐明了符号的四个重要性质:一是符号具有物质性。任何符号只有是一种物质符号,它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物质符号包括有声符号、光学符号等。二是符号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如用天平表示法律的公正,用V形代表胜利。三是符号具有社会性,传递一种共有信息。符号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认识,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共有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例如“砰”的一声,它可能是鞭炮声、枪声或汽车轮胎破裂声,但对赛跑运动员来说,起跑的枪声才是符号。四是符号具有对等性。任何符号都由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构成,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式与内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以一束梅花为例,可以用梅花表示坚贞,这时,这束梅花就是符号形式,坚贞就是符号内容;梅花当然不等于坚贞,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对等性不仅是意指论的,更是形式论的——强调了符号结构系统对意义的生产性: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的符号系统分类框架,让梅花获得了“坚贞”的意义。以往,在秉持狭义形式论符号观的学者看来,绘身纹身、人身装饰、林中起烟、窗户结冰、风信旗摆、周易卦象、象形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等都不是真正的符号,最多属于类符号现象。但从广义符号观出发,它们都具有物质性,能表它意,可以被社会所认识,其形式与内容对等呈现,完全具有符号的属性。中国传统小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广义符号思想”,如对“文”这个字的释义,许慎《说文》:“文:错画也。”即花纹的“纹”。古汉字“文”的另一个常用义是“文字”,《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指的就是文字。而明宋濂则认为(三代)“动作威仪,人皆成文。”(转引自申小龙 2001:4)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夏商周三代的“文”这个字包括了今天的文字、图画、仪式等等一切视觉性的符号,所以古人将包括汉字在内的各种视象性的符号表达统称为“文”,体现了一种广义符号观。
因此,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并不是指单一的语言、文字等。它的研究对象是围绕人类的生命活动所展开的各种意指实践或符号化过程,包括姿势、踪迹、语言、图像、书写、艺术、仪式、实物等各种表意方式。一言蔽之,符号学所处理和思考的对象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符号综合体,需要从“大符号”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
2 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
广义符号观是一种大符号观,它能够容纳异质多元的符号入列,与语象合治问题密切相关。在广义符号家族中,有两类最基本的原型符号:一类是语符,即通常所说的语言符号,包括口语、文字或书写文本以及各种语言替代品如手势、代码等符号;另一类是象符,即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符号,包括了实物符号和各种视觉技术符号。语/象符号是广义符号观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突破了传统上要么以语言的语符号为中心、要么以非语言的象符号为中心的狭义符号观的分治立场。
“语象合治”是我们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提出的一种符号意指方式,体现了一种中性符号观。“中性”或“中和”,在法国符号学家巴特看来意味着二元对立的解除(2010:10-11),拿网络表情包为例,就是图像和语符的中性合治符号,它既不是图像又不是语言,但又具有语符(文字)和象符双重编码性质。表情包是对传统图文分治格局的消解,在传统线性书写的文体中,插入表情包显然不得体,但在网络语言诸如微信体中,空间非线性的、信息浓缩的碎片化句式与表情包彼此融合,相得益彰。因此,表情包乃至更大的符号单位——微信体,都是一个语和象、线性和非线性融合的合治符号。故我们把合治符号定义为: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多重异质符号要素(主要是语象)并相互跨界、相互补充的符号或符号表达单位。
在各种异质符号中,语符号(包括口语、书写语言以及语言的各种补充替代品如盲哑语、公共标识、数字记号等等)和象符号(包括图象、实物、仪式、行为举止之类各种视觉性符号)是广义符号家族中最重要的两翼,因此,“合治观”处理的异质符号关系主要是语符和象符的关系,简称“语象合治”。
2.1 从圣书字来看语象合治
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语象符号的合治现象源远流长。众所周知,西方字母文字的重要源头是古埃及圣书字,它自身就由图像化的象形符号和记音化的辅音符号构成,是一个典型的语图合治的符号系统。如古埃及圣书字既可以用作形符(象)表示“房子”,也可以假借作声符(语)表示双辅音pr。可以看出,圣书字在形符(象)和声符(语)之间变换角色时,有相对明确的外部标记:形符(也叫做“定符”)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它一般置于字符组合的末尾,而声符置于定符之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