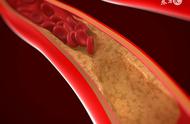一
屋后那颗臭椿树,是什么时候有的,不知道。三个人手拉手合围,还有两只手够不着。树杆伸向天空就像挿在云中,夏天的绿叶铺天挡地,朝天望去,天空都在绿叶下面。晴朗之日,从山那边传来的汽笛声波,使树叶微颤,似乎在说我听到了。
大树后面是一块坟场,竹林包围着大大小小的坟墓,还有板栗树核桃树,春天百花盛开,小孩子们常到坟地去摘杨梅花,摘刺果,到秋天就爬上树杆打板栗打黑桃。板栗、核桃落在草丛中,一个个被俘,装满一筐又一筐。
坟场中间有一座石碑坟,上下结构,下层左右两块石碑,有一人多高,中间有一石柱隔开,石碑中间一排碗大的字,书曰:“故显考XXX老大人之墓,” “故显妣XⅩX老孺人之墓,” 小字分别记载生卒年月,其子孙姓氏名谁。石碑锈迹斑驳,但也看得十分清楚,大小字均是正楷,刻工精细,布局工整。碑铭左右有侧门,八字敞开,上层是坟帽,形状如“山”字,侧门、横粱和坟帽上雕刻着飞禽走兽,长龙翩跹,麒麟、山羊仰头凝望,眼含深情,默默走来,栩栩如生。
臭椿树前面的老屋外墙已伤痕累累,斑驳陆离,茅草下面的墙梁厚重地记录着烟熏的历史。屋里的兄弟二人三两岁时,母亲因病魔撒手人间,离开了他们,父亲因生计时常劳碌在外。冬天的山野,北风呼啸,吹断了臭椿树的枯枝,落在门前厚厚的积雪上,弟兄俩捡起来,燃起堆火,小脸烤得像沙田的红薯,烤干了的鼻涕像红薯皮上的裂缝,赤裸的小屁股、小腿杆贴在地灰上,眼球许久不转动一下,活像草屋里的泥塑。当包谷或黄豆颗粒在火中炸响时,才见四只小手伸向灰中寻找,泥塑才有了生命。
二
没有娘的娃天照应。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兄弟俩已长大成人,老大刘善祥、老二刘善额先后娶了媳妇儿,刘善额的媳妇儿郝明艳能说会道,细腰肥臀,走起路来大屁股左右扭动,很有几分姿色。刘善祥的媳妇儿赵明翠身材苗条话语不多,说起话来且轻声细语,两对夫妇仍在一个锅里吃饭,郝明艳负责做饭,中午,刘善祥的媳妇儿很快吃完了第一碗饭,去厨房添饭,却找不到甑子,心里明白,一定是刘善额把甑子藏起来了,饭没吃饱却气饱了,赵明翠转身走出灶屋,站在桌边,眼睛直射刘善额,目光像颗被点燃的炮竹冒出的的火焰,刘善额不敢对视,赵明翠舀了一碗懒豆腐,三两口扒下肚就离开了。晚上,媳妇儿把中午的事向丈夫刘善祥说了,自然不会有好结果,俩弟兄从此分家了,各自另立门户。
老二刘善额新选了屋场,盖了新房,灶屋后面是房屋,从灶屋的隔门子进,灶屋房屋两不防碍。
刘善额俩夫妇吃苦耐劳,天不亮出坡看不见了才收工,勤爬苦挣,日子也算红火。一年喂两个猪,卖一个*一个,快到年底,刘善额觉得可以出售了。山里人卖个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山上背下河到收购站七八十里路要走一天到黑,为了赶在收购站下班之前到达,刘善额半夜就得出发,带上媳妇儿炒的包谷炮,饿了就䄰上一口,冬天的山里寒风刺骨,背上的猪却把刘善额压得满头大汗,揩汗的麻服子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时不时地拧出一滩水。猪在背上还唉声叹气,它受不了这捆绑,不耐烦地把屎尿撒出来,顺着背篓流在刘善额身上,下坡过河走不尽的羊腸小道,在太阳落山前,刘善额终于到达收购站。
收购站在溪水尽头的岸坡上,溪水尽头成九十度与长江交汇,因江水阻拦,溪水蓄水成湖,碧波荡洋,被两山夹得毕直。岸坡上有供销社,有小饭馆,小饭馆楼上有几个床铺,叫做“旅社,” 这里是山里人通往山外的小码头,油盐布杂也从这里背进大山。
刘善额靠稳背篓,连板带猪一起抱到地上,去找收购员。收购员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要他把猪放到磅秤上,猪在磅秤上不时地蹬弹,称杆也随着上下跳动。
“你不要让猪动啊!”收购员大声吆喝。
刘善额伸手把猪腿摸一摸,猪不动了,收购员将称标一点一点向左扒拉,称杆悬稳。
“一百一十八”。收购员报出斤数。“咧不够称咧!”收购员的话十分严肃。
“干部同志,” 刘善额哀求道:“我在屋的称了的是够称的,只是猪在路上窝几啪粑粑还有好几啪尿,您看,我身上还有呢。”
收购员瞅瞅刘善额,搭拉着脸:“我还没有给你除食呢,不够称不能收。”
刘善额顿时脑壳一蒙,眼睛发黑,像一块石头砸在脑袋上,扑通一声,跪在磅秤前:“干部同志,求你收下吧,我真是没法呀。” 从哽塞的喉咙里挤出来的话,在泪水下面不成句。
收购员坚决执行政策,猪卖不掉,刘善额已没有力气把猪背回来,丟了也实在太可惜。想想把猪喂这么大,哪那么容易,起早贪黑,不论天晴下雨去打猪草,一身泥一身汗,年把时间才把猪喂这么大,怎舍得丟呢!就是累死累活也要把猪背回去,转念又想,经过两天的折腾,这猪也伤了元气,只怕也是虾喂,刘善额心一狠,两打杵就把猪头打蒙了,决心把死猪背回去刮肉。
背到半山坡,刘善额转身向下面望去,溪水与长江的交汇,形似一颗钉子扎在自己心里。
山里人说上坡容易下坡难,刘善额背着死猪,一路都是上坡,累得喘不过气,到家时已是第二天深夜,精疲力尽,躺倒床上,活像一个死猪。
刘善祥帮哥哥去卖猪,并没有去收购站,捆好猪,刘善额只身背起猪,半夜离家出发走了。赵明翠见丈夫深夜未回家,就猜想在弟媳家留宿,弟不在家,兄嫂在一起还能有什么好事吗?于是点起火把,怒气冲冲的来到刘善额家,踢开大门直奔房屋,刘善祥早已从灶屋门溜走了。妯娌俩互吐恶言,赵明翠没有抓到丈夫,也就没头没脑的回家了。
刘善额背着活猪出去,背着死猪回来,俩口子撕心裂肺的哭一场,心里像装个疙瘩,大半年不舒服,祸不单行,刘善额拉着耕牛去沟里喝水,山高路滑,牛失前踢,沿着七八十度的山坡,滚到小河边才停下来,把正在灌浆的包谷滾倒三百多米,刘善额急忙跑到小河边,只见耕牛已紧闭双眼,刘善额扑到牛肚上泪如泉涌:“我的牛啊……呜……呜……”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眼泪和鼻涕把牛毛粘合一大片。
三
这年冬天,刘善额参了军,走后第二年,郝明艳就到邻村的一个男人家里,生活在一起。刘善额当了三年兵,学了文化,开了眼界,长了见识,退伍回乡,尽显军人气质,身边的人都刮目相看。郝明艳又回到刘善额身边,不到半年,郝明艳生下一男孩,取名刘相青。刘善额得了儿子,又当上了大队支部*,双喜临门,进进出出披着一件军大衣,走起路来轻风气爽,黄泥巴色的脸上盖不住心里的得意。郝明翠被选为大队妇女主任,从县里开会回来也是精神气爽,头上包着花毛巾,毛巾下面露出一绺头发搭在额上,和娘娘们分享在县里的见闻:
“那个床摆得整整齐齐的,铺盖、床单、枕头白得像米饭,都铺得好好的,枕头一绺线的整齐”。
说起话来,嘴巴皮儿像含苞待放地花骨朵儿外瓣,似包未包。
一夜雪飘,足有一尺厚。刘善祥背着板铁,煤炭,还有豆食炒腊肉,去铁匠铺请师傅打挖锄。
刘善祥除了在队里劳动外,下雨天就做些木工活,有人家请上门的,或是在家做些桌椅板凳,背出去卖,有点小收入,贴补家用。刘善额很是不舒服,多次在群众中扬言“我几时是要把刘善祥的斧头给没收塌的!” 刘善额在大会小会上宣传割资本主义尾巴,屋前屋后不能种瓜种豆,尾巴被割的干干净净,每到春季就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等国家供应。国家供应也不是能满足的,分个三、五斤包谷,放在石磨子上推,一家大小就等着面出来打糊嘟,还不能吃光糊嘟,野果野菜充饥,熬等新粮。秋天收了粮食,必须搀和野菜,黄豆叶是最佳搀和物,把黄豆叶搁在煤炭火上炕,炕枯了用手揉搓成面,用水浸泡,滤凈,与包谷面搅拌均匀,上甑蒸熟,盛碗即食。黄豆叶即使清洗得再干净,蒸出来的饭仍是黑黢黢的。刘善额到水井淘洗黄豆叶,从刘善祥家经过,遇上赵明翠端一碗金黄的光饭,不说话,两眼皮之间眯条缝,盯着那碗光饭,木讷着脸,快步朝熟悉的方向走去。
刘善祥听说大公鸡香烟在夷城比本地卖得贵,就想贩点烟赚点差价,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刘善祥有个主意,他把六条烟卷在铺盖里面,上船时,剪票员觉得被子异常,于是拦截检查,当即送往县里关押。公安局觉得就是几条烟,而且没有出手,就通知区里来人领回去,按投机倒把分子游街,乡里没有街道,就游公路。队里人听说刘善祥搞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消息很快传到刘善祥家里,儿子刘相学随即出门去看他爹。
羁押人员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高帽子是用纸糊的,成圆锥状,足有两尺多高,用绳索把双手捆在背后,脖子下面挂一个大牌子,上书“投机倒把分子刘善祥,” 后面几十人敲着锣,一遍又一遍高呼:“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刘善祥!” 游到公社处,众人解散,由大队干部把刘善祥领回家。
刘善祥睁开眼皮在人群中瞄到儿子刘相学,父子目光相遇,刘善祥立即收回目光低头不语,刘相学心里像压块石头,闷闷不乐,无话可说。
第二天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投机倒把分子刘善祥。大队*刘善额来到群众前面,高声喊道:“不要说话啦……不要说话啦,咧时开会。……今儿批判刘善祥。嗯……刘善祥不认真学习*语录,资本主义思想作怪,想搞投机倒把……嗯……” 振振有词,于是话锋一转,问道:“刘善祥,你带了*语录没有?” 刘善祥摸摸衣服荷包道:“没有。” “你看,你就是没有把学习*语录放在心上,怎么不会犯错误呢!……” 刘善额估计刘善祥没有带*语录,故意找茬,让刘善祥在群众面前出洋相。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个个严肃紧张,低头不语,眉毛紧锁。
刘善额开完批判大会,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刘善祥门口的包谷杆垛子在燃烧,跑近察看,是几个小娃子玩火,引燃了枯燥的包谷杆,火势越烧越大,小娃子们束手无策急得乱喊,若起风就会火烧茅草屋顶。刘善额把屋里所有的水提出来泼向火堆,明火熄灭了,青烟漫过屋顶,一场火灾因批判会而避免。
四
刘善祥的子女并没有因批判大会而疏远刘善额,大儿子刘相学把个“幺爹,幺爹”叫得甜蜜蜜的,刘善额也是笑脸应答。这年秋天,区里开办一所高中学校,在各公社选抜学生进入高中预备班,刘相学是其中之一。 在校住宿,一星期回家一次,上学时母亲赵明翠总是给他准备一瓶咸菜,冬天刘向学的手背生冻疮,肿得发亮,他从不叫苦,学习成绩优异,老师也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讲。两年高中很快就结束了,刘相学回到生产队里劳动。
批林批孔运动在乡下开展得如火如荼,深更半夜,刘善祥家的狗汪汪地叫起来,只听得刘善额在门外喊道:“相学……相学……,”刘相学在床上应道:“哦,幺爹”,“你明天去公社开会,做好发言的准备。”刘相学应答刘善额的话:“好。”
五
冬季征兵开始了,刘相青又报了名,去年刘相青本来是考取了的,到了县里后,接兵部队发现刘相青不够年龄,就退了回来。刘相青希望今年不要拉下,经过体检、政审,刘相青如愿以偿。
公社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公社领导讲话后由各大队代表发言,主持人宣布:现在请金凤大队的刘相学同志发言。刘相学说:林彪嘴上喊*万岁,背后却要夺权,这就是两面三刀,我老爹(爷爷)就遇到这样的人,今年春上,一个陌生人来到老爹屋里说自己姓刘,叫刘啟保。老爹一听是自家人,就做饭招待,还留宿在家,陌生人走后,老爹发现抽屉的五十块钱不在了,不用想一定是陌生人拿走了,于是,出门去追。刘相学联系实际,讲述生动,与会的人听得明白,得到领导认同,也给*刘善额争了面子。
秋天,包谷成熟了,社员群众每天早早下地抢收,刘相学和表哥等青年背着大篾框负责收集。表哥问:“刘相学,你什么时候趷双河教书”?
“到哪里教书?我没有听说。”刘相学很惊喜。
“刘*说的”。表哥答。
“没有人跟我说”。刘相学希望能有这一天。
“你什么时候去?我给你背箱子”。表哥由衷的高兴。
秋天还未结束,冬天就来了,雨雪时不时地飘在空中。刘相学在去公社的路上遇到高中同学陈再先,陈再先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走?”
刘相学摸不着头脑,“到哪去?什么时候走?”
“去上大学哇!”
“我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我哥说的。” 陈再先的话里充满了羡慕。
刘相学知道陈再先的姐夫哥在公社里当干部,刘相学觉得这话有准,转念又想到,自己连一床像样的铺盖都没有,怎么去读大学?!尽管穷,但听陈再先的口气,似乎是真的,刘相学的心里像喝了蜂蜜,甜滋滋的,像开了花的包谷粒在滚烫的沙锅里,默默地等着,天天盼望对面山路上出现一个人来通知他。
十一月中旬,今年的征兵又开始了,刘相学报了名,得到刘善额*的批准。体检、审查通过,十二月下旬离家入伍。
六
农村改革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刘善额少了很多公务活动,多了做自家农活的时间。经常向刘善祥借农具,一会儿要榔扒子,一会儿要晒席,一会儿要薅锄,一会儿要背篓,时间长了,刘善祥很不耐烦,碍于兄弟情面,不情愿的给了他,背后只是闷闷的出口长气。
刘善额的承包地与刘善祥家相邻,刘善祥家的鸡就常跑到刘善额的地里吃黄豆,刘善额很不高兴,几次跟刘善祥说:“哥哥,你把鸡子看好,我的黄豆可是比你的鸡贵多哒。” 这还不算什么,刘善额最心烦的是,地边上的一颗华树遮住了太阳,刘善额多次要求刘善祥“砍塌,” 刘善祥不为所动,刘善额就自己挥刀砍树了,刘善祥听到声音,见状,恼羞成怒,随即拿起一根木棒,吆喝道:“刘善额,你今儿敢砍,我给你把膀子打断塌,这树是去年、前年才长的啊,几十几年啦,你的田在哪里?” 刘善额自觉理亏,丟下刀就跑了。刘善祥把刀捡回来,放了两天,又给刘善额送回去了。
刘相青退伍后,刘善额就特别关心刘相学在部队的情况,常常夜里站在刘善祥门口偷听有什么消息,刘善祥早上起来,看见门口道场几组深深的水靴印,就晓得是刘善额的那双深桶胶鞋底,估计站了很长时间。
刘相学在部队收到刘善额的来信,信中说“你母亲有病,身体不好,弟妹小,家里现在很困难,回来吧。”
刘相学回家探亲,跟父亲说“我去看看幺爹幺妈。” 刘善祥说“好。” 刘善学提着酒、白糖到了刘善额家里,刘善额见相学穿一双黑皮鞋,搭拉着眼皮,从牙逢里挤出来几个字:“咧孩(鞋)子在咧里阔不行吧”。
刘相学每次回家都去看望刘善额,冬月十四是刘善额的生日,火垅里坐满了客人,郝明艳在灶屋的弄饭,刘善额拿着一根大脑壳长烟杆,“拔啦……拔啦……”几口,与众客人围坐火垅拉家常,几根碗粗的梨柴烧得冒青烟,坐在顺风的人熏得睁不开眼。刘善额吐出一口旱烟,问相学:“你有小孩儿了吗?” “叫什么名字啊?” 刘相学答:“叫陈玲,” 刘善额立马仰起头,朝灶屋喊道:“没有姓刘哇!” 看起来像是告诉在灶屋的郝明艳,火垅屋的客人被刘善额这一声无头无尾的吆喝,弄得莫名其妙。刘善额的小女儿相婷倒是听得明白,说:“现在姑娘跟妈姓的也多”。
刘善额的小女儿相婷,要出嫁了,婆家在山那边,请刘善祥来家打嫁妆,做一个大衣柜。出嫁那天,两人抬着衣柜,经过一条小河,“嘣”的一声,衣柜的一只脚断了,送亲的人面面相觑,都感到兆头不好,刘善额说是刘善祥没有做好,心里闷闷不乐。果真,相婷出嫁的第二年因车祸死亡,刘善额认为与衣柜断腿有关系,更是仇恨刘善祥。
刘善额与刘善祥两弟兄恩怨越结越深,不断在田地交界处找茬,不是你占我一点就是我占你一点。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刘善额上山割草,割着割着就割到刘善祥田里了,刘善祥带着背篓打杵来到田里,见刘善额把自己田里的草割了,气不打一处来,“刘善额!你割谁的草,真是越搞越没明堂哒!” 抄起刘善额的背篓就砸,刘善额也不示弱,伸手去夺刘善祥的背篓,互吐恶语,那脏话早已不在一个妈的份上,两兄弟扭打在一起,滾下土坎。
刘善额提着破背篓回家,郝明艳见状问道:“你的背篓怎么成弄个家货啦?“刘善祥给我砸的。” 刘善额把割草的事细数一遍。郝明艳听了,像个法官道:“你们挒两弟兄还不如五家外百姓,挒是晒起!你割草就好好割你的草,你把人家的多割一把就发财啦!”
七
刘善额割草挨打后,心情郁闷,茶饭不香。肚子总觉得闷胀,到了冬天,手摸肚皮,似有疙瘩,越来越感觉腿乏力,脸发黄,饭量减少。求诊,老乡医摸摸左腕脉,又摸摸右腕脉,道:“看看舍头。” 刘善额伸出舍头,老乡医端祥道:“肝火重啊。” “我给你开两副药,你吃完后,再来看看。”
病来如山倒,中药不见效,到医院检查,肝上包块有八公分大,刘善额同意做手术,医生拉开肚皮,见肝脏像稀粥,已不能切除,随即缝合。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刘善额向刘相青交代后事,有哪些人情往来,有哪些经济账目,死后把他埋在老坟场(臭椿树后面)。回忆着一生的得意与忧伤,带着一生的希望与嫉妒,伴着一生的幸福与辛酸,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臭春树后面的老坟场在刘善祥的林山里,刘善祥不同意把刘善额埋在那里,任凭别人做工作,刘善祥就是不同意,两兄弟的爹看不过去,来给刘善祥做工作,刘善祥就是转不过来弯,逢人便说“他们把老天牌搬出来压我,就能把我压服?” 每每想到刘善额生前的烦心事,咽喉如哽,不想在他死后还天天挂在眼皮下。
刘善额的舅老官,看他们两兄弟不和,刘善祥不让刘善额葬在自己林山里,就给刘善额家人出主意,说刘善额是被刘善祥打死的,要他们去法院告刘善祥,刘善额家人觉得打架与死没有关系,没有听他舅老官的教唆。
八
刘相学在外,不知道父亲两兄弟为割草打架的事,回来时也没有人向他说起这事,毕竟不光彩。但以前那些疙疙瘩瘩他是知道的,他觉得弟兄之间闹成这样很不该,尽管这样,每次回家,都要去看看长辈,刘善额去世后,刘相学只要回家就去看幺妈,一斤糖两斤面,不在东西多少,总是一份亲情,日长月久,幺妈也很受感动,时常想起刘善额在世时,两弟兄的矛盾,郝明艳对刘相学说:“看你们现在这么好,当初他们那又是何必呢。” 郝明艳把自己种的嫩包谷送给刘相学,说:“这嫩包谷推浆,煎粑粑蛮好吃。” 刘相学每次走的时候,郝明艳又送来葵花籽、腊肉等,两家往日的仇恨烟消云散,和和气气有说不完的话。
刘相青起新屋,刘善祥负责加工门窗,快架横粱时,后墙出现歪斜,刘善祥天天在这儿帮助加固,砌保墙,立支架,有时忙到深夜,在昏暗地灯光照耀下,覆盖在脸上的汗 水,像雨水沁透在青涩的石板上,显得格外苍老,刘相青非常受感动,去去来来“大爹……大爹……”叫得也是亲热。
春节前,刘相青的新屋砌好了,搬进新居,亲戚朋友前来庆贺,刘相青请大爹坐上席,特意斟满一杯酒,走到刘善祥旁边,“我敬大爹。” 刘善祥笑眯眯的端起酒杯,两叔侄仰头一大口,酒从嘴里流到肚里,刘善祥感觉热乎乎的,全然不知烈酒的辛辣味。桌上火锅里的腊蹄“咕嘟……咕嘟……”的跳着,热汽升腾,吃饭的人个个喜笑颜开。
岁月不饶人,刘善祥一天天变老,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儿子刘相学把他接到夷城生活,到夷城的第四年,刘善祥病了,腿无力走不动路,脸发黄,肚子发胀隐隐做痛,到医院检查,竟然与刘善额患同样的病,医生对刘相学说“好好静养吧,他想吃什么就弄什么给他吃,估计能维持半年。”
刘相青得知大爹病了,给他送来腊肉、鸡蛋、包谷面、洋芋淀粉等乡味。刘善祥说,你这么远来看我,领当不起,还拿这么多东西,路上不方便啊。刘相青说,“看嗨儿大爹是应该的。” 两叔侄聊起家常,“现在山里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出去了,老年人一个个走了,今年就又走了一个,以后山里恐怕是没人了,现在山上树多了,林子密了,野猪常出来毁包谷。”
第二天早上刘相学送刘相青上车,刘相学说:“你大爹拖不了蛮长时间,到时候还是想把他送回老家。” 刘相青说:“行,到时候我们来帮忙。”
刘善祥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每天只能进少量流汁。老家的娃儿朋友张叔来看他,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我们咧些老家伙都不行哒。”
“你身体还硬扎,我咧,在数天天。”刘善祥接着又说:“连*弄么伟大的人都要走类条路,阎王爷要你死,那是拦不住的。”
张叔问:“你给自己选好屋场没有?”
“我还是想到臭椿树后头的老坟场。”刘善祥停了一会儿,又说:“唉,这么远,随他们怎么弄。”
张叔说:“底下要烧的,你还是上趷吧。”
刘善祥说:“死了管他烧不烧,随便朗哈搞起都行。”
刘相学回老家找刘相青商量给老爸办后事,来到臭椿树后面的老坟场,看好一个地方,刘相青说:“现在农村都是要找导师看的,刘兴旺的妈死了放了七天才埋。”
刘相学认为这都是迷信,但想到现在山乡都这样信,如果没有导师看,恐帮忙挖墓地的人心有忌惮。于是请来阴阳师。阴阳师放好罗盘,望望远处又看看近处,目測方位,坐下来,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张白纸,不知写些什么,又掏出图章,掰开印盒,用力按上印泥,图盖在白纸上。这严肃认真的态度,很像公务员下乡办公一般。然后将盖有图章的“公文”燃烧成灰,装进一个玻璃瓶,在候用墓地的中间挖一小坑,把玻璃瓶放进去,掩盖起来。离开时,嘱咐刘相学,“到时候打个电话,我把日期看哈,看需要放几天。”
刘相学和刘相青商量说:“人一不行,我就告诉你,你帮我把人找好,把坑挖好,上来就入棺砌墓,不在上面停留。” 刘相青应允。
刘相青十天半月给刘相学打一次电话,询问大爹的病情。
十一月十八下午五点,刘善祥停止了呼吸,刘相青即刻邀来众人搭起灵堂,放置灵柩。购买烟酒茶,谁弄柴,谁烧水,一一安排妥当。刘相青的媳妇儿保莲领头做饭。
刘相学等众子孙连夜把遗体送回老家,各辆车头挂着大白花,一路顺利抵达。
大清早,刘相青领来八大金刚,将遗体入棺,刘相学一一跪谢。四人掘墓,四人运石,搜尽周围石头还不够,刘相青领四人把自己责任田的培坎石拆掉,拉来砌坟。保莲送来一大蒸锅米饭和各式菜肴,有腊蹄、蒸肉、豆腐、豆芽、肉炒土豆片、酸菜炒肉、魔芋豆腐、小炒包白。热饭、热菜、热茶温暖着送葬的人们。保莲默默走到灵前,烧纸磕头,泪水沁溢,起身到一边拭泪。
拢好坟墓,孝子焚纸磕头,鞭炮齐鸣,响彻山谷。苍翠的臭椿树傲然以立,枝叶在爆竹声中随风摇曳,见证着山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完
后 记
二十二日早晨,还未起床,电话响了,显示是庆雄的来电,但对方传来的却是庆雄的姑娘玉华的声音:“大爹,爸爸给您说话。” “我给你商量个事……” 声音很小,后面就不明白在说什么,我顿时感到不祥。还是玉华讲,“爸爸要到您们那个老屋场去。” 我问怎么回事,玉华说:“病了,肝癌。今天清晨,把我们叫到床前,交待了后事,最后要我给大爹打电话。” 我感到十分突然,除夕时我给庆雄打过电话,正月末我又给庆雄打了电话,正值武汉闹新冠肺炎,他问我们怎么样?声音洪亮,听不出异常,他也没有告诉病情。仅一个月后便传来噩耗。去年十一月母亲在宜昌病逝,送回老家安葬,全靠他张罗。没想到仅成了永别之时,—— 生命仅如此随便。不禁想起父辈兄弟在世时有些疙疙瘩瘩,到我们这一辈亲密无间,心情难以平覆,于是添油加醋写下这些无聊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