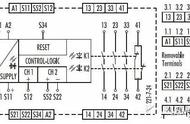我给宋远霖当了四年情人。我死那天,他正和别人举行婚礼。「大喜的日子都不来,怎么,不想看见我娶别人?」「还是说你觉得,耍小性子我就会妥协?」「路杨,我最后说一次,今天你不出现,这辈子都别想回来。」后来,他跪在我的墓前,亲手为我刻上墓志铭。「吾妻路杨。生于杨花落尽之日,死在我最爱她那年。」那是他第一次承认他爱我。可那又怎样呢?我已经死了。
「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你难道不高兴吗?」婚礼现场,我飘在宋远霖身边。他听不见我的话,只是沉着脸,让助理不厌其烦地拨打我的号码。两遍无人接听。第三遍直接关了机。10 分钟后,他不耐烦了。拿出手机给我发几条短信,言语里满是戏谑和威胁:「大喜的日子都不来,怎么,不想看见我娶别人?」「还是说你觉得,耍个性子我就会妥协?」「路杨,我最后说一次。今天你不出现,这辈子都别想回来。」和我说话时,他总是一副大权在握、生*予夺的模样。可惜,如今他火气再大,也没法发泄在我身上了。因为几个小时前,我死了。「宋总,婚礼快开始了,您该去换衣服了。」袁秘书抱着平板提醒他,板正的身条不卑不亢。闻言,宋远霖的手在屏幕上停住,锋利的眉皱到了一处。停了几秒,才把手机丢给袁秘书:「继续打,打到她接为止。」
不知道为什么,我离不开宋远霖。或者说,灵魂状态的我无法离他三步以上。我被迫跟着他上了台。婚礼现场布置成了海洋主题,巨大的蓝鲸悬浮在空中,和梦里一样漂亮。只不过婚礼的主角不是我,是季晴。一年前,宋远霖让我去公司送午饭,指明了要吃盐焗虾。我从早晨折腾到中午,挑虾线的时候还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可是一进办公室,袁秘书就把我拦住了。那时候他也刚进公司,第一次处理那样的事情,还没什么经验。「宋总在开会,麻烦路小姐在外面等一下。」相当拙劣的谎言。话音未落,门缝里就溢出几缕可疑的声音。袁秘书一下红了脸,眼神闪烁,似乎在思考怎么说才能让我好受点。我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没关系,我在外面等就好了。」结束后宋远霖搂着一个娇俏的姑娘走出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季晴。皮肤很白,眼睛很大,高马尾有些凌乱,但青春靓丽分毫不减。尽管我和她都不是宋远霖万花丛中唯一的娇花,但纵观这人过往的口味,没有这样清纯的学生妹。所以当宋远霖跟我说他要和季晴结婚时,我是有些惊讶的。好在我很快就平复了情绪,当天晚上就收拾好了所有东西。说是收拾,也只有一个行李箱而已。出门前,他坐在阳台上,修长指尖缠绕着迷蒙的雾气,笑得有些讥讽。「这就受不了了?」他一步步逼近我,浓重的烟草味道侵袭着感官,让我有些想吐。「不好意思啊宋总,我不睡有家室的。」如果有镜子,我一定笑得很难看。宋远霖的笑僵在脸上,低头掐住我的下巴。「那我是不是该夸你有职业道德啊?」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个花钱买来的女人。不睡有家室的,听上去像句可笑的说辞。「还是说,你还想着嫁给我?」我低下头。我想过的。但也仅仅是……想过。可连这个,我也不敢承认。见我久久不答,宋远霖略带嘲讽地拍了拍我的脸,微凉的语调直刺人心。「路杨,问问自己,你配吗?」
宋远霖以前不是这样的。青梅竹马十载。他会在别的女生控诉他不给自己讲题,只给我讲时,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别人。也会在我来姨妈弄脏裤子,被别人嘲笑时,一拳砸在那个嘴欠的男生脸上。可现在,我已经想不起那个处处维护我的宋远霖长什么样子了。他对我,只有绵延不绝的恨意。「路杨,你为什么不和*一起去死啊?」这是他后来对我说过最多的话。高三那年,学校突然停电。我和宋远霖提前回家,正好撞见我妈和他爸不堪入目的场景。单身寡妇勾引有妇之夫,谈资很快在街坊四邻传开。宋远霖爸妈大吵一架。可就在他们去民政局离婚的路上,一辆大货车突然侧翻。他们甚至没能撑到救护车赶来,就撒手人寰了。葬礼那天,我红着眼睛在宋远霖家门口等了一夜。憔悴不堪的他从熹微的天光里走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杨杨,我没有爸妈了,你开心吗?」他抱着我,修长的手指在我双臂留下一道道红痕。肩上偶尔有泪水滴落。我忍着疼,嗫嚅着嘴唇,一遍遍向他道歉。可最后,宋远霖也只是摇摇头,丢下一句泪眼婆娑的「我恨你」。他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得彻彻底底,我妈也因为受不了打击中风瘫痪。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七年后,在我为医药费发愁时,宋远霖会再次出现,轻描淡写地帮我补齐了住院费。「路杨,她得活着,亲眼看你是怎么受苦的。」也许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结局就注定了是个悲剧。
只不过,宋远霖折磨我的手段不怎么高明,无非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咖啡泡个八遍才肯喝,洗澡水低了一度就要发脾气。一旦我表现出一点不满,晚上就别想睡了。原本我就皮肤敏感,稍稍用力就会捏出一片瘀痕。宋远霖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怜惜我,往往是怎么尽兴怎么来。有次我病了,去医院挂了两天吊瓶,回来时刚好遇见一位学长。他把我送到家门口,又跟我随口聊了两句。刚好宋远霖出差回来看见这一幕。「我还发着烧,你能不能让我休息会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生气,只幻想他可以念着多年交情,放过我一次。「还能和别人说说笑笑,应该也不需要休息。」「而且 39 度,没试过,想试试。」禽兽。我骂他,故意跟他较劲,眼泪却在无声时滑落。宋远霖将我的脸掰回来,拇指轻轻擦过被我咬出血的唇瓣。「别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大不了明天去刷我的卡泄愤。」「反正用身体换取利益,是你们家一直擅长的。」我怒视着宋远霖。戳到我的痛处却让他异常快乐,脸上的笑都带了几分狰狞的快意。「不然你以为,我爸对你们家的照顾都是无缘无故的吗?」我的力气一下就卸了下去。因为在这一点上,我根本无从反驳。隔三差五的糖果,逢年过节的硬货。早已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成了我这辈子想起来就会受之有愧的东西。结束后我又烧了三天,一个人在客房里自力更生。而一墙之隔的宋远霖,只在第一天扔过来一盒退烧药。他说:「路杨,别死在我家里,我嫌晦气。」
会场里播放着记录新郎新娘相爱过程的动画。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马虎的姑娘撞到了正在发呆的路人。姑娘匆忙道歉,捡起男人掉落的手机,对方却在她转头的瞬间狠狠愣在当场。没过多久,他们相爱了。他带她去过长满薰衣草的普罗旺斯,在圣雷米小镇的钟楼前拥抱接吻。宾客们为他们的爱情鼓掌喝彩,我却被这一幕深深刺痛。这就是宋远霖想让我看到的吧。不得不承认,他总是知道怎么折磨我最疼。高中时,同桌问我将来想在哪里结婚。那时候我被偶像剧洗脑,脱口而出想去普罗旺斯。结果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宋远霖耳朵里,放学后他把我堵在器材室,一本正经地讨论这事。「唔,普罗旺斯么,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对薰衣草的花粉过敏,小路同学记得提前给我买药。」我像热锅上的虾子一样红了脸,小声嘟囔:「我又没有要嫁给你。」「那你还想嫁给谁?」少年板着脸,把班上的男生数了个遍。我又哪里敢承认,随便说了个明星的名字。宋远霖牙都咬碎了,回去后到处打听那人是谁。最后真相大白,气得三天没理我。我在无人处偷笑。可从那之后,我做的每个关于普罗旺斯的梦,都有穿着白西装的宋远霖。……我转着圈,试图找到能离他最远的地方。然后就飘到了程铭身边。他是宋远霖的伴郎,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时他主动放弃了年薪五百万的 offer,和宋远霖一起休学创业。如果没有他,远霖科技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婚礼进行到一半,程铭怼了怼另一个伴郎老凌,小声说道:「卧槽老凌,你有没有觉得新娘有个角度特别像路杨。」老凌也是宋远霖扩张商业版图的功臣,不过我们只见过两次,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咂咂嘴,点头道:「你还别说,真有点像。」程铭叹了口气,悠长的目光似在追忆当年。「老凌,你是不知道他俩高中时多好。有一年路杨生日,霖哥骑了五公里车,就为了买一个限量版的蛋糕给她庆祝生日。我真不明白,他俩怎么就走到这步了。」是啊,我也不明白。我和宋远霖,怎么就走到这步了。
婚礼结束后,宋远霖带着季晴回了新房。我无意听人墙角,却又避无可避。好在他并没有打算做些什么,心不在焉地安抚了下季晴,就走向了书房。「有点事要处理,你先睡吧。」新婚之夜独守空房,季晴当然不乐意。噘着嘴把高跟鞋一蹬,「宋远霖,我生气了。」这大概就是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吧。我从来不敢这样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季晴生气了宋远霖会哄。而我生气了,没有人会理。我这辈子呢,孑然一身来,孑然一身走。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消失,也不会有人记得我是谁。真奇怪,人都死了,心里某个地方还有冷风呼啸。果然,宋远霖又耐着性子哄了季晴两句。他本就长得不差,稍稍说几句软话,小姑娘就心猿意马了。来到书房时天已经很晚了。看见没有消息回复的聊天框,宋远霖沉下了脸。但他并不是在担心我的失联。只是在恼怒,豢养的金丝雀竟敢这样忤逆他。这一晚,我毫无睡意。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着不远处端坐的宋远霖,恨不得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但我大概没什么做鬼的天分,手指触到他的身体,直接穿了过去。宋远霖也没有睡好,靠在书房的躺椅上沉思了半宿。天亮时从抽屉里拿出药片,没喝水直接吞了下去。我偷偷查过,那是一种三环类药物。主要作用是抗抑郁。程铭说过,双亲同时过世对宋远霖的打击很大。他在国外那几年,过得并没有表面这般光鲜亮丽。只是他习惯了什么都不说,放任绝望和焦躁在心里攻城拔寨。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我。有一次吵架后,我在手腕上割了一道极深的伤口,决然地望着冰冷的天花板,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还你一条命,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吧。」电话那头只有冷笑传来:「你敢死,*也不用活了。」他总爱这样威胁我。思绪拽回。我拧了把湿淋淋的衣服,抬头时刚好发现熹微的晨光从窗缝中溜进来。天,居然亮了。
我跟在宋远霖身后晃了两天。第三天,江海市公安厅找到了我的尸体。宋远霖还在开会,电话是袁秘书接的。「宋先生您好,我们在滨河公园打捞到一具尸体,进行 DNA 比对后,确认死者是一名叫作路杨的年轻女性。我们恢复了她手机里的信息,看到您是死者的紧急联系人。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尽快通知家属来认领尸体。」当着一众甲方,袁秘书直接冲了进来。宋远霖浓眉蹙起,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压力:「懂不懂规矩,滚出去!」袁秘书满头大汗,难得没有听老板的话。「宋总,路小姐出事了。」「啪。」签字笔掉在地上,在鸦雀无声的会议室里显得尤为突兀。我扭头看向宋远霖。只见他微微愣了一下,半晌才自顾自捡起笔,淡淡说了句「抱歉」。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继续开起了会。割腕那次,我问过宋远霖:「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