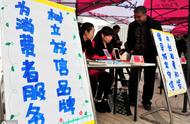除了在收音机里听到“晴朗的一天”,我最早是在1979年买到一张中唱出的《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张权(女高音)演唱》33转密纹胶木听到蝴蝶夫人,里面有张权演唱的二首咏叹调《巧巧桑的婚礼行进》和《晴朗的一天》。说到张权,应该多说二句。张权是中国最早的女高音,黄源洛作曲的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抗日题材,1942年首演是张权出演女主角秋子。她1949年赴美国纽约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获得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女高音和歌剧女高音三个证书,能同时获得这三个证书说明她擅长多种唱法。她可以唱抒情女高音,也可以唱花腔,我曾听过她唱的花腔《小鸟》。她1951年就从美国回到新中国,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中国演出的第一部意大利歌剧《茶花女》,张权就是唱薇奥列塔的A角,演出一百多场,轰动全国,我的母亲当年听过现场。张权把《茶花女》全部译成了中文,而且把她自己演唱的所有外国歌曲、歌剧的歌词都翻译成中文,真正做到了向中国听众介绍外国音乐。但是1958年首演《蝴蝶夫人》的时候,张权没有赶上。上面那张唱片里巧巧桑的二段唱是张权1964年的录音,黎国荃指挥中央歌剧院乐队。这位黎国荃还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访问中国时的乐队指挥。张权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过很长时间,差不多有十六七年,她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回到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歌剧系主任。张权不仅唱西方歌剧和歌曲,而且也唱中国歌曲,极力推广中国民族音乐。她的吐字非常清晰,声音甜美、明亮,感情非常充沛,激情四射,很有卡拉斯的风格。她唱歌即使是清唱,也是充满感情,而且因为她唱中文,我们没有理解上的障碍,听起来就更感人。张权还是中国第一位担任国际声乐比赛评委的,那是1981年在巴西里约声乐比赛,中国歌手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去比赛,好像成绩不是很好。2015年,中唱出了一套二张CD,《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张权演唱歌曲集》,这套CD在2017年获得金唱片奖。由于她在中国美声女高音领域的极高声誉,大家都尊称她张权先生。
1985年,我在一个工厂工作,有一位同事的父亲是中央歌剧院的导演。那一年歌剧院重排《蝴蝶夫人》,我这位同事拿来几张票,我们去天桥剧场看了一场改革开放后首次演出的西方歌剧。我记得平克尔顿是刘维维,巧巧桑是陈素娥。当时,这两位还都是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上来就唱大戏,也是很不错的。那时的刘维维已经小有名气,比陈素娥名气大。后来陈素娥去了意大利,曾经和小泽征尔合作唱巧巧桑,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蝴蝶夫人“。过去都是西方人高头大马来唱小巧玲珑的巧巧桑,形象上就差了不少,当然比不了东方人。张权当年基本上没有出国演出,其实张权的声音比现在这些年轻的女高音都要甜美,但是现在新一代女高音的技巧是好多了。
我手上现在有一套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帕瓦罗蒂和弗芮妮演唱的全剧和选段(黑胶)版本,DECCA1974年;

一套卡拉扬指挥斯卡拉剧院,卡拉斯和盖达演唱的全剧,EMI1955年;

埃莱德指挥圣契西利亚乐团,苔巴尔迪和坎波拉演唱的全剧,DECCA1951年。

这些版本里,录音最好的要数卡拉扬/帕瓦罗蒂/弗芮妮版,DECCA的歌剧录音效果是最好的。要说最好的巧巧桑,那肯定是卡拉斯!最有激情的平克尔顿是帕瓦罗蒂,第一幕里的爱情二重唱里,他的唱腔催人泪下。《蝴蝶夫人》对女高音要求很高,那就是第一幕里《巧巧桑的婚礼行进》最后一句的高音F,就是小字三组的f。卡拉斯的这个音几近完美,弗芮妮的这个音的音量小了一半,苔巴尔迪把这个音躲了,张权的这个音是卡拉斯的四分之一长度,陈素娥好像也是躲了这个音。一般的抒情或者戏剧女高音唱这个长度的高音F非常费劲,像弗芮妮那样能唱出来就不错了。只有那些有花腔功底的戏剧女高音才能把这个音唱圆满了,像卡拉斯这样的可以作为样板了。张权也是因为有花腔功底,才能准确地唱出这个高音F。要说这位普契尼还就是喜欢玩悬的,前面一部《波西米亚人》给男生来了一个高音C,这部《蝴蝶夫人》又给女生来了一个高音F。《波西米亚人》里“冰凉的小手”最高潮也是一个三度级进,然后飚到高音C。我听过的最古老的录音是新西兰女高音弗朗西斯·阿尔达(Frances Alda)唱的“巧巧桑的婚礼行进”,1913年录音。她唱的那个高音F也是非常精彩,既轻松又飘逸,那个时候的阿尔达在大都会歌剧院是卡鲁索的搭档。
总之,我觉得《蝴蝶夫人》是最美的意大利歌剧,也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歌剧。
(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