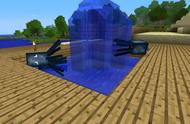《鱿鱼游戏》剧照。
游戏测试人性:
在虚拟世界里学会思考道德、警惕邪恶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只需换一个视角便能发现,身为《鱿鱼游戏》观众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这场生存游戏的参与者。“希望看到更残忍的厮*”、“两个只能活一个,迫切想知道那对夫妻档会怎么做”,这些都是观剧时的常见心态。创作者利用了这种心态折射的幽暗,令观众照见自己人性中的局限。
也许《鱿鱼游戏》还只是看破不说破,名导迈克尔·哈内克的《趣味游戏》则更直白地解释了上述这点。打破第四面墙的哈内克不断挑衅观众,让滥施暴力的凶手直接转过头来和观众对话,并通过任意改变剧情走向、几乎是嘲讽式地迫使观众承认自己对这种(尽管只存在于画面上的)暴力也是认可的,至少是欲拒还迎的。

《趣味游戏》剧照,剧中演员会打破“第四面墙”挑衅观众。
比起《鱿鱼游戏》,《趣味游戏》与观众建立起更直接的互动,以此搭建了一个由影片和观众共同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观众会感受到自己人性的底线一再被测试。不知是否因为激怒了包含影评人在内的观众,《趣味游戏》当年的票房相当糟糕。
如果说大多数影视作品囿于传统形式,与受众的互动尚且有限,那么电子游戏的风行恰好补足了前者的这一弱点。由于其自带的交互属性,电子游戏为玩家体验各种系统开辟了一条通途。许多电子游戏都竞相在剧情和游戏方式中融入哲学思考,那些难以取舍、几近残酷的道德选择纷纷被丢到玩家面前。只要沉浸感做得出色,玩家就会被放置在类似成奇勋们的位置上,仿佛得到一张加入“鱿鱼游戏”的号码牌。
在某些开放世界的游戏中,玩家可以随便殴打或者抢劫路上的NPC,并轻易逃脱惩罚;当然,你也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从头到尾不做任何坏事,只是这并不会给角色带来任何实质性奖励。在这样的系统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遵从内心的道德律——即使那些NPC做得像《失控玩家》的主人公那样栩栩如生。

《失控玩家》剧照。
让人更直接体会道德困境的是《这是我的战争》。游戏背景设置在战争末期,炮火令城市几乎成了废墟。玩家作为幸存的平民,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和亲友活下去,一直撑到若干天后战争结束。由于物资匮乏,角色很容易陷入饥饿、疾病、寒冷、抑郁等各种负面状态,所以获取生存物资成了游戏中最重要的行为。
问题是,战争中物资是稀缺品。于是,一位母亲在风雪中敲门,跪求你把仅剩的食物送给她即将饿死的孩子;或是你的亲人病势沉重,隔壁街区的老人恰好有一颗保命药,但他不会给你,除非你偷窃或者使用暴力,无论如何,老人失去了药就意味着他注定会因你的行为而病死……玩家会频频遇到这样的随机事件,没有一个决定是轻松的。
被戏称作“致郁良方”的《这是我的战争》试图探讨一个沉重的命题,即:在远离正常社会秩序的极端系统里,如若提高生存概率的代价必然是作恶、牺牲他人,那么,人性中悲悯、克制、正义的那些部分,与人类生存本能间的冲突,究竟是否有调和的可能?在游戏中做出何种选择,本身只是玩家采取的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必经受道德的诘问;但经由虚拟世界学会拥抱良善、警惕邪恶,才是游戏过程所附赠的更宝贵的心得。
拒绝参加游戏的人:
抵制不人道的指令是英雄之举
《鱿鱼游戏》像一记警钟,提醒观众勿忘正视人性的深渊。在它身上,人们不难窥见其他反乌托邦作品的影子。例如十年前的《饥饿游戏》,二十年前的《大逃*》,都是此类影视的经典。
三十年前在中国公映过的美国电影《过关斩将》曾因惊悚与刺激程度而轰动一时,它火力全开,批判娱乐至死的电视工业。施瓦辛格主演了一个孤胆英雄,一路击败“冰场*手”、“电锯狂人”等以屠*为乐的对手。系统在此以综艺节目的形式出现,假借娱乐和竞赛的名义对人实施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最终将血腥的*戮合理化。所以,《过关斩将》也很可能是《鱿鱼游戏》的灵感来源。

《过关斩将》电影剧照。
上述作品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即主角在关键时刻都选择冒生命危险,去抵制系统所制定的规则。就像P.K.14乐队一首歌曲的名字,他们都是“拒绝参加游戏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拒绝,才得以部分或完整地保留了人性中的良善。津巴多的研究显示,身处恶劣的系统中,大多数人或是顺从、屈从,或是被劝服、受诱惑而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始终有少数人拒绝服从不符合人道的指令。
和平庸之恶一样,平庸的英雄之举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你当然可以跟随系统,跟随权威,跟随大流,那样看似最安全和有利;但也始终可以选择遵从内心的道德,对系统说不。在这方面,独立游戏《遗忘之城》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它发生在一座古罗马城市中,这里的市民相信神明制订的“黄金法则”——即“一人作恶,众人受难”(这个设定的灵感源自罗马军队中通行的“十一抽*律”)——统治着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