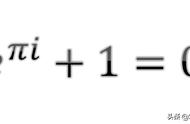要是给每个人出一道问答题:你记忆中最模糊的年代是什么时候?估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童年。
我自己对童年的记忆就是梦幻般模糊、碎片般散乱:
碎片一:
刚解放的时候没有计划生育限制,军队的供给制又十分优惠,那些个三十好几四十出头才由组织上“分配”到老婆、精力旺盛且传宗接代观念浓厚、下定决心要把战争年代损失时间补回来的军官们无所顾忌地争分夺秒,于是在解放初期,军队大院的孩子像雨后春笋般地出了一茬又一茬,生了一堆又一堆,差不多每家都是四个五个甚至六个七个的。
50年代初我家在四川乐山,当剿匪司令的父亲整天带着部队钻深山老林打狗日的土匪。
用我妈的话说,在我出生前,家里已经有好几张小嘴了:我哥、金丝猴、马猴和那条大狼狗(详情请看下一篇《从前,我家有条日本狼狗》)。我是52年11月来到这个世界的,因能吃能睡长肉快,爸妈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胖子。虽然我长大后别人多次对这个小名的准确性产生过疑问,但我小时候确实很“富态”。
我们家前面有个石阶,二岁左右穿着开裆裤的我喜欢在两旁的斜面青石板上滑滑梯,弄得一裤子的灰土不说,还经常让屁股“挂彩”,妈妈或保姆怎么喊都不听,但只要说“你爸爸回来了”,我就会一颠一颠地跑回家躲到门后头。
别看我父亲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可腰里别着左轮枪,大头皮鞋咚咚响,眼珠子一瞪,嗓门吼起来震山震地,神气得不是一般。
碎片二:
我们家孩子中,只有我一人儿时曾长期不在父母身边。三岁时,与《激情燃烧岁月》中石光荣一样大老粗的父亲,被组织安排去重庆上了军队干部文化速成班,我母亲一人照顾三个孩子忙不过来,就把我送到西南军区成都保育院。当时的我,那可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背井离乡”来到蓉城,在那个好吃好喝但不太好玩的地方呆了三年左右。我自己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十分朦胧,话又说回来,三五岁的事情哪个还记得一清二楚。我只记得,小朋友整天都穿着围兜,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小勺,唱歌要背着双手,睡的是那种四周有栏杆的小床。一个大屋子有很多小床,两张并在一起,我的旁边是个女孩,我在入睡前与她说过悄悄话,似乎还早熟地拉过人家粉嫩的小手,至于亲没亲过就记不得了(就是记得也不能在这里说呀)。我还记得,那里的老师都是女的,夏天她们要么穿 “布拉吉”,要么穿露出大腿的短裤,好像有一次我趴在老师的大腿上流着哈喇子听她讲故事,感觉她的大腿雪白雪白的,在阳光下很刺眼,几乎每个毛孔都非常清晰,越看越觉得雪白雪白的,越看哈喇子越多……
碎片三:
我爸曾说,他有一次去成都开会,从保育院把我接出去玩了一整天,我走不动,他就把我架在脖子上,带我吃饭馆,看耍猴,晚上还听了一场川剧,其实就他自己欣赏,我进剧场就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妈还告诉我,保育院给我的评语其中包括:憨厚(直说就是笨),能吃,不太讲卫生,是个小齁包(哮喘)。只要妈妈冬天去保育院探亲,我几乎都歪在医院的病床上大喘气。
碎片四:
别看我爸一生廉洁自律,他也犯过以权谋私的小错误。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晚上,有个单位放露天电影,我和老三想进去看,但看门人不让,拉扯之后我们只好哭哭啼啼回家,父亲问清楚后骂了几句就接着看文件,可我们不停的哭泣声影响了他工作,就四下找东西想打我们。婆婆(四川人对姥姥的称呼)不依,说他没本事,就知道打孩子。他一气之下拉着我们就到那个单位,大声对看门人说,我是XXX的XXX,老子要工作,我这两个儿子想看电影,要不要得呀?看门人一看这阵势,吓得全身筛糠:“长官,要得,要得唦。”
碎片五:
当时的绵阳还是个小县城,没有高层建筑,密密匝匝的青瓦平房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就跟现在云南丽江保存的老房屋差不多。街道不宽,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牛毛细雨中显得油光水滑。路两旁排列着木门木窗的各类店铺。每天清晨鸡鸣狗吠,各家各户的炊烟在瓦房上空袅袅氤氲开来,整个城市弥漫着焦炭、柴草、马桶、麻辣、叶子烟和各类吃食的混合味道。除了必须早起的大人外,路人中多是三三两两背着书包的学童。
碎片六:
“挺进报事件”。六年级时,班里有个女同学,名字叫杨红,他父亲好像是县法院院长。小学快毕业的某一天,她悄悄地从桌面下递给我一个红皮日记本,封皮上面写着“挺进”两个字,那个年代与《红岩》有联系的物品很时兴,扉页还写了几个字,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估计应该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我当时真不懂也真该死,翻过去翻过来看了看就大声问她:“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她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不说就把笔记本夺了回去。这个过程让另一个男孩看见了,他四下与同学们咬耳朵还在班里大声叫喊:“挺进报,挺进报,谁要谁要?”从此,她再也不搭理我,直到我们分别上了不同的中学。其实我平时也喜欢和她说话儿,因为她长得很好看,经常穿一件红色灯心绒上衣,剪的是短发,高兴了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这件事情让我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她。
碎片七: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上学都自己带饭,到学校后把带去的饭盒放在厨房的大蒸笼里,等中午下课就可以吃热乎的。我和几个家境稍好的同学每天都带一个饭盒,里面除了米饭和蔬菜外,有时还有点荤腥。但农村的同学就比较艰苦,几乎每天都是几根咸菜就红苕。
记得婆婆在后院养了一头猪,那个时候能养猪可不简单,因为连人都缺吃食,何况食量大的猪。我和我哥去郊外打过猪草,还在单位食堂偷过泔水。我们兄弟几个经常在后院用小木棍支起一个簸箕,下面撒点米,等馋嘴的麻雀进去后一拉绳子就有“战利品”,婆婆利索地褪毛开膛抹盐然后用油一炸,啧啧,香得我们连骨头都嚼碎了吞进肚里。有的时候那头猪很讨厌,它知道簸箕下有米粒后,经常哼哼哼地跑过来,拱翻簸箕找米粒吃,怎么打它都不走,惹急了一头就把我们拱翻在地。
碎片八:
短暂的绵阳一中时光。考初中前,母亲反复地唠叨,要我争取考上当地最好的中学----绵阳一中,据说我哥考试发挥失常差点没考上。但我发挥正常,尤其作文不错。因父亲离休举家迁往南充,我在一中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其间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位女同学,也姓杨,她父亲也是老红军,是从广西军区来绵阳离休的。可能当时的我还没正式开始发育,所以觉得她比我高大许多,白白嫩嫩的,梳着两条大辫子,举止很矜持,说一口悦耳的普通话。她坐在我后面,平时彼此很少说话,离别的时候好像也没专门打招呼,毕竟我们不熟悉。
时隔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恢复了联系,相互之间也有一些故事。要说青梅竹马是有点牵强,定义为两小无猜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