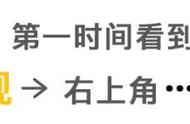年龄越大越想家,不轻易间,思绪总会飘到30多年前: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五服之内兄弟几个初一早上拜年、收割小麦轧场看麦子、冻得裂缝的土地、倒计时的二月二庙会、偷吃邻居家稚嫩的茄子纽、面露狰狞的村医握着的玻璃注射器、青瓦沿垂吊的冰溜子、被母亲扭红的腿里子、不几年嫁走的姐姐们、转不停的室外电视天线、三分钟抢空的喜酒菜、给当班主任的婶子儿子擦得红屁股、妯娌们跳起三丈高互卷的国粹操作、被闹到急眼的新入村婶子嫂子们、老婆婆们议论的儿媳妇的多宗罪……,等等都是纯粹的记忆,散发泥土的清香。

照片来自网络
想到这些,脑袋中闪现出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村头的大兴哥,不管风吹日晒他还在守村平安,他熬走了一代一代嘲笑过他的人。真想活成他,但又怕他嘲笑我不虔诚、缺修行。

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