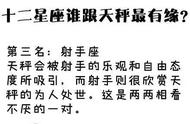越剧不在乎别人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什么;越剧在乎我们能做什么,别人做不了我们能做的什么。
一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2年的20余年间,可以看作越剧的第一次觉醒。这第一次觉醒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剧场意识”的觉醒。从乡村到城市,从广场到剧场,从戏台到舞台,越剧从唱戏时代进入了演戏时代。女子越剧自诞生那天起,就是中国的剧场艺术,因为是剧场艺术,所以才需要配备编导机制。编导机制的介入,助推了剧场艺术的发展。时代性和艺术性,以及舞台艺术的综合性,因此才真正确立。第二,“性别意识”的觉醒。越剧在上海命名之初指的是女子越剧而不是男班或男女合演,这是中国戏曲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全女班命名的剧种,标志着女性意识在当时的觉醒。强调越剧的女性性别,并不仅仅出于商业性的号召,而是包含着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自主自立和自尊自强的观念,包含着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环境与文明风尚。而这种性别意识,更是走在了古老戏曲剧种与各新兴地方戏曲的前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越剧都是中国新戏曲的舞台艺术风向标,影响着中国地方戏曲甚至整个中国戏曲的审美风尚。在越剧主要是上海越剧的引领下,全国各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开始建立起编导制度,与此同时,戏曲也开始强调女性的平等意识。对一个时期的戏曲艺术转型,上海越剧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这是越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浪潮,它的标志就是赢得了那个时期的年轻人。但为什么今天的年轻戏曲观众会首选昆曲等古老剧种而后选择越剧等新兴剧种?这说明越剧与这个时代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距离。
第二次越剧觉醒的中心在浙江,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创作的那几出新戏。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越剧院特别是吕瑞英老师任院长的那几年,为中国越剧在新时期的转型发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努力,希望通过这一轮的创新发展带动越剧走入现代剧场、现代观众和现代市场。如在表演方法上、在戏剧观念上引进了许多现代戏剧的思想,同时面对市场的式微与经费的拮据,拓展新的艺术疆界和新的经营理念,非常之早也非常之自觉地试图从计划经济的困境中突围出来。如与上海梅龙镇餐饮企业合作开办“越友酒家”;如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的一团更名为“红楼剧团”,与泰国正大集团文企联手,共同开拓越剧的海内外演出市场;如将吕瑞英和优秀男演员赵志刚、史济华等领衔的男女合演三团与上海露露化妆品厂合作冠名;再如聘请著名导演胡伟民担任男女合演团的艺术指导,同时面向全国发现并引进30岁年龄段的青年编剧、导演、作曲等创作人才,我也是因此从江苏淮阴调入上海越剧院的。
吕瑞英是袁雪芬的学生,不仅在艺术上师承袁雪芬的“袁派”,并且在“袁派”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自身表演艺术特点的新的越剧流派“吕派”。吕瑞英还是在精神气质上最像袁雪芬并最具有改革意识的越剧领军人物。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越剧院便在她的带领下,开始了即便放在今天仍属于先知先觉、先锋先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与此同时,浙江越剧乘势而起,以浙江小百花越剧的青春之美、江南之美和契合新的剧场艺术的现代之美,一举完成了中国越剧艺术的升级换代。我以为这就是越剧的第二次觉醒,也是越剧的第二次浪潮。从此,以茅威涛为代表和以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舞台艺术风格为风尚的一个新的越剧时代就此到来。
二
在我1986年加盟上海越剧院后的那几年里,袁雪芬老院长数次约我谈话,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向我强调要坚守上海越剧院的现实主义传统。我由衷地尊敬袁雪芬老院长,也由衷地表达了对她所说的越剧现实主义传统的疑惑。我心想,越剧现在应该面对的是现代意识的更新。
1992年,袁雪芬在汾阳路上海越剧院旧址主持了纪念越剧改革50周年的研讨会,会上安排了我的发言,会后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呼唤越剧精神的回归》的文章,我在文章里说上海越剧淡薄了四个意识——“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团结意识”和“与新文化人结合的意识”。
今天回忆当年与袁雪芬的分歧,我觉得坚持上海越剧院曾经实践的现实主义越剧创作传统,与实现现代意识在新时期的艺术转化,其实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没有曾经的越剧“现实主义创作”,不会诞生上海越剧院《梁祝》《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四部经典名剧。但是,仅靠传承传统,仅靠传播传统,仅靠传扬传统,上海越剧也可能逐步与时代脱节。就其积累而言,上海越剧院还不是欧洲的著名大歌剧院,还没有仅靠储备的经典家底就足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实力。当然,如果连传承、传播、传扬这些传统经典的能力都没有,或者失去了再造这些传统风格新剧目的能力,那么也极有可能既没有开创新局面,也丢失了根本。
假如时光倒流,我想我会更多一些与前辈艺术家的共识,也会努力寻找彼此观念的平衡点。
三
浙江越剧的应运而生,发展了第一次越剧觉醒的理念。即一方面重新理解“剧场艺术”,拓展“剧场艺术”的综合表现外延,再一次向古老剧种——昆剧和向当代艺术——现代话剧学习,使传统更传统,使现代更现代。另一方面重新唤醒“性别意识”,而此时的女性意识已经上升到个性意识——个性化的追求与个性化的表达。遍布浙江省境内的小百花青年演员,正是“三花一娟”和“越剧十姐妹”当年改革越剧的年岁,与当年越剧赢得青年观众一样,新生代越剧演员也赢得了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观众,越剧因此而再度焕发青春。
浙江越剧“重返青春”的小百花青年演员选拔机制和人才成果也惠及上海,上海越剧院现在的五位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钱惠丽、单仰萍、章瑞虹、方亚芬、王志萍,都是从浙江引进的“小百花”会演的优胜者。所以说,因为以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为代表的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场艺术”与“性别意识”的二次觉醒,越剧又一次影响到了中国戏曲的审美走向。这一次,虽不及第一次越剧改革对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深刻和深远,但对全国的越剧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越剧还是中国地方戏曲中受到广泛关注和效仿的剧种。
越剧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几家国有越剧院团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创新突破,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准方向,或者说始终没有出现新的标杆,也没有再出现继袁雪芬、茅威涛之后可以代表一个剧种并且影响到剧种发展的领军人物,困顿徘徊,直至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的2022年。
今天,我们放眼越剧,好像在舞台艺术、地方戏曲的大版图上,越剧的色彩越来越不那么鲜艳夺目,甚至还有点暗淡,暗淡到几乎看不到与其他兄弟姐妹剧种之间还有什么色彩差别和个性特点。
在争奇斗艳的戏曲大观园里,越剧暗淡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两个方面——“剧场意识”与“性别意识”,首先就是“性别意识”。
四
从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院的黄金时代开始,越剧就强调要发展“男女合演”。其实,“男女合演”与“女子越剧”是同一种方言曲调的共存关系,而不是女子越剧表演风格的性别延伸。从绍兴方言与民间曲调发展而成的越剧,声腔宾白并不受性别制约,可以男演,可以女演,可以男女合演,但是唯有女子越剧才是她的特色与魅力之所在。全世界,全女班的舞台艺术品种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越剧与日本的宝冢。在越剧发展历史上,男女合演本就存在,用不着再从女子越剧的声腔身段出发,进行一番倒流回流、分支分野。相反,女子越剧的发展,近些年来已有逐渐男性化的趋势——男性化的题材,男性化的表演,男性化的审美,甚至男性化的战争场面和与之相匹配的男性化的武戏打斗。凡是女子越剧不擅长的硬着头皮要去演,凡是女子越剧所擅长的恰恰不愿意去演。而今走进越剧剧场欣赏越剧的,已经越来越少是因为越剧演员的性别特点。事实上,性别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爱情观念、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等,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所面对的时代话题,也是女子越剧所擅长表现的精神与情感的无垠疆域。
越剧的第一次觉醒建立了剧场艺术的综合性审美,越剧的第二次觉醒拓展了镜框式舞台综合艺术的表现功能,越剧的第三次觉醒应该进入到新的演艺时代。中国戏曲从“唱戏时代”到“演戏时代”再到“演艺时代”,就是从田头街头、草台庙台到镜框式舞台的现代剧场,又从镜框式舞台的现代剧场里挣脱出来,走向更加多元的演艺空间,如大剧院、小剧场、沉浸式、体验式以及回归原生态的厅堂、园林、庭院。10年前、20年前戏曲剧团晋京演出,能够进入梅兰芳大剧院、长安大戏院那是何等荣光,而今天则希望进入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和新建的天桥剧场。戏曲演出对演出空间要求的演变,也折射出戏曲表演艺术的自身发展。为此,期待越剧再一次唤醒自己的“剧场意识”,再一次唤醒自己的“性别意识”。
或许,在2022年越剧改革8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期待越剧新的觉醒恰恰是一种回归的选择。回归我们曾经建立的剧场意识,拓展剧场意识在今天的新的空间意涵;回归我们曾经建立的性别意识,面对新的人际关系与伦理观念,发现我们对于人类性别情感的新的诠释。
越剧不在乎别人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什么;越剧在乎我们能做什么,别人做不了我们能做的什么。让越剧更越剧,这是我的期待。
(作者罗怀臻系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剧作家)
来源: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