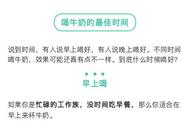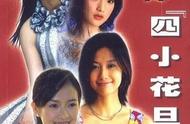音乐实践
有两种音乐(至少我总是这样想):人们听的音乐和人们演奏的音乐。这两种音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而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社会学、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色情:同一个人,在他听的时候可以是次要的,而在他演奏的时候(即便演奏很糟糕)可以是主要的,舒曼[1]就是这样。
人们演奏的音乐,是一种不大属于耳朵却尤其是属于手工的活动(在更为可感的意义上)。这便是您或我可以单独地或在朋友们之间演奏的除了参与者而没有其他听众的音乐(也就是说,带有远离任何做戏的风险和远离任何歇斯底里的意图)。这是一种肌肉的音乐,耳朵的感觉只占有一种确认的部分。这就好像是身体在听到,而不是“灵魂”在听到。这种音乐并不以“心”来演奏。身体坐在键盘或乐谱架前面,它在支配、引导、协调,它必须自己来编排他所读到的东西。它在制作声音和感觉。它是编排者,而不是接收者、截取者。这种音乐已经消失了。首先,这种音乐由于与空闲阶级(即贵族阶级)相联系,所以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钢琴、年轻的姑娘、演奏厅、夜曲)到来之际已经蜕变成上流社会的礼仪;尔后,它便被人忘却了(今天有谁弹钢琴呢?)。为了在西方找到仍在实践的音乐,就必须到另一种公众、另一类保留节目、另一种乐器方面去寻找(年轻人、歌曲、吉他)。与此同时,被动音乐,即被接收的音乐、发声音乐,则变成音乐(即演奏会的音乐、狂欢节的音乐、唱片的音乐、收音机里的音乐):演奏不复存在了;音乐活动从此不再是手工的、肌肉活动的、具有塑造能力的,而仅仅是流动的、吐露的、用巴尔扎克的一个词就是“滑动的”。实践音乐的人本身也变了。爱好者,更被作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欠佳的技巧来确定的角色,已无处可以找到了;职业演奏人员,即其接受的培训对于听众(有谁还知道音乐教学的问题呢?)来讲完全是秘密传授的专业人员,不再表现出完美的爱好者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高贵价值,我们在利帕蒂[2]、潘泽拉[3]那里还可以辨认出,因为这种风格在我们身上并不动摇满足心,而是动摇*,即制作那种音乐的*。总之,首先有音乐的演奏者,然后有演唱者(洪亮的浪漫嗓音),最后是技术人员——他使听众摆脱任何活动,哪怕是委托性的活动,并在音乐的秩序中废除制作的思想本身。
在我看来,贝多芬[4]的作品,就是与这一历史问题相联系的——该历史问题不是像对于一个时刻的简单表达(从爱好者过渡到演唱者),而是像一种文明之苦恼的强有力的类型,对于这种类型,贝多芬已同时汇集了其所有组成部分和描绘了解决方法。这种含混性,便是贝多芬的两种历史角色:整个19世纪使他扮演的神秘角色和我们的世纪开始在他身上看出的现代角色[在此,我参照了布库雷什列夫(Bou-courechliev)的研究工作]。
对于19世纪,如果我们排除某些愚笨的形象,例如那位差不多将贝多芬变成某种反动和反犹太人的伪君子万桑·德·安迪[5]的形象,贝多芬是音乐方面的第一个自由人。人们第一次称赞一位艺术家具有多种的连续方式;人们承认他具有变化的权利。他可以表示不满足于自己,或者更为深刻地讲,不满足于他的语言,他可以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改变其规则(这正是伦茨[6]为贝多芬的三种方式提供的天真和激励人心的形象所说明的东西);而且,自作品变成一种运动、一种路线的痕迹起,它便求助于一种命运观念;艺术家寻找他的“真实”,而这种寻找变成一种自身的秩序、一种总体上可以解读的讯息,但全然不顾其内容的变化,或至少,这种内容的可解读性是靠艺术家的一种整体性来得到的:他的职业、他的爱好、他的观念、他的性格、他的言辞,都变成一些意义特征。贝多芬的一种生平(我们似乎应该说,一种生物—神话学)诞生了;艺术家像一位完整的英雄出现了,他带着一种话语(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这种现象是稀少的)、一种传说(足有十几个趣闻)、一种肖像、一种世系(即艺术的泰坦[7]世系:米开朗基罗、巴尔扎克)和一种注定的厄运(为我们耳朵的快乐而进行...
然而,这种浪漫形象(其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总的说来就是意义)会产生一种演奏上的不适:爱好者不能控制贝多芬的音乐,这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而是因为前面的音乐实践的编码的衰退。按照编码,引导演奏者幻觉的(也就是说,是身体的)形象,就是(人们在内心“织就”的)歌曲的形象。演奏贝多芬的乐曲,模仿冲动(音乐幻觉,难道不就在于本身就像主体那样位于演奏之中吗?)会变成乐队性的。因此,这种幻觉躲避对于单一成分(嗓音或节奏)的偶像崇拜:身体想成为完整的。由此,一种有关表达内心情感的或家庭式演奏的想法,便被破坏了:想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便是将自己设想为乐队指挥(这是多少儿童的梦想啊?这是多少忍受着慌乱的中魔符号的领队人的一再的梦想啊?)。贝多芬的作品放弃爱好者,而似乎在第一时刻呼唤着新的浪漫神性,即演唱者。不过在此,也是新的失望:有谁(哪位独奏者?哪位钢琴家?)能够很好地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呢?就好像这种音乐只在“角色”和它的不出现之间、幻觉的创立和以整理为名而升华的适度平淡之间才让人选择。
这是因为,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也许有某种难以听见的东西(对它用耳去听不是正确的场所)。在此,我们又与第二个贝多芬会合在一起了。一位音乐家由于偶然或悲伤的命运(这是一回事)而重听,是不可能的。贝多芬的重听指明了那种任何意指都居于其中的缺失(manque):他的重听求助于一种并非是抽象的或内在的音乐,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求助于具有可感觉到的一种心智世界的音乐,即心智世界就像是可感事物的音乐。这种类型是真正革命性的,人们不能按照古代审美的术语来想象它;被演奏的作品不能按照作为总是文化的纯粹的感觉来接受,也不能按照可以是(修辞的、主题的)发展秩序的一种心智秩序来接受;没有这种类型,现代的文本、当代的音乐,都不能被接受。自从布库雷什列夫的分析问世以来,我们知道,这位贝多芬是标准的《魔幻变化》(Variations Diabelli)的贝多芬。掌握这位贝多芬(以及他所开启的类型)的过程,既不是演奏过程,也不是听觉过程,而是解读过程。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面对贝多芬的一个总谱,并从中获得一种内心的听力(这种听力还总是依赖过去的泛灵性幻觉);这意味着,不论是抽象地掌握或是从官能上掌握,都不重要,而是应该面对这种音乐将自己放在一种运用者(perfor-mateur)的状态或最好说在活动之中,这种运用者懂得移动、*、组合、安排,总之一句话(如果不是过分使用的话),赋予结构(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的建构或重新建构区别很大)。就像对于一个文本的解读(至少像我们可以假设、可以要求的那种解读)不在于接受、认识或重新感受这个文本,而在于重新写作这个文本,在于以一种新的记入方式来横穿它的书写,同样,解读贝多芬,也就是运用他的音乐、吸引它(它已准备好)到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实践中去。
于是,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某种音乐实践,那是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而被改变了的音乐实践。如果作曲就是为了将产品幽闭在音乐会的内部或无线电的收听活动的孤寂之中的话,那么作曲有什么用呢?作曲,至少在倾向上,是使人去进行,不是使人去听,而是使人去写。音乐的现代场所,不是大厅,而是音乐家在一种通常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之中,从一种声响起源转生到另一种声响起源的场景。是我们在演奏,当然还是通过委托形式来演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是要等到以后吗?),音乐会必须是一种工作室,任何梦幻、任何想象物,总之任何“灵魂”,都不能溢出这种工作室,而且,在这个工作室内,整个音乐行为都可以在一种毫无保留的实践中被吸收。某一位尚未被演奏的贝多芬在教我们去完成的,正是这种乌托邦——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在他身上预感到他是一位未来的音乐家。
1970,《艺术》(l'Arc)
注释
[1]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德国作曲家。——译注
[2]利帕蒂(Dinu Lipatti,1917—1950):罗马尼亚歌唱家。——译注
[3]夏乐·潘泽拉(Charles Panzera,1896—1976):瑞士歌唱家。——译注
[4]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译注
[5]万桑·德·安迪(Vincent d'Indy,1851—1931):法国作曲家。——译注
[6]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1926— ):德国作家。——译注
[7]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