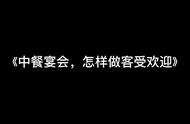中国农历的四季更迭以春为首,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岁时的流转以春最为艳丽,又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春天的节日,很多中国人脑海第一个浮现的可能会是春节。
这里其实有些误会,春节以“春”为名却未必在春天。中国农历是阴阳合历,春节属于阴历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为起点,立春却属于阳历那部分。也就是说,春节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晚冬。而且,春节尚处于数九寒天,百姓家的门前虽然贴满了红幅,大自然却依然一片万物肃*,春节的春意,终究还是淡了一些。
其实,中国有一个更适合代表春天的“艳丽”节日,那就是花朝节。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实在有些生僻。花朝节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终在岁月流逝中湮没无闻;花朝节所供奉的花神曾庙宇广布、香火不断,如今却在大众认知中被遗忘了姓名。
更令人讶异的是,花朝节究竟在哪一天也是桩“疑案”:山西人认为是在二月初二,北京人、江苏人相信是在二月十二,浙江人则笃定是在二月十五。细细算来,花朝节的日子竟横跨了小半个二月,真要叫人感叹“芳踪”难觅了。

花之时:仲春飘渺百花生
花朝节的花香飘渺,日子也飘渺。要确定它的时间,非得从更大尺度的时间单位入手,回溯十余个朝代才行。
“花朝”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晋人周处的《风土记》:“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 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见在浙江百姓眼中,此时正是赏花观月的好时节。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句中,“花朝”二字已不算罕见,如萧绎有“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江总有“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从字义中不难看出,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为“花开的清晨”,恰能与“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赏花的雅趣,顺着南北朝一路向未来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风。唐人爱花、赏花、鉴花,如晚唐罗虬甚至写了一篇《花九锡》,用重顶帷、金剪刀、甘泉等“九锡”,作为对花的礼赞——要知道,古代加“九锡”的权臣往往有称帝建国的野心,罗虬以“九锡”歌颂花却不觉僭越,唐人对花的宠溺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花朝在唐代依然未形成法定节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这一掌故很有些真伪莫辨。因为,直到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李适因为二月没有节日而与大臣李泌商议,李泌回答:“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可见,“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时”在唐代只是约定俗成的观念,但二月的确没有像样的节日,所以李适君臣这才将二月初一定为中和节。不过,虽然没有节日的“加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终究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一句,甚至将这一天凌驾于中秋之中,可见春花的魅力竟是盖过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终于“修”出了节日的“正果”。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花朝节的表述不再暧昧:“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可见,宋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节明白无误是在二月十五。当时花朝节民俗活动也蔚为壮观,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赏奇花异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园、包家山桃花、天庆观老君诞会等“知名景点”,各处一派“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热闹场面。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人的花朝只是达官贵人用于吟诗作赋的良辰美景,但宋代的花朝节则已经发展成君民同乐的世俗节日。花朝节的出现,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的流变,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
宋代花卉种植与买卖已是颇为常见的行当,不然也不会有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种种“小心思”。宋人对花的喜爱痴迷到了何种程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百姓出城探春的胜景:“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踈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
从时令轮转来看,花朝节“相继清明”;从朝代更迭来看,花朝节则要“相继明清”了。明清时期,花市比之于唐宋愈加繁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的扬州花市盛况,直让人在几百年后依然感到惊艳,甚至还有张秀才举办“百花会”,“四乡名花集焉”。不过,花朝节的日期也出现了“变数”——明代民间多认为二月十二为花神生日,这一观念影响极大,以至于花朝节自然而然被“合并”到了二月十二,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便有“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的记述,这分明是将花神生日和花朝混为一谈了。当然还有些地方将花朝节定为二月初二,其源流已不可考,大约是受了中和节与龙抬头习俗的影响吧……
面对这些“乱象”,明末陈继儒曾专门考证:“二月十五日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为花生日者,讹也。”当然,这种考证显然对抗不了民间的约定俗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曹雪芹将林黛玉的生日定在二月十二——这当然是为了暗示林黛玉是百花之神了。

花之史:十二花神各争春
花神用生日将花朝节“抢注”虽然有些“强势”,但背后的逻辑倒也称得上水到渠成。那么,花神又是何许“神”也呢?曹雪芹将林黛玉写成百花之神当然纯属个人创作——在历史上,花神其实另有其“神”,只是相关记载略有些漫漶不清,需要后人花些心思加以整合。
最早的线索,源于唐代颜真卿的墨宝。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专门写过一篇《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记录当地一位名为黄令微的女道士的“神迹”:这个黄令微八十岁时依然鹤发童颜,面容如少女般姣好,因此时人称其为“华姑”。黄令微寻访魏夫人未遂,后终于还是修炼成仙。
这个故事初看与花神无关,但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北宋成书的《太平广记》记载同一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魏)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黄灵徽明显是黄令微的音讹,“华”与“花”则相通。这里明确了黄令微是受到魏夫人点拨之后得道,因此可视为魏夫人的女弟子。比《太平广记》略晚的《类说》,又引《花木录》载:“魏夫人李弟子善种,谓之‘花姑’。”魏夫人,指的是晋代开创道教上清派的女道士魏华存,后被奉为紫虚元君,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地位颇高,黄令微能得到魏夫人指点,成仙自然也不足为奇了。
可见在两宋时期的传说中,黄令微已经从“华姑”演变为“花姑”,但她距离“花神”还是差了一步——这一步,就要从更古老的《淮南子》上跨出去了。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向召集门客所编,其《天文训》中记载:“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后高诱作注云: “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也”。到了南北朝时期,杜台卿《玉烛宝典》又明确了这位女夷的身世:天帝之女。可见,女夷作为天帝的女儿,是一位掌握春夏两季万物生长的神祇。
农耕时代,女夷这样的神祇当然大受世人爱戴。周代以降,历代王朝均有颇为完善的劝农制度,在仲春二月,皇帝要亲耕、后妃要亲桑,各州县还要设专门的劝农官员,祭拜主事的相应神祇,当然是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随着岁月流逝,主管万物生长的神祇女夷和被称为“花姑”的黄令微逐渐合二为一,最终就成为了“花神”的模样。明清时期,这两个源头并不相同的传说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明代陈懋仁《庶物异名疏》记载:“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清代冯应京《月令广义》亦载:“女夷,主春夏和养之神,即花神也。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为花神。”
黄令微荣升花神之后,与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的传说再次融合,于是这复杂的花神生日自然成为二月最为盛大的节日。只怪这传统的花朝节与花神生日实在过于接近,于是百姓眼中花朝节就渐渐被花神“捕获”,变成了二月十二。说来也是,还有什么日子,比花神生日更适合作为花朝节呢?
不过,“花姑”黄令微也没有笑到最后,因为在后世建造的花神庙中,广受香火的并不是这位曾经的道姑,而是一组由十二位花神组成的“花神团队”,更过分的是黄令微并不在其中。比如清代吴有如的《十二花神图》阵容如下:
一月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神杨延昭,四月蔷薇花神张丽华,五月石榴花神钟馗,六月荷花神西施,七月凤仙花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绿珠,九月菊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神谢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白居易,十二月腊花神老令婆。

十二花神在民间版本众多且越传越“走样”,清末俞樾认为这些版本过于“鄙俚不经”,于是亲自加以勘定,还又增加了两位“总领群花之神”,一位是佛教的迦叶尊者,因其曾在释迦牟尼面前“拈花一笑”;至于另一位,依然不是黄令微,而是魏夫人……
花之事:扑蝶赏红品糕酒
曹雪芹没能将林黛玉成功捧为花神,但《红楼梦》却还有一处暗笔勾勒出了花朝节的风俗,那就是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指的是薛宝钗,飞燕指的是林黛玉,而“戏彩蝶”“泣残红”背后,则浸染着满满的花朝节意象。
《红楼梦》中是这样写“宝钗扑蝶”的:“薛宝钗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虽然只字未提花朝,但要知道,花朝节别名“扑蝶会”,节日中最吸引人的游艺活动,就是扑蝶。
至少在宋代,扑蝶这一活动就已经为文人墨客所喜闻乐见,如苏轼《蝶恋花·佳人》中有“扑蝶西园随伴走”,苏汉臣的《婴戏图》所画也正是两个儿童扑蝶嬉戏的场面。清代《广群芳谱》引《诚斋诗话》云:“东京二月十二曰花朝,为扑蝶会。”这里更是将扑蝶与花朝节结合在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世传本《诚斋诗话》中并无此句,而宋代花朝节应为二月十五,因此这一引用是否为讹误尚有待商榷。不过在明清时期,花朝节中的扑蝶确确实实是一时盛事。明代汤显祖即有《花朝》诗直咏扑蝶之俗道:“百花风雨泪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清代不少地方直接称花朝为“扑蝶会日”,如嘉庆年间《如皋县志》载:“十五日花朝名扑蝶会,好事者置酒园亭,或嬉游郊外。”正至仲春二月百花盛开,这春光明媚之时,以扇扑蝶实在是最应景的雅趣,又何需“好事者”呢?恰如清代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所云:“是日闺中女郎扑蝶会,并效崔玄微护百花避风姨故事,剪五色彩缯,系花枝上为彩幡,谓之赏红。”

袁景澜这句话,前面说的是扑蝶,后面所言则是花朝节另一项活动:赏红。赏红是女子结伴出阁踏青,在游春过程中将红纸、红绢悬系于花枝,又称“挂红”或“百花挂红”。赏红虽是娱乐,倒也有祈农的寓意在里面,陈继儒考证道:“仲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缯, 悬树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谷之丰稔。”清代袁枚亦有《花朝日戏诸姬》云:“花朝时节祭花神,片片红罗缚树身。”可见,女子赏红有祭花神之意,而且能为花祈晴甚至占卜五谷的收成,这又与女夷崇拜的传统结合到了一起。
袁景澜所说的“崔玄微护百花避风姨”却是货真价实的唐代传奇。《太平广记·崔玄微》篇中记崔玄微为保护园中诸花,“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帮助群花抵抗住了“风神”封十八姨的摧折——这便是赏红活动中红纸、红绢的原型。不过,赏红的习俗唐宋未见,崔玄微之事应当是明清时期被附会的遥远缘起。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乐事,吃从来未曾缺席。花朝节吃什么?当然是吃花。中国人吃花的传统自古有之,屈原《离*》中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在花朝节,最出名的美食便是以花为原料的百花糕和百花酒。
关于百花糕的传说,可以追溯至唐代。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以赐近臣。”这一典故出处不明,不过却有佐证,清代光绪年间《青浦县志》载:“二月十二日花朝,群卉遍系红彩,家食年糕可免腰疼,谓之撑腰糕。”撑腰糕是苏州一带的名点,乃是将正月里没吃完年糕切成长条形薄片,用油煎了吃——讲究点的,还要撒上干桂花或是玫瑰花,据说吃了能让腰变结实,所以叫“撑腰糕”。不过,撑腰糕多在龙抬头这一天吃,如果武则天的百花蒸糕真是撑腰糕的前身,那花朝节与二月二倒又多了一些渊源。至于百花酒,也并非是真的纯粹用花酿酒。中国传统中的酒并非蒸馏而成的烧酒,而是用谷物、水果制成的发酵酒,若其中混入花自然能称为百花酒,但纵然没有花,只消在花朝节饮用,一样可以视为百花酒。百花糕也好,百花酒也罢,既然能在百花盛开时享用,自然就无愧于“百花”之名了。

花朝节肇始于唐、形成于宋、兴盛于明,至清代已极为盛大隆重。然而,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节日,却在清民易代的乱世中迅速衰败。1925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上海世界书局《红玫瑰》杂志专门开设“百花生日号”专刊,纪念当时已经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花朝节,可以视为这一节日的时代绝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花朝节的影响江河日下,其习俗逐渐被人淡忘,唐代“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的景象也不复存在。
花朝节衰败原因可以有很多猜测,比如各地花期不一因而日期不同,比如习俗地方特色过浓而未能普世化,比如百花糕和百花酒不如月饼和粽子那般“货真价实”……不过论其根本,恐怕离不开清末以降长年战乱导致的民生多艰——温饱尚成问题,谁还有心花事呢?
花的绽放需要春意盎然,人的雅意自然也要太平盛世打底。一旦国泰民安,花朝节的复兴便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汉服文化复兴大潮的驱使下,花朝节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民众眼前。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身穿传统汉服前往各自城市的郊野踏春赏花,被春色浸染的公园尽是《梦粱录》中“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场面——如果,下次有人问哪一个节日代表春天,可千万别忘了这三个字:花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