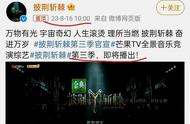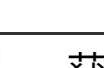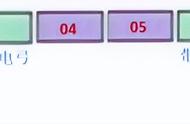《模仿犯》中的凶手被设定为一个表演型犯罪者。
推理迷常调侃“日本人的后脑勺是西瓜瓤一击即死”,说的是日本影视剧中*人手法已经愈发简单。在《模仿犯》中,如果不是凶手被设定为一个表演型犯罪者,那么推理故事的起点——凶*并没有什么值得玩味的地方。“*”在宫部美雪这里已经从一种必要的技法弱化为故事的起点,复仇的核心也不是凶*、技法,她强调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孕育的再平常不过的“*意”——“说不定是为了配合社会中充满这种蓄势待发的气氛,才会出现这样的罪犯。说得直白一点,犯罪的出现正是应了社会的某种需求。”这实质上是一种指涉,但犯罪称为一种日常的公共事件,每个人无论身处局中还是置身世外,都负有责任。
凶手“自己的舞台”
当前畑滋子在电视节目中揭穿网川浩一的真实面目时,这场直播就被作者赋予了舞台的意味。不同以往的是,原先被设定为棋子的前畑反客为主,用模仿故事犯罪成功激怒了凶手,让浩一在大众面前完成了犯罪“告白”。
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日本读者,对于宫部美雪这本小说最大的指摘,可能就是小说的冗长,以一部推理作品而言,《模仿犯》似乎长得有些过头。大量日常的细节,几十号有名有姓的人物,都会让读者有些无所适从,直呼铺垫过长。所以电影、电视剧都对原作的情节进行了大量的修剪,弱化枝干,强调前畑为核心的叙事主线。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也削减了原文所构筑的社会镜像。有人说宫部的小说让人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作品,确实,人物的群像轻描淡写但又面面俱到,情节十分的舒缓但一个瞬间悲剧就从天而降。这种舞台足以以假乱真,宫部美雪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在法律事务所做过一段时间的速记员,这为她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你可以从《模仿犯》的细节中提取出大量日本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模仿犯》剧集剧照
在塑造凶手网川浩一的时候,作者实际上面临一定的风险。这样一个在故事前期全知全能的高智商犯罪者,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暴露,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落差,稍有不慎就会让读者觉得索然无味。比如知名的“黄道十二宫”*手,如同浩一一样,连环作案不断地挑衅警方,寄出费解的密码,不断撩拨公众的神经,但是最终无法将他抓捕归案,这就形成了一种叙事的闭环。宫部美雪显然不想给大家讲一个正义缺席的黑暗故事,坦白说,网川浩一的身世设定是有些无趣的,寄人篱下又志在上游,他一方面痛恨贵族颐指气使注重血统的封建,另一面又自卑于自身出身低贱。他的复仇其实也是一种演化,从操控个人的快感逐渐上升为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控诉。宫部恰切地掌握了暴露的尺度,浩一每一次和受害者的通话其实都会透露出他的面貌,警方也会在犯罪者的宣言中不断地积累侧写的素材。
但即便是这样,即便前畑已经知道面前这位魅力十足的年轻男子就是十恶不赦、为了愉悦*人的罪犯,她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浩一对于舆论或者说对于人性太了解了,他指称前畑一系列的新闻调查目的就是为了名利,前畑对于案件中几位受害者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故事中,真一和义男都从不同角度反击了浩一的论点,但是实质上前畑的动机剔除小说作者预设的正义立场,确实很值得读者深思与琢磨。
与其说凶手最终在正义面前束手就擒,不如说浩一完成了他的犯罪表演,他选择电视直播作为剧目华丽的谢幕,因为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并不是说正义一定必胜,这样的胜利不会有任何的赢家。因为任何人都是这个社会形态中的一分子,浩一作为一颗带有破坏性的石头,或许在犯罪的那一时刻会激起社会的涟漪,但是更多的时候,当你在东京各个JR站看到如沙丁鱼一般忙于通勤的社畜们,日复一日地完成着规定动作,你会意识到日本社会的停滞性。无论发生多么光怪陆离的案件,都会被这个名叫“日常”的怪物慢慢咀嚼吞噬,进而成为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大约就是宫部美雪在推理这个装置之外的野心,既有娱乐公众的现实目的,又不乏指涉现实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