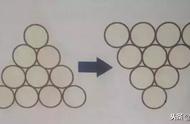我并不想写三个完美的女性,我也不想写什么“恶毒女二”,写一个人一坏到底,这不符合我的审美。一个人从出发点来说他可能认为自己做这件事是对的,或是为了争取权益,或是为了捍卫利益,不得不为之。我这些年写作中会尤其注意描写人物的弧光,无论是好人或坏人,都是复杂而立体的,没有人是完美的。
《梦华录》这个戏里,我并不是只写了这三个女孩,20集之后,其实还有高慧、葛招娣、皇后这些女性形象,她们都逐一展现出人生的另一个侧面,还有男性形象,每个男性角色身上其实也有我的想法。他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处理和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奔波。
这跟我当时写作的状态跟心境是有关系的,我那会儿遇到了很多状况,整个人是懵的状态,觉得人生就是“起落落落落”,真的已经被打到马里亚纳大海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去学习了心理学,我觉得要是不学点什么新的东西,写点不一样的题材,当时可能真就过不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梦华录》,所以想写一个古代的故事,写一群女孩,就像今天的“北漂”女孩,她们有各种各样的挣扎,谋求幸福和爱,这样的愿望跟今天的女孩是没有区别的,这都是人的本能。

“所谓高于生活,高于多少,我希望是半尺”
我是写时装剧出身的,我的时装剧早年也被人家讲是偶像剧,我自己不这么看,只是因为演员都是年轻的帅哥美女,有很多粉丝,所以会被定义为偶像剧,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写作的标准叫“离地半尺”,而不是“离地三尺”。
为此,我需要做大量前期的调研和案头工作,做实际的采访,去采风,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去交流体会,甚至浸润,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有悬浮感,只有根基和框架立住了,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写观众比较爱看的谈恋爱的情节,才不会被觉得“假”。
《梦华录》作为一个古装剧,也许观众不会跟它的历史背景那么较劲,但是在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能力范围里做得严谨一点。我笔下的主角不能是那种身怀各种技能,不受任何商业、道德、法律伦理和历史框架的限制,需要的时候就开“金手指”的人物,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希望我笔下的古装人物有现代思维的同时,也尊重历史。

这部剧我最花心力的其实是如何尽可能地做到历史落地,才能显出足够真实的古代市井风情。为此我请了好多顾问,我父亲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我请他帮我审过稿子;常彧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请来的剧本顾问,全程一直在帮我。其他像《宋宴》的作者、茶百戏的非遗传人等,我都辗转托朋友去找到他们,在剧本写作期间请求他们的技术支持。在剧组拍摄期间,剧组的老师们据我所知也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观众能看到我们尽量对宋早期的一些生活风貌作了还原。宋代的官制特别复杂,赵冬梅老师(著名历史学者)说,“能够写出‘勾当皇城司使’,说明编剧应该是做了功课了。”我看到这个评价特别开心,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确实努力过了。
这一行有一个说法叫“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品肯定是来源于生活的,但不是严丝合缝跟生活一样,所谓高于生活,高于多少,我希望是半尺,别太远,太远就不接地气了,就到空中去了。我追求的不是“飞在空中”的那种戏,飞在空中的戏,写得好的也非常好看,只是我不是这个类型的作者。

“女性友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很擅长欣赏别人,也会鼓励彼此”
2012年我在中欧上学的时候,班上有13个女生,我是其中岁数最小的,所以我是在全班女生的呵护下“长大”的。我认识的那些女同学,她们都非常优秀,也因为优秀,她们特别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秀,而且她们能够发现别人的好,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在她们的鼓励下被发现的。
我觉得女性友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很擅长欣赏别人,也会鼓励彼此。每个人都有闪光点,我们自己要发现特长,也要发现别人身上的与众不同,就像我欣赏我的一个女同学,有一次,我跟她一路打车40多分钟,她不停接电话处理工作,对电话那边的每个人都细致、耐心、不厌其烦,我非常佩服,换我肯定做不到。
我记得中欧有一门课是“360度测评”,我们全班几乎所有人的自我打分都比周围人打分要高,这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如果没有“大老虎”“大孔雀”的人格,你是做不到领导者的,对吧?只有我给自己的打分要比周围人平均低2分。中欧同学里像我这样的人非常罕见,因为这说明我当时对自我的接纳是很低的,现在如果再做同样的测评,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别人打分跟自己打分持平了。这就是一个自我肯定和自我接纳的过程,我有了更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