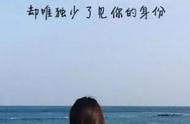我出生在素有"渔米之乡"的洞庭湖平原,这里地势平坦,沃野千里,江河星罗棋布,处处稻花香,家家鱼儿欢,好一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听祖辈讲,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原来是洞庭湖湖底,后来围湖造田,人们纷纷迁移过来,所以造成这里地势低洼,但以平坦多是黑色肥沃土地为主,很适宜水稻种植,水稻也高产。
一到夏天,真是千里稻花飘香,蛙声十里。大大小小的池塘,江河也是密布其中,家家户户房间屋后都被大小池塘包围。池塘里有种满荷花,有鱼戏莲叶间,池塘边有风吹杨柳依依,*诗词里面"芙蓉国里尽朝晖”就是对这里的真实写照。
每个乡镇被挡水堤坝围住,我们称之为垸,乡民们就住在垸子里,垸与垸之间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江河隔开,各种大小船舶穿梭其中,汽笛声此起彼伏,河两岸的人们通过各种建在江河上的桥梁来往通行,通婚嫁娶。

我的故乡还有一个美称"江南水乡"。水乡就是其中一大特色,因为水而充满生命和活力,也因为水乡亲们也心生敬畏。
长江的支流湘江流经我的故乡,湘江又分化为各种大小不一的河流湖泊,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点缀在故乡土地上。
每年的春季,冰雪融化,万物苏醒,故乡进入了梅雨季节,整天下着毛毛细雨,注满江河湖泊。加上从长江倾泻而来的水注入湘江,最后分散汇入其它的支流我们称之为"西水"。
到了夏天房前屋后就像水漫金山,四周被水连成一片,水中有我,我中有水,出门都要摸水过河。更令人担忧的是挡水堤坝也经常被河水漫过堤面,乡民们因此整天24时派人巡逻值守,加固加高堤坝,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有点像堰塞湖一样,人们就住在湖水下,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乡民早早的把家里细软搬上堤坝,用木桩钉牢捆住。晚上也不敢安心睡觉,有的干脆睡在堤坝上,以防随时溃堤。像这样的日子一般要经历一个炎热的夏天。
记得有一年我们对面的垸子缺口溃堤了,老远就听到对面敲锣打鼓,放土炮,乡民们在堤坝上边来回跑边大喊"缺口啰,缺口啰,大家快点上堤",政府派的直升机也在垸子上空盘旋投放救灾物资。因为对方垸子成了泻洪区,我们这些周边的垸子自然也松了一口气,免除了水患的危险,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通过政府每年大力兴修水利,长江三峡大坝调节,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患了。

故乡的风景这样美丽,那是因为四季分明的气候给我们呈现出一年之中四种不同的风光和感受。
春天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季节,每到春天,虽然春寒料峭,但水开始流动了,小鸭子嘎嘎嘎在水中环游,小荷也露尖尖角,河边的柳树抽出细细的嫩牙,柳条随风飘扬,轻抚水面。更漂亮的是田间地头的油菜菜花烂漫,小朋友乐在其中,好一个"待到春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不过也有挺烦的时候,我们这里的春天也是长达好几个月的梅雨季节,整个季节没有几天是晴天,每天一睁眼就是阴雨绵绵,到处湿潞潞的,弄得衣服都发霉了,好在晴天那种雨后充满泥土气息的春光美,所以在下雨天想想那种期盼也是美好的。
故乡的夏天是我即爱又怕的季节,爱的是终于不用像冬天样把自己包裹得厚实,可以行动自如。小时间经常邀上三五好友钓鱼,采摘荷花,莲藕根,池塘里光屁股游水戏耍都留下了我们欢快的笑声。不过正是因为池塘多也经常埋下了隐患,那时候我们溺水是常事,好在大难不死,但儿时的伙伴总有那么几个不幸的,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都会游泳,这和夏天我们经常玩水,溺水有关,淹了几次自然也就会了。
家园里的瓜果蔬菜也丰收在望,这时家家餐桌上都是新鲜生长的黄瓜,茄子,扁豆,豆角,辣椒,空心菜。
怕的首先是故乡夏天的酷热和劳作。故乡的夏天有一伏二伏三伏几个阶段,高温达到四十多度,而且时间长,要持续三四个月。炎热的时候太阳是白色的,大地是滚烫的,天空是安静的。那个时候没空调,大人都直接躺地上,用蒲扇扇风,其实也没多大作用,因为扇来扇去都是热风,小孩泡在水里解暑。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傍晚,父母早早的用冰凉的井水泊在门前屋后的地面上降温,同时擦拭好竹板床,然后搬到堤坝上摆好,其实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堤坝上摆满了竹板床,在堤坝上乘凉,大人们蒲扇不离手,家长里短的好不热闹。我们小孩子嘛追打嘻戏,玩迷藏,捉萤火虫……。玩累了,深夜了,月亮当空照,大家挂上蚊帐,睡在竹板床上渐渐进入梦乡……
我想在炎热的夏天忙着"双抢"应该是我最难以忘怀,甚至至今还留下了阴影,以至于我在那个时候立志发誓要走出故乡,与"双抢"永远告别。
双抢顾名思义,就是抢时间收割稻谷,播种插秧。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机械化,都是人工靠双手操作,又热又累又慢,真是背晒青天手抓黄土。首先要收割,你可以想像大热天,顶着大太阳,戴着草帽,弓着背,身体向前倾,窝在密不透风的稻穗里,一手扶稻杆一手持镰刀割稻穗;一脚踩打禾机,双手把住一把稻穗升进滚筒里打稻谷,脸上背上爆汗涟涟,全身溅满谷子,爬满各种昆虫使劲的撕咬你,那真的是酸爽。
收割完稻谷,父母接着要耕地整地,早上四点多我们就要跟在父母的屁股后头去秧田扯秧,扯到太阳刚露鱼肚白才能回来做饭,快速扒了几口饭趁着上午天气凉快早点出工插秧。这个还可以忍受,最痛苦的是下午时分,一般是下午两点左右,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水田里的水都可以把泥鳅鳝鱼煮死,我们要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冒着大太阳,弯腰弓背,站桩似的在水田里插秧一直插到太阳下山。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一身臭汗,就剩一口气。像这样高强度的劳作一般都要持续半个月才收场,我想七零八零后应该深有体会,心有余悸。
我本是一个感性的人,故乡的秋天莫然带给我一种落寞。有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失落。
秋收的开始是故乡的秋慢慢弥漫开来,由夏天的绿装换成了金黄色的秋装。稻穗黄了,弯下它那沉甸甸的身子,在风中摇曳,形成一波又一波厚实的麦浪。随着第一场北风的到来,植物变得枯黄,树叶也披上黄色的嫁衣,经风媒婆一吹,纷纷飘散,撒落一地。池塘里的水也干了,乡民们不分男女老少,纷纷扎进泥汤里,摘的摘莲蓬,捉的捉鱼,挖的挖藕,尽管每个人身上脸上都被黑泥画上了妆,但喜笑颜开,丰收的喜悦夹杂着嘈杂的欢快声响切故乡的每一个角落,直至消失在傍晚的炊烟里。秋天的夜充满初冬的寒气,秋天早晨的霜降预示着冬天的来临。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故乡,那时正值故乡的隆冬,寒风呼啸,万物萧条,逛风夹杂着冰雨漫天飞舞,但好几年都看不到下雪,我讨厌现在的冬天,更加怀念儿时的冬季。
记忆中儿时故乡的冬天比现在还要冷,但总有我喜欢白雪,一个冬季至少要下好几场大雪,有四十公分厚,一脚踩下去快淹到膝盖,踩在雪上嘎吱嘎吱响,真是过瘾。
更小一点的时候,冬天下雪了,我们一般围在用藕煤做燃料的火炉旁边烤火,父母亲把饭桌移靠在我们周边,我们一边烤火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视,其乐融融。上学了,父母一般做好早饭再叫我们起床洗漱吃饭,背着书包,冒着鹅毛大雪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上学的路上,白茫茫的世界里留下我们隐隐约约的身影……。
最后我要满怀深情的叙述我的父老乡亲,故乡的父老乡亲是随着共和国从艰难困苦的脚步一起走到了幸福安宁的今天。
打我记事起初,故乡的很多乡民从事水运工作,他们家里都有一条货运船,常年累月漂泊在故乡的江河湖泊中,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洗脚上岸,开始了水稻的种植,渔业养殖。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故乡的中青年人才陆陆续续离开家乡南下广东打工。得益于祖国的改革开放,乡亲们纷纷发家致富,建起了洋楼,买起了汽车,做起了老板,人人都富足起来。
我也是追随前辈的足迹,毕业后就离开了故乡,往来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为了生活我很少回故乡,每次回去,故乡的一花一草还是很熟悉,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唯一变化的是曾经熟悉的面容慢慢的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年轻陌生的面孔,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把我当作一个外来客,其实我才是这个村子里长大的人,却被别人问起这是谁家的客人。
这时我想起一首歌:"我多想回到家乡,回到她的身旁,看她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伤……"
我多想回到过去,回到过去的故乡,见一见故乡的父老乡亲,重温儿时的生活,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故乡,我深深的爱着你,眷恋着你!何时才能回到你温暖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