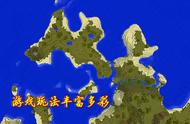一部被观众“偷走”剧情的喜剧
对美国的电视观众而言,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大书特书“宽松”和“自由”的创作新时代。
《纽约》杂志前主编库尔特·安德森在《为什么90年代是最好的10年》一文中表示,90年代是美国电视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新时代”。
“90年代末,我们都有了手机,但还不是智能手机;我们还没有被设备过度连接,或者受到技术的控制。社交媒体还没有令社交生活变得病态般无休无止,一方面又弱化了社交生活。”
他用“和平、繁荣、秩序”三个词形容美国社会当时的文化氛围,“文学、音乐、电影、电视,这其中既有承袭自过去的东西,也有崭新的原创形式”。
一群希望通过介入社会科学、文艺创作找到身份认同的“沙发土豆”(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人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提出,指手握遥控器蜷在沙发里,跟着电视节目、电视剧转的人)诞生了,这个群体被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统称为“过度的读者”。

沙发土豆们决定了剧情的走向。
“粉丝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热烈、狂热和参与式’的,这和中产阶级试图与文本保持距离、持‘欣赏性和批判性’的态度正好相对。”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写道。
沙发土豆们对参与剧集的渴望,正好赶上90年代美国电视兴起的“唯收视率论”,于是不少《老友记》的观众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决定“谁和谁好”。
在他们的坚持下,瑞秋和乔伊分道扬镳,最终回到罗斯的怀抱;再比如,他们希望看到钱德勒和莫妮卡发生“伦敦一夜情”后继续在一起,而不是像编剧之前预设的,“这两人只是玩玩罢了”。
《老友记》似乎把90年代美国观众的“社会乌托邦”情结放大到了极致。它填充的不是《宋飞正传》里的惨淡人生,也没有像《*都市》那样对两性边界进行探索,它是电视圈献给美国观众的一份“千禧大礼”:
在“宇宙中心”纽约,六个年轻人活出了乌托邦式的洒脱生活,每个在电视机前为剧中人物握手、拥抱、接吻、孕育新生命而鼓掌的人,都从中分享了自我认定标准里的“美好生活”。
和过去观众“被灌输”的过程不同,在都市乌托邦的美好愿景下,《老友记》践行的是近乎“一人一票”的“观众中心制”:你想怎么拍,我们就怎么拍。

《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剧组的合影。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把观众和读者比喻为“偷猎者”,他们入侵文化领地所有者的疆域,“偷出”他们满意的、想要的东西。
《老友记》似乎就是这样一部被观众“偷走”剧情的喜剧,它的超前理念,预言了21世纪人设、粉丝和流量的重要性;它的包罗万象,则让每一个观剧者都能从中“偷走”属于自己的治愈情节。

“一块单片镜”
有微博网友这样分析《老友记》假如放在今天拍摄的角色安排:
瑞秋有个亚裔死敌;罗斯是非洲裔美国人,他的妹妹莫妮卡是一对黑人夫妇领养的白人女孩;钱德勒是同性恋,并和一起合租的乔伊“擦出火花”;菲比吃素,走上“环保卫士”的不归路,还受邀到联合国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演讲……
2019年,BBC给正在庆祝开播25周年的《老友记》泼了一盆冷水:这部剧以纽约为背景,但根据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这个城市的白人比例只占33%,遑论纽约加速种族融合的上世纪90年代。
超前性的另一面,是这部剧在26年后被业内人士诟病的局限性。
该剧出品人大卫·克莱恩说:“如果今天让我们重拍一次,剧中女同性恋婚礼的剧情可能会被放大,甚至成为某一季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