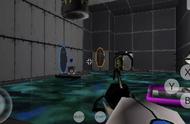那天下午遛弯儿,路过一所小学,从校园里,随风飘来稚嫩的童声合唱,好熟悉的旋律——《我们的田野》。
现在是2023年。这首歌创作于1953年。它70岁了。1953年,我11岁,小学六年级,音乐课上,老师教我们唱了这支歌。不过,我上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是按立式风琴伴奏,现在听到的音乐课飘来的歌声,是钢琴伴奏。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管桦,谱曲者是张文纲。
我如今81岁了。下楼遛弯儿,由助理焦金木陪着,遇到路面不够平整处,他会搀扶着我。那天蓝天白云,小风徐徐,遛得远一点,才路过了那所平日遛不到的小学墙外,恰巧听到了那歌声。
回到家里书房,我坐到懒人椅上——那是一张坐上去就把你身子兜住,舒服得你再懒挪窝的休闲沙发椅——金木给我端来新沏的乌牛早茶,端详着我问:“怎么?被那歌声触动了?”他怕我伤感,确实,老年人最忌讳的情绪,就是伤感。见我一时不作声,他用劝解的语气说:“很平常的歌嘛。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教我们唱过。”我就心算,他上小学唱那歌是什么时候?大约1983年,那歌30岁的时候。一首歌,几代人唱过,而且很可能还要被下几代人续唱。这歌算得生命力强劲了。呷口茶,我就跟已经坐到飘窗靠着腰枕的金木,聊了起来。
我跟他说,我不伤感,但感慨非常丰富,一系列面影,纷至沓来于心头。
他就问:首先涌上你心头的,是谁的面影?
我说,是德国女孩子的面影。他大吃一惊。
我跟他徐徐道来。1984年,当时我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那一年深秋,我接到来自德国的一个邀请——那时候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东边叫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西边叫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邀请我的是西德,先是请我参加一个大学生的冬令营,那一年的冬令营的一个主题是“了解中国”,安排我做一个关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演讲,内容不限于文学艺术;然后,再有几所大学的东亚文化系邀我去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他们提供了来回的机票,是那种分段转机费时较多的便宜机票,也是为了便宜,机票是通过航空货运,让我自己到北京机场货运场,拿已获得签证的护照认领。当时有朋友跟我说,邀请方太抠门了,明明有直飞西德法兰克福的航班,却让你这么风尘仆仆。我那时正当壮年,不怕劳累,而且一看那机票,先飞巴基斯坦卡拉奇,再转阿联酋迪拜,再转埃及开罗,从开罗再飞法兰克福;回程则先从法兰克福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再飞停中国乌鲁木齐,从祖国新疆再飞返北京——这比北京与法兰克福往返的飞法,大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我很高兴!

1984年,作者出访西德留影
去参加大学生冬令营活动,介绍中国,光凭演讲——虽然他们说了会请同声翻译——恐怕还是隔靴搔痒,最好还是提供一些直观的视听资料,那时候我的中篇小说《如意》在198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为一部抒情文艺片,就想带去录像带放映,但《如意》是表现黄昏恋的,最好能有表现中国青年人情感生活的片子拿去,于是想到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由谢飞执导的新片《我们的田野》。不是参加电影节,只是在冬令营做非商业性放映,因此不必带胶片拷贝,带录像带,在冬令营用录放机在电视机屏幕上显现就可以了,我在北京市文联开了介绍信,到电影局借到了两部电影的录像带,当时光盘还很不流行,电影胶片转换为录像带的技术已很完备,《我们的田野》拍摄于1983年,1984年也才刚在国内放映。影片里的青年人唱了《我们的田野》这首歌,由其变化出的旋律回旋在全片中。
当时西德的那个大学生冬令营,是在离科隆不远的一个小镇的一处会所建筑中举办的。其他情况都略过,单说放映《我们的田野》的情况。那个多功能厅不算大,看这部电影的活动,事先有通知,但冬令营的所有活动基本上都遵循自愿原则,那个下午去看的德国大学生不算多,我数了数,大约十几个。我说有德国女孩的面影飘上我的心头,就是那天去看电影的两个德国女大学生。我那之前虽然已经有过出访罗马尼亚、日本和法国的一点经验,但是对西方国家的种种方面,实在是仍处于雾里看花的状态,一些细枝末节,聚焦后,往往就会令我觉得惊奇。那天坐在那里观看中国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德国大学生,一个女孩一头银白的短发,后来知道,德国人当中,有些人生来就是银发,那并不是因为她忧愁而“白了少年头”,众多观影者中,唯她最专注,可谓目不转睛。当电影中响起《我们的田野》那歌声时,我见她睫毛抖动。一首1953年产生于中国的歌曲,那天下午响亮于遥远的德国小镇,哪怕是只令几个德国大学生动容,我以为,也是一桩美好的事。

《大众电影》1983年第九期的封面是
谢飞执导的电影《我们的田野》剧照
放映完《我们的田野》以后,有一段自由讨论的时间,我听不懂德语,好在有中国留学生可以充当口译。有一个头发是玉米色的德国女孩,她跟一位中国留学生似乎在讨论什么,后来我问中国留学生,她询问的是什么?中国留学男孩笑着告诉我,她看电影里有进屋子掀门帘的镜头,很好奇,问:中国人家里的门,都要挂那么一块纺织品吗?我就想,哪怕对方只是注意到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也很不错。相互了解,有时候就需要从最细小的地方发端,比如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有的德国姑娘,她那银发不是染的,而是天生的。那位观影格外专注的银发姑娘,对影片当中由演员雷汉饰演的肖弟弟一角,似乎印象最深,而且这个角色的名字弟弟也容易记住很好发声,她的感慨是:“那个弟弟的眼睛里,怎么有那么多的忧郁啊!”不知道导演谢飞听到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当时有个德国男孩说:“我的眼睛跟他一样,不是忧郁,是善良。”谢飞听了大概会微笑颔首。
我告诉金木,浮现在我心头的,又出现了一位钢琴家、指挥家。谁呢?石叔诚。他1983年获得德国DAAD奖学金和弗利德利希·瑙曼奖学金,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跟随著名指挥家沃尔克·汪恩海姆进修指挥,得到教授和乐队队员们的高度评价。1984年他也应邀去了那个大学生冬令营。他比我小四岁,一头黑发自然卷曲,戴副金丝边眼镜。他乡遇同胞,我们都很高兴。他在营里应邀演奏了若干钢琴曲。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建议他弹奏《我们的田野》,没有谱子,未经编配,钢琴家是不会当众演奏的。但他说他小时候也唱过这首歌,很喜欢。一天晚上,非正式活动时间,我从附近原野散步回来,没走进建筑物里面,就听见似乎是石叔诚在随意拨弄钢琴,是《我们的田野》的旋律。我走到窗边,没有马上进去,忽然,心里油然旋出酽酽的乡愁,此处虽好,非我故乡,我亲爱的祖国田野啊,“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金木问我:你跟《我们的田野》导演谢飞,交往过吗?我告诉他,交往谈不上,但是,1983年,我参加过一个持续多日的电影界的座谈会,谢飞和他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的人士,都在会上,我得以和他,以及郑洞天、林洪桐、张暖昕,还有来自上海的黄蜀芹等,有所交谈,我和他们,大体是同龄人,记得我和郑洞天谈到,我们现在搞创作,需要有“史”的意识,就是要清晰地认知,自己目前处于历史进程的哪一个节点上,如何将“前史”中的精华加以继承,如何为“后史”留下光斑,他很赞同我的看法。1992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风过耳》,林洪桐联系我,说想将其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道出了他的一些构想,但他晚了一步,那时我已经授权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唐果做这件事了。谢、郑、林、张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留校的,他们的同窗蔡晓晴那时候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拍摄了我的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还得了个奖。《我们的田野》是谢飞执导的第三部作品,他后来执导的《湘女潇潇》《香魂女》《本命年》都受到观众欢迎,并获得国际声誉。当时黄蜀芹刚拍完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的《青春万岁》,举行了首映,王蒙非常兴奋,跟我说:“比想象期待的更好!”黄蜀芹跟我说:“我是当作历史片来拍的。”我觉得她还原共和国初期青年学生的风采真实生动,特别是片尾,北京西郊杨林大道,一群骑自行车的男青年,追着卡车上女青年们互喊:“下一个五年计划再见!”重重拨动了我的心弦。但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些同代人,他们对黄蜀芹的这部作品有所批评,认为是落了以谢晋为代表的“上海模式”的窠臼,引出争议。争议归争议,大家还是友好相处,奔向各自的下一部创作。这些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面容,如今飘来叠印心头,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和我一样迈入耄耋之年。

电影《青春万岁》也出自1983年
金木问:你既然心里生出乡愁,是不是冬令营结束就回国了呢?我说还有下一段行程,就是到几所大学去访问。我心头,又飘出了一个德国——不能说女孩,得说女士——的面影。我告诉金木,我原来眼里看到西方白人,总觉得都一个样,分不清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后来出国机会更多,接触更广泛,就大体上能分清,比如现在浮现于我心头的女士,我一见她,就觉得是典型的德国女子。
话说我乘火车抵达维尔茨堡时,她从月台上迎着我走来,用纯熟的普通话问我:“您是从科隆来的刘心武先生吗?”我们一边往车站外走,一边交谈。她告诉我,是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派她来接我的,她已学了五年汉语,虽然还没有到过中国,但她起码在口语水平上,已达到优秀。当我们走出车站,坐到她开来的小轿车中时,我问:“你一定有汉名吧?你的汉名是怎样称呼的呢?”她微笑着告诉我:“葛伊莎,‘诸葛亮’的‘葛’,‘秋水伊人’的‘伊’,‘莎士比亚’的‘莎’。”我不禁大为佩服——“秋水伊人”的“伊”!即使是如今中国的大学生,怕也不是个个都知道“秋水伊人”这个语汇吧!
在那个大学生冬令营,因为参与的要么是理工科的,要么是攻读西方哲学历史的,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多还处于蒙昧状态,请他们随意道出所知道的中国人,想来想去,也就只能道出一个李小龙,因为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在那边有过商业放映,电视台也播过。参加那个冬令营活动的,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男孩子,他穿了一袭中国男士长袍,他告诉我他最崇拜的人是李敖,他说这些德国人甚至不知道孙中山,可是我们一般大学生都知道歌德、席勒,就信息交流而言,我们处于入超状态。
一般德国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但是到了维尔茨堡大学,我就发现,在他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中,其研究,可以细化、深入到何等程度,当时维尔茨堡大学正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合作,进行一项研究总计5485卷的明刊《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学术工程,其第一步,便是将这5485卷经书的所有语汇用电脑梳理分类,比较注释,以利理解与探究道教的全部奥秘。后来我进入大学图书馆的东亚图书藏书库,被引到整整一列长达40米高达五层的书架前,并被告知那便是不止一种版本的《道藏》时,就真的只能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那场面和自己的心情了。在那浩瀚的道教经典中,我只读过5000字的《道德经》,因此,倘若他们正经八百地要同我讨论“道”,以为我既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定对自己民族唯一成型的宗教道教及其理论能“头头是道”,那我可就露大“怯”了……
葛伊莎陪我畅游如诗如画的维尔茨堡,我们在市区豪华的宫殿中仰观绚丽的穹窿画,在山顶神秘的古堡中想像古时的火炬与呐喊,在有着一尊尊高大雕像的主教桥上徜徉,在河畔绿藤萦绕的咖啡馆里坐在高脚凳上呷浓浓的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葛伊莎有时交谈,有时各自想心事,《我们的田野》旋律又浮现心头,我不禁哼唱起来,葛伊莎微笑地望着我,我就问她:“你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哼起童年时唱的歌吗?”她告诉我:“当然。”于是轻轻哼唱出一串略带忧伤的旋律,我问:“这歌什么名字?”她说:“《小小汉斯》,应该是上个世纪就有的老歌,前几年我们这边拍了部电影《铁十字勋章》,片头就用了这首歌。是一首反战的歌。”因为各自哼了童年的歌,我们之间的隔阂,就进一步消融了。于是憬悟:无论人与人之间有怎样的种族、国别、语言、习俗、历史与现实因素形成的差异,交流永远是必须的,而且要坚信是会有良性效益的。
金木问:一首《我们的田野》,引出那么多的面容浮现你的心头,那最该浮现的,难道不应该是歌词的作者管桦吗?
我说:是的,是的,现在,管桦的面容身影,浓墨重彩地浮现在我心头了。
我告诉金木,我是1980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可惜我1986年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任职,竟从此再无专业作家身份。我很珍惜1980年至1986年那六年在北京市文联的岁月,那时候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队伍蔚为大观,最老的有上世纪初“南社”成员柳倩,还有一批建国前就从事文学创作的前辈,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从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老作家,其中有雷加、阮章竞、张志民、古立高等,管桦属于这个系列,他1940年在华北参加革命成为战地记者,至于建国后涌现的作家如杨沫、浩然、林斤澜、李学鳌、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刘厚明……资历都在以上老作家之下,如我等改革开放后才吸收进去的,实实在在属于小字辈了。
我这人不善交往,但也因某些机缘,到若干老作家家中拜访过,其中去过管桦家一次,那时候他还没有住进楼房,记得是在一个宽敞院落的一隅,他家门窗外,自种了一丛翠竹,别有意趣。管桦告诉我,他原来是中央乐团,专门负责写歌词的,跟他同一编制的,有乔羽。他们二人真是不负组织和民众期望,各自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写出了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歌词,他最著名的两首是《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乔羽最著名的两首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
记得那时管桦刚届花甲,他五官刚毅,身体健壮,说话中气很足,而且整个人显现出自信心爆棚。他从书柜里取出一本书拿给我看,封面是充满童趣的,艳丽明亮的水彩画,书名是《夏天旅行之歌》,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署名是管桦词、张文纲曲,翻开,里面是五线谱和歌词合璧,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出版过这样一种书,真的很特别。原来,管桦是一口气写下了五首总题为《夏天旅行之歌》的组歌:《森林欢迎我们》《营火烧起来了》《我们的田野》《准备着》《美丽的祖国》。《我们的田野》只是组歌中的第三首。现在知道这个情况的人,恐怕不多。那次我就跟他说,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都经常唱《我们的田野》,这歌对我的熏陶,太深入了,我爱画水彩画,中学时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我田野写生,画的时候胸中就有这歌的旋律,有好几幅就命名为《我们的田野》,回校后在教室后面的展示板上展览过。他就跟我说,其实,五首歌词他都写得很用心,张文纲的谱曲也都精彩,他说第一首《森林欢迎我们》,不信你对照五线谱在钢琴上弹出来,旋律的优美,绝不亚于《我们的田野》,说完微微叹了口气。文学艺术家普遍有这种遭遇,就是自我遮蔽,冰心因为一篇《小桔灯》选入了课本,就使得一些年轻人只读过这篇,以为这就是冰心散文的水平体现,《小桔灯》遮蔽了冰心许多高水平的佳作。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拍成了电影,《活动变人形》演成了话剧,《这边风景》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结果他精心结撰的“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就简直被遮蔽得似有若无。我自己的长篇小说“三楼系列”《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也是因为《钟鼓楼》得了茅奖,拍成过电视剧,搬上了话剧舞台,版本印次多,前两年又由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了英译本,响动大点,就把另外两部遮蔽得声息甚小了。

管桦著述甚丰。他建国前就写成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英雄雨来》,建国后基本上一直被课本收录,影响甚大。他还是画家,专攻墨竹,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居所窗外栽种竹丛的原因。他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致力于小说创作,1963年转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开理事会,当时一辆大巴车开到北京东四宾馆,我和北京市几位作家登上去后,发现车上已经坐了一些上海代表团的人士,我上去后坐到一位老大姐身边,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她笑:“啊,班主任嘛!”问我:“管桦来了吗?”我告诉她我们北京团分住几处,管桦不在此处。车往会场开去。我身边那位大姐,是上海与茹志鹃齐名的女作家菡子,我正纳闷她为什么偏偏问到管桦,她主动笑着告诉我:“1958年我是《收获》编辑,管桦的《辛俊地》我是责任编辑。”原来如此。《辛俊地》是一篇很独特的小说,刚在《收获》刊发我就看了,记得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写个人英雄主义的游击队员辛俊地,自作主张去伏击一个骑自行车的汉奸,将其击毙,其实那人是我方打入敌方的卧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作者的立意,是批判个人英雄主义,但以辛俊地为主角来写是否合宜,引来了批评,也算当年文坛的一个波澜。但总体而言,管桦一生顺遂,没有什么大的颠簸。为《夏天旅行之歌》谱曲的张文纲就没那么幸运,好在阴霾消去艳阳普照,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我们的田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2019年6月,《我们的田野》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算起来,到今年,是管桦101岁的冥诞,21年的忌日。我到他那窗外有竹丛的家里拜访,弹指已经40年了。谁能永领风*?谁能超越忘却?一个文学艺术家,一生有一首诗,一首歌,一幅画,一篇散文,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部电影,不被岁月抛弃,长久流传,就是大幸运,大福气。

我们的田野(刘心武 水彩速写于1958年)
说到这儿,我有点累了。金木说:“你今天因为一首儿童歌曲,回忆起这么多的人和事,我听了好有一比……”我就问:“比作何来?”他笑道:“像春节庙会,那种一米多长的大串糖葫芦。”我也笑了:“我自知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串起长长的糖葫芦,不过是觉得,大历史毕竟是由诸多小细节聚合而成的,我把自己生涯中亲历亲闻的种种细节串联起来,也许,可供今后的人们认知来路,遥望去路,增添些参考资料。”
我从懒人椅上起来,找出我上世纪末专门去新街口北大街——当时那里音像店密集——买到的女生三人组合黑鸭子的专辑《岁月如歌》,放进音响里播放,其中第一曲就是《我们的田野》。我没有再坐下,而是在书房里来回踱步。金木仍坐在飘窗上倚着大方枕,跟我一起静赏。只觉得碧绿的河水,流淌过我的心田。
2023年7月23日 绿叶居
作者:刘心武
编辑:谢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