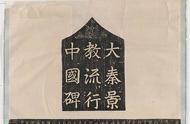古人有时以北斗九星的八九两颗星来讨论问题,有时与九的数术关联不明显,主要是从北斗七星的核心地位和其它两颗星为辅助的角度来比喻人间之政的。像关于辅星,《史记·天官书》曰:“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晋书·天文志》曰:“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 宋何薳 《春渚纪闻·歙山斗星砚》曰:“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因目之为斗星砚” ,明何景明 《告咎文》曰:“又使北斗以振纪兮,命辅星以佐之”,等等。

古人选择八九两颗星时,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两颗星与整个北斗七星的远近协调问题,否者以玄戈、招摇两颗星或较远的相、太阳守等作为九星组成的情况下也可以融合相关的数术问题(大火星是古代重要的授时主星,依文献记载、天象历法实际及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就有类似火正的观测者。以玄戈、招摇这两颗星与北斗七星、第五星、大火星连线,基本在一条直线上。陈久金先生还认为(陈久金:《北斗星斗柄指向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03期),由于岁差的原因,大火星出没的方位与北斗斗柄指向在季节中产生变化,原来夏至初昏大火星位于南中天,由于北斗七星5、7两颗星与大火星基本位于一直线,所以可以说夏至北斗斗柄南向,但是春秋战国时初昏南中天者为角、亢,所以从斗柄方向观测季节的角度考虑,就以北斗第6、7两颗星与角、亢连线而可以称夏至北斗斗柄南向)。《史记.天官书》也说,北斗旁的辅星明而近,则辅佐的大臣受信任而且权重;离北斗远而小,则不受信任,权轻而弱。
郑州荥阳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斗魁前方的圆形黄土台实际应在5500年左右的北斗九星围绕的极星位置附近。我们知道,天龙座 (Draco)是北方星座,是88个现代星座之一,也是托勒密所定的88个星座之一。它是拱极星座,在北半球四季可见,纬度变化在 90°和−15°之间可全见。理论上讲,西元前3942年起,天龙座的a即中国古代所谓的右枢星(Thuban)取代了之前最靠近北极点的牧夫座θ,成为肉眼能直接看见最靠近北极点的恒星。虽然右枢依照拜耳法命名为天龙座α,它却不是天龙座最亮的星,它的目视星等为3.65,比起最亮的天棓四(Eltanin,天龙座γ)的亮度2.23低一度。该星在西元前2787年最靠近北极点,距离只有2.5弧分,在之后的200年也没有超过1度,即2587年之前其近离北极。即使在最接近之后的900年距离也仍只有5度,直至西元前1793年才被天龙座κ取代。该星象非常有名,约在西元前二千七百年,天龙座α还成为古埃及人的北极星。从星象连接看,北斗七星中的天玑(大熊座γ)和天权(大熊座δ)的连线指向右枢附近,右枢就在天权前方7.5度之处。这样看来,黄土台附近代表的北极星就是天龙座a。黄土台不应是北极星,但是其位北极星附近(北极星基本处于天璇天玑连线的延伸线相切的位置),其应是一个祭坛。因为若表示极星,没必要制作一个圜丘,只用一个小的圆形圜丘甚至类似北斗九星的陶罐即可。该黄土台表面是天然黄土,形成一个圜丘状。诸多文献记载,冬至祭天于圜丘。对于这一圜丘,《尔雅.释天》认为应是非人为之圜丘,从青苔遗址的材料看早期恐非有此制。不过若从青台圜丘的上端全部是取来的纯净生黄土组成的情况看,也有可能是特意表现这一特征的,换言之,这样的圜丘也可以认为是非人为的。

青台天文遗迹的发现说明该黄土台不是北极星,不过其位置在北极星附近的情况说明,5500年左右北极星未能用北斗个星予以代替,这显然说明历史上的古人确实把天龙座a确定为当时的北极星,不少学者以为早期与北极距离明显更近的天龙座a星,由于是三等星从而古人会以北斗个星代替其为北极星,这一认识是不完备的。古代的巫术家、数术家、天文家都是耳聪目明的圣者,我们无法低估其观测的准确度。当然古人若视5500年左右的天龙座a为真正的北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北极星,则这时北斗的个星可能充当北极星,不过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历史上有天一、太一星,其星等都低于附近的北斗星,但是名字却是首星神的意思。尤其是天皇大帝星,其位置近于当时的北极,其时北斗个星也有非常近于北极的,并且与天皇大帝星也相近,为何以之名为天皇大帝呢?显然也是视其为首星神,即北极星也,但是其星等明显低于附近的北斗个星。
斗柄东北向,依据5800年——4800年前冬至时黄昏左右天空中北斗斗柄的方向,显然表明这是冬至时节的天象。同时从荥阳青台周边的地理地貌并结合初步的太阳观测看,西南、东南有关山脉有可能与黄土台构成一组冬至日出日落的天文准线。从古今天文准线相关角度的差距可以计算青台天文遗迹建制的年代,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际观测。这类天文准线的存在可能也是圜丘选择在这一地点的重要原因。当然冬至祭天季祭祀太阳的圜丘依礼仪制度应位于居住建筑主体的南方也是重要原因。
九星附近的瓮棺都应是祭祀星神的。同时在北斗、北极星天文遗迹的南面还有一倒立的瓮,可能是象征祖先的,随祭有一人,被去掉了手脚。从考古学层位看,相对于北斗这一组天文遗迹,这一祭祀祖先的遗迹时代应该更晚一些。可能在晚些时候,这一冬至祭祀北辰天神、北斗的天文遗迹依然存在或古人知道其位置,所以在选择在此地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
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与北斗、北辰、祖先有关的祭祀,是古往今来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周礼·春官·神仕》云:“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周礼·春官·大司乐》云:“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关于冬至祭天的理由,唐贾公彦疏《周礼·春官·大司乐》解释如下:“礼天神必于冬至,礼地祗必于夏至之日。以天是阳,地是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是以还于阳生、阴生之日祭之也。”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以冬至为年始即以冬至月为新年之始的历法实践也利于说明这一原因。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天神”郑玄注为天皇大帝(古代星图中有一星即名天皇大帝,其在斗魁附近,其在某一时间距离北极较近),有的学者认为不正确,从本文的考古发现看,冬至祭祀的天神包括北极星是正常的。不过这一理念在不同区域及时间段可能不一致。像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实践崇拜北极、北斗的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南方低纬度地区观测到周天北斗不落下的时间会较晚一些。而北方时代会早一些,所以北方中高纬度地区的人们对于北斗、北极会更为熟悉,利用或把人事与其关联可能会更早并且更为丰富,考古学发现南方广泛崇拜太阳更为丰富而中、北方广泛崇拜北极早早期明显优于南方。崇拜太阳和北斗、北极实际是与天文随着时代变化以及维度不同有联系的,人文思维和数术思维集中体现的易学之先天八卦及后天八卦中心的格子为太阳和北极的特征有利于说明这一问题,也利于说明古人对于太阳和北极星、北极的关注情况。
另《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报天而主日。”郑玄注云:“天之神,日为羊。”“以日为百神之王。”孔颖达疏云:“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居群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晋王嘉 《拾遗记·炎帝神农》曰: “筑圆丘以祀朝日。”由此可知冬至于圜丘祭祀的重要神灵还应有太阳神。荥阳青台天文祭祀区域的黄土台位置整体上是在环壕区域的中部略东,居住区东南,区域地势高,也符合有些时候会在东郊、东南郊祭祀太阳的古制。依据何弩先生的认识(何弩: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 ——以陶寺遗址为例,中国考古网,2013-11-04),石家河古城外东南角罗家柏岭遗址有“圜丘”、陶寺中期大城外东南部的中期小城内半圆形建筑 IIFJT1都有祭祀太阳的功能,于是我们判断,荥阳青台遗址这一更早的圜丘具备这一功能也是有晚期考古材料支持的。
依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圜丘之祭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其中的《云门》之乐舞,一般认为是黄帝时代之乐。《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晋杜预注:“ 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云门实际是出云之门,类似谷口,晋惠远《庐山东林杂诗》:“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闢。”唐马戴《早发故山作》诗:“云门夹峭石,石路荫长松。《文选·左思<蜀都赋>》:“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 张铣注:“言水自渠而灌田,故指渠口为云门,犹云来则雨至也。” 自然也类似云岫。这类云气之谷,应可称为云门。有这类祥云则即祥瑞,有四季之祥云则有符合规则的节气和风雨,这样的话,则有丰年。
至于冬至祭祀太阳的原因,若所述郑玄注、贾公彦、孔颖达疏。其实冬至祭太阳还有一个原因应是早期的传承:从考古学来看,古代有把猪与太阳予以关联的文化习俗,甚至以猪象征太阳。为了不让太阳在冬天一去不复返,就在冬至的时候祭祀以恭迎太阳开始回家。双墩文化、良渚文化中还出现过以绳子拴住太阳的图像,应是由于不希望太阳走掉从而拴住太阳之魂的巫术行为。
青台遗址北斗九星斗魁附近的黄土台,其附近约为距今5500年左右的北极星所在区域,其时极星应为天龙座a。当然那个时代其他地域和各个文化中或不同层次的人们也可能会有人把附近的北斗星视为北极星,只是青台这一天文图像的信息表明的这一区域人们这一时期所认为的北极星是天龙座a。
另,结合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那一时代的北极、北斗、天龙座a的相对位置图可以看到,整个天文图像中黄土台与当年的实际北极星位置不一,这似乎是设计建造的不特别严格使然,实际是尊重北极星的原因。商代卜辞及周代金文中讲,人间帝王死后在天帝左右,青台这一圜丘的位置恰好也体现了这一方面。濮阳西水坡M45的死者位于斗魁之上,其位置虽然无法严格论定,但是也应是在北极星附近的,而非北极星。
另,青台遗址北斗斗魁所向的圆形黄土台遗迹,原认为其应是三级象征性分层,但是经过综合判断和进一步发掘,该天文遗迹之圜丘虽然不完整,但是三层特征应该并不存在。不过从其可能位于冬至天文准线的角度以及整体为圜丘的特征看,这并不也不影响其是位于北极星位置附近、在该地点观测太阳以及其是冬至祭祀北辰、太阳等天神性质的圜丘等基本判断。我们知道三级分层的天文遗迹,有的拟合昆仑形。承文献所述,昆仑和圜丘都有特殊性,本身可以与天神像北极星和北斗神关联。陶寺天文观象台之观测点为三层及一周,陶寺天文观象台主体实际有一段三重台基、基址本身为蕴含天道、地器之阴阳气的太极形,也即是天地之中的造型和内涵。关于其与阴阳太极、天道、地器的讨论,参见何弩:《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 ——以陶寺遗址为例》一文。其文中还把陶寺台基S形与屈家岭有关彩绘纺轮予以关联。不过屈家岭纺轮彩绘旋臂更有可能是太阳光气,倒是高庙文化一件小陶罐罐底有一太极形符号,是由一人为的旋臂和一地纹旋臂构成的,与陶寺天文观象台之天地之中的太极形很类似,不知是否有联系。考虑到高庙文化太阳大气光象信仰高度发达,所以这一太极形可能还是理解为太阳的旋臂光气为佳。另陶寺观象台中心的观测点应该为三重土组成的蕴含三衡的天结构以及三层的昆仑结构,其外还有一周土地,一般认为是基础土,这一基础土与中间的三重造型可组成另一个相关的文化场地,即昆仑与其周围的弱水,与新石器早期的有关环壕聚落、有关古代有城池一样,还应蕴含明堂辟雍的概念。诸多纬书中都记载昆仑为地中,其上应北斗或北极。还有记载其为登天梯,实则是连接地中和天中的。红山文化的圆形三层祭祀遗迹是呼应包括天中的天的,良渚文化的方形三层或三重祭坛是呼应地中的,并且是一种巫术模型。陶寺天文观象台本身为三层,从其三重半径判断,也是宏观呼应三衡的天的,不过本身也具备昆仑特征,并且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特征高度相应,其观测点也具有这一特征。
詹鄞鑫先生总结文献和卜辞认为(詹鄞鑫:《禘礼辨——兼释卜辞“帝”礼及“宁”礼》,《中国文字研究》,1990年第一辑),周代应该有“冬至祭天”与“启蛰而郊”祭祀。他还认为圜丘祭天与惊蛰祭天来源和性质是不同的,冬至祭天是祭祀冬至太阳而报天的,惊蛰祭祀主要是保农祭天,郑玄等把“圜丘之祭”、“郊”视为不同是正确的,王肃认为禘祭与圜丘之祭及郊祭无关的认识也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认为,圜丘祭天的礼仪应该起源甚早,从青台遗址这一北斗九星、圜丘遗存看,至少在仰韶文化中期已经出现。同时参照詹鄞鑫先生在所属论文中对于禘礼以及郊祭的总结可以判断,距今5500年左右的圜丘已有祭天的功能,古代这一祭祀场地整体位于生活或者文化空间的南方也应是正确的。从青台北斗九星斗柄方向呼应冬至的情况看,这一北斗九星及圜丘主要还是用于冬至祭祀以北辰为主的天神的。
同时由于其时广泛存在以北斗授时和指导农业的情况,青苔这一祭祀遗存之祭祀,也应可能与郊祭保农的祭天之礼相关。这一时期可能存在圜丘冬至祭天及郊祭统一的情况。《礼记·郊特牲》载:“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由这些记载看,也可能存在郊祭时以其始祖之所由来宾祭的情况。
中国古代存在冬至祭祀祖先的情况,一般在宗庙、墓地及聚族而居的南方,青台这一以北斗九星和圜丘未中心的祭祀遗迹之公共能是否包括这一方面不易于论定。不过从同一方位的晚期,概在大河村四期的时候,该区域发现有一倒立的瓮代表和象征祖先的祭祀遗迹,附近还有相关墓葬祭祀,这可能有助于说明稍早的北斗九星及圜丘遗迹的功能中包括祭祀祖先。
商人不祭祀上帝,这是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认识,然而关于为何不祭祀,却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上帝可敬畏,是不可由人间之人来祭祀和交流的,有的认为其降好运与灾完全取不决于人间的祭祀,其运行超越人的层面,也无需人类祭祀。我们认为这一认识是较为有道理的。这有可能是商人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宗教心理。但是从龙虬庄五帝陶文及周代金文的记载看,相对于商代,早晚均有祭祀上帝的案例,所有青台这一北斗九星及圜丘的祭祀至少包括当时的北辰和北斗等神灵。
关于青台天文遗迹,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即视黄土台——圜丘位置可能即是接近天心的地方,又是接近地胆的地方,换言之即是傍依天地之中的模型。古人从心里和模拟巫术的角度认为于此地观测天垂象、制历法等,更为清晰和准确,于此地祭祀更权威和中正。之所以未在天心地胆观测,是古人以北极、北极星为尊的原因使然。当然这一圜丘无疑也是通天台。
荥阳青台遗址的这一北斗九星、圜丘等,显然属于一个精心制作的祭祀场,并经过一定的简单设置程序。从旁边的作为瓮棺的小口尖底瓶的时代及代表九星陶罐本身的时代看,应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范畴。时代距今大概5500年左右。这说明中原地区的古人早在5000多年前这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已清晰地建立了北斗、北极星和北极的信仰。若这一认识不误,则青台这一早期天文遗迹,为中国古代天人相依的人文宇宙观以及中心统一的社会文化观找到了早期的天、地、人关联之文化来源!
从濮阳西水坡M45号墓的与天文有关的图像看,其中也有北斗,其中的北斗斗魁一般认为是三角形,实际应近似四边形,只不过不太明显,应是制作不严格所致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学者以其为三角形从而判断其为十万年以前的北斗造型。冯时先生曾经复原过该星图,并识别了其中的北斗等星相。并且从其复原图看,死者的位置应该占据了理论上包括北极的位置。陆思贤先生也曾经判断该死者位在北极,并认为其拟北极神(陆思贤:《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华夏考古》1999年03期)。我们认为,死者位于这一地方,并不像陆思贤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比拟自己为北极神,自然也不是比拟为北极星神。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人间王者死了一般可以升天,但是只能在北极星附近或者北极星所象征的天帝附近,像商人、周人均是这样(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宏观上位在北极及其附近区域,或曰在璇玑之内,但是并不是在北极或北极星位置。商周时期,卜辞、金文及相关文献表明,人间帝王死后能够在天帝左右或帝廷),所以这一死者只能是人间的首领,并且可能是自认为或实际上权能和统治地位近似天下的王者。
从青台的这一天文及祭祀遗迹的发现看,其北斗与北极星、北极之间的位置关联与5500多年前的实际天象已达到非常近似的地步,这一位置关联与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死者和北斗的位置关联也较为一致。这一方面为冯时先生有关濮阳西水坡M45的盖天复原方法提供了更为朴素的天文论据,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人们确实是以天龙座a星作为北极星的,自然其附近即为北极了。
另外不少学者人认为濮阳西水坡M45的墓主是颛顼,从其时代为6400年左右看,也有可能呼应所谓的伏羲。
另在青台遗址该天文遗迹的附近还有四座瓮棺,我们初步认为其应与北斗九星有关的遗迹。其排列并不像濮阳西水坡M45的四子那样规整(冯时先生先生认为是羲和四子之中的三个,详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但也是围绕着整个北斗的,不过其有可能不属于同类现象,而是祭祀北斗的。
濮阳西水坡M45墓葬、青台遗址北斗、太谷白燕F504北斗、北极、商代殷墟晚期基址北斗七星陶尊、微山武梁祠黄帝斗魁等遗迹或汉画,清楚地表明天上之星官与地上之人事密切相关,尤其是濮阳西水坡后岗一期文化M45墓主位于北极、北极星位置附近的情况利于说明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存在以天地之中互相呼应的记载以及北极、极星与天下帝王宏观呼应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并且实物证据可以早到6400多年。 《吕氏春秋》言昌意“取蜀山氏曰妪,是为河女,所谓淖子也。淖子感摇光于幽防,而生颛顼”等北斗为神祖的记载都是这类天中星象呼应神祖、圣人思维的产物。
古人信仰天人合一,君权天授,所以历代帝王高度重视天的问题,《汉书·郊祈志》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这其中天中的天象尤其被重视。柿子滩北斗九星岩画、濮阳西水坡墓地M45、青台遗址天文发现表明,有考古学意义上的证据材料可以早到万年以前,实际应更早。以濮阳西水坡M45为代表的6400多年以前的后岗文化一期、以青台遗址北斗九星、圜丘等天文遗迹为代表的5500多年以来的仰韶文化中期、以牛河梁第五地点的红山文化晚期(其编为1号的三重圆形积石冢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以及以太谷白燕F504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早期或仰韶文化末期以来的发现表明,古人非常重视北斗、北极星、北极,这些早期天文考古学材料的发现,对于中国早期天文学研究和与其呼应的中国早期语焉不详的礼仪制度、精神信仰的内涵认识,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传:“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 孔颖达 疏:“七政,其政有七,于玑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谓日月与五星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史记·五帝本纪》:“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裴骃集解引郑玄注同此说。《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裴骃集解引马融注《尚书》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镇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考古发现表明,这类古人重视天中星象以及以人事法天象的现象确实是有早期文化来源的,《书·舜典》所谓的“璇玑玉衡”,历代有争论,看来确实还应该是北斗七星的称谓,至于七政,认为是日月五星也应是较为客观的。实际上即是以北斗七星主日月五星的,换言之,也即是历法整肃。
青台仰韶文化中期天文遗迹的发现尤其是北极、北极星附近圜丘的发现,以及濮阳西水坡M45的发现、太谷白燕F504的发现、殷墟基址北斗七星尊天文遗迹的发现,确切地表明古人不仅重视北斗,还高度重视北极星以及为北斗所围绕的北极。同时青台北斗天文遗迹与红山文化相关三层积石冢内涵非常一致。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冢体是一三层的圆形石坛。对于这一石坛的三重冢界石墙性质,学术界以往并未认真讨论,学术界以往讨论的多为与三衡相应的石坛。董婕和朱成杰两位学者慧识(董婕、朱成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辽宁科技出版社,2016年5月。董婕,朱成杰:《现代科技破译古老璇玑 牛河梁再现黄帝族新证》,光明网,2016-07-13 11:25:59),他们并未限定在红山文化圆形祭坛三衡的思维中,转而依据相关天文软件以及发掘报告关于三重冢墙直径数据,计算出其与公元前3600年立夏节中候天文昏影终这一时刻的北斗天象图非常相符,其中残存的三重冢界墙分别与天璇、天枢、天玑三星绕极轨迹圆周吻合,而且北斗最亮星玉衡也刚好与中心大墓主人的头部吻合,同时天极点也落在了中心石堆的中心附近。红山文化中又发现诸多三衡遗迹,这都表明红山文化的人们在理论上也高度重视天中、北极、北极星、北斗星问题。良渚文化中的三重或三层土台祭坛,也蕴含了地中,自然古人认为其上的空中在思维中也象征性地呼应天中。龙山时代陶寺天文观象台的南墙及三层夯土观象台基址组成天圆(三衡)地方的特殊组合,与著名的濮阳西水坡M45造型蕴含的宇宙观思维是一致的。至今明清天坛为圆形,其南边也有一墙,其人文空间依然是遵循天圆(其三层台阶应为三衡,不过天坛附近的祈年殿三层显然不是三衡。其原为方形地坛,明代以后改为今天的样子。其这样三层设计的思想,似乎与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冢体三层圆形界墙类似,分别与天璇、天枢、天玑三星绕极轨迹类同。不应视为是一种地坛似三层的表达,因为其是为圆形。其实北京天坛祈年殿为明清君主祭祀上帝之处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地方这一原理,只不过三层意义不一致,并且天坛是完整的三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早期祭坛上有祭祀坑,其中有石头,可能也是呼应天上的星象的。附近和祭坛上也有同时代墓葬,与良渚文化多数祭坛、红山文化多数祭坛类似。而青台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的这一天文遗迹目前也发现有瓮棺,不过不应是墓葬,而应视为祭祀。参照双槐树遗址墓地祭祀设施与墓葬的分布情况看,祭祀设施没有墓葬可能是中原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特征,崧泽等其他文化中也有这类祭坛,但不是主体。在青台遗址相当于大河村类型第四期的时期,在青台这一天文祭祀遗迹的位置,应该重新予以了治理,有相关祭祀现象,附近有对头墓葬,可能也是祭祀所为,而非祭坛墓葬。
所述各类天文现象表明,中国古代赤道星象体系的发展历程很早,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中道、中心、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始终有宇宙观这一重要原因。自然也表明所谓天中、地中、国中之互相关联的思维是传承有序、来自久远的!
另在5500年或5300年这一中华文明起源之重要历史时间段,东北、东南、中原都具有非常类似的天文观、宇宙观,并且考古学材料表明中原这一思维可以早到距今6400年左右。但从这一极其重要的精神思维角度看,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起点期,确实是满天星斗,但是始终都是向着北极的。换言之,这一宇宙观促使四方向中、中为天地之正的思维成为其时和历代中国的正统精神和代表政治思想,并且在自然条件影响、人地环境互动、生业规律制约和文化竞争融合的条件下,时代的引领者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努力实践着这一理想。

作者:顾万发
1971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主持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发现有大量高等级的新砦期遗存,后历任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院长。还兼任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郑州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