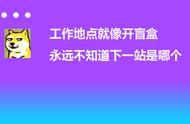“云梦”被称为“泽”已经是西汉中前期以后了,毫无疑问,洞庭湖的成湖与所谓的“云梦泽”是没有继承关系的,洞庭湖不是“云梦泽”的残存,孟浩然的诗应该使用了借代之辞。
洞庭湖得名于“洞庭之山”,《山海经·中山经》说“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位于“江渊”(河流回水区域,东洞庭湖最早的湖泊水体)和长江交汇地带(或为今天的君山),屈原的《九歌》中有“洞庭”,即“洞庭波兮木叶下”。

有洞庭之山方有“洞庭之野”,洞庭之野中的大湖即为洞庭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直接言明“湖即洞庭湖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四水就是湘江、沅江、资水、澧水,接着他又写道“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与其中”,其实郦道元没有到过洞庭湖,应该是综合他人关于洞庭湖的记载而写的,这时的洞庭湖仍处在扩大过程中。
八百里洞庭
洞庭湖的扩大,固然与洞庭湖区沉降有一定的联系,但本质上洞庭湖非构造湖,所以洞庭湖的变迁,与荆江的发育过程,及四水变化息息相关,就说荆江,在缺乏大堤控制江水形势时,一旦河水泛滥,就向两岸漫溢,呈泛滥平原特征,公元450-524年,荆江南岸的太平、调弦两口溃决,江水进入洞庭湖区,极大干扰了洞庭湖水系。

唐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是洞庭湖的全盛时期,所以唐诗宋词中的洞庭湖非常广阔,一眼望去浩瀚无边,有《岳阳楼记》中的“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之景观,洪水季节更甚,唐末至北宋,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加快,导致江水从岳阳城江口向南倒灌洞庭湖,五代的《北梦琐言》、北宋的《岳阳甲志》和《岳阳风土记》皆有描述。

浩浩汤汤
江水倒灌给洞庭湖区带来水量的同时,也输入了大量的泥沙,泥沙在湖底淤积,使湖水深度减小,最后导致了汛期时洞庭湖水面大为扩展,洞庭湖群连成一体,《资治通鉴》注引《巴陵志》有“(洞庭湖)西吞赤沙(湖),南连青草(湖),横亘七八百里”这一的景象,《太平寰宇记》也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