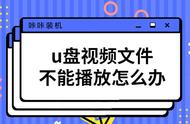但是绝不仅仅是在这一区域内才出现跨生态贸易。阿姆河的城市也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内印度进行贸易。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甚至可能和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最早在中国之外发现的丝绸是在大夏北部的萨帕利(Sapalli),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年。这对上一句的观点加以佐证。到公元前2000年,阿姆河文明成为跨生态和跨文明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覆盖了整个非洲—欧亚大陆。
诸如此类的证据佐证了最近有关丝绸之路的看法,“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已经有一条明确延伸至亚洲的贸易路线;并不是一条可由一个人完全走完的连续道路,而是由亚洲西部到中国之间一连串的贸易连接起来的近5000里远的道路。”这也佐证了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观点,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整个亚欧大陆被纳入到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之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世界体系联系着这两个相互区别的交流网络:一个是处于萌芽时期的跨文明交流网络,其中心是阿姆河文明附近的城市;另一个范围更广、形成时间更长的交流体网络则处于欧亚内陆草原甚至超过这一区域。
总而言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交流网络已经作为一个富有活力和覆盖广泛的交流体系在中央欧亚草原内部运作,有时甚至溢出这一范围。这个结论似乎是相当合理的。早期的交流系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牧社会。正如弗兰克和布朗斯通所指出的:“在很早的时候,游牧民就将铜制品、锡制品和绿松石从伊朗带到了城市,也从蒙古的阿尔泰山带来了黄金,从阿富汗带来了青金石和红宝石,从西伯利亚带来了毛皮,从印度带来了棉花,以及游牧民自己的羊毛、兽皮和牲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描绘出了穿越亚洲的主要路线,丝绸之路就在其中。
古典时代的丝绸之路
一旦意识到这些交流网络的深层根系(deep roots)和游牧民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对古典时代丝绸之路历史的标准解释进行严格反思。
我们已经看到对丝绸之路起源的标准历史解释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中亚之间国家支持(state-sponsore)的贸易。这种贸易类型的发展当然是重要的,并且其被保留在了文字材料中,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它们能稳固地存在于丝绸之路的历史编撰之中。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转换到内亚草原,并且更多地运用考古证据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活跃的跨欧亚交流体系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汉武帝如同之前的阿契美尼德人和马其顿人一样,仅仅是通过武力介入已经建立起来的跨欧亚交流中。
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千年,草原内的交流体系就在不断增强。最令人瞩目的证据就是新技术和艺术风格在草原上的传播。
我们所说的“斯基泰”(Scythic)生活方式从中部草原向外传播。曾在黑海北岸遇见过斯基泰人的希罗多德就描述了这种生活方式。希罗多德给出的描述与中央欧亚的状况是相同的。斯基泰风格的图案、伊朗风格的地毯以及显然是中国仪式上所用的二轮战车在图瓦(Tuva)附近的巴泽雷克(Pazyryk)——公元3到4世纪的一座坟墓——的发现,表明了甚至中央欧亚草原深处的社会在公元前1千年就与丝绸之路的两端相联系。
斯基泰文化也对周边农耕文明施加了压力。公元前2千年对印度的入侵仅仅是公元前1千年对伊朗入侵的先导。到了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遭到草原民众周期性的攻击,最后一代入侵者成为了地方统治精英,建立了米底王国(Median)和波斯帝国。
在草原世界的另一端,华北列国于公元前4世纪已经引入了骑兵作战方式来应对游牧民从北部带来的军事压力。这些游牧民已经有了许多斯基泰文化的特征。与草原联系的增多也反映在骑兵作战传播到草原之外、雇用草原骑兵以及草原贸易增多这些历史现象上。在与草原的贸易中,游牧民用马匹和牲畜交换诸如丝绸或者陶瓷这些大型农耕文明才有的物品。

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在草原的出现,加速了交流的进程。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泰商人通过当地人进行远途贸易。交流网络可能已经覆盖到阿尔泰山,我们在那里的巴泽雷克坟墓所发现的貂皮衣服和黄金表明在鲁滨逊(Rubinson)所称的“毛皮之路”上存在着繁荣的贸易,并联系着西伯利亚和中国。而这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就出现了。
刻赤半岛对于希腊人和斯基泰人的重要性则表明了顺着顿河通往伏尔加、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的草原道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在商业上具有吸引力。然而,这些早于希罗多德时期,通过草原覆盖到从斯基泰到阿尔泰的中继贸易体系并不能常规化地或者系统性地运行,因为在斯基泰所发现的来自于中亚或东亚的物品很少。
相较于斯基泰人建立的各种政权,匈奴建立了实力更为强大,组织更为完善的草原帝国。这一时期关于草原贸易的证据就更为广泛了。
汉武帝的使者张骞抵达中亚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一些中国的物品已经在中亚广为流传,其中包括一种特别的中国竹子。安息商人在公元前150年将中国的丝绸销往希腊。这些物品运输过程中可能穿过了匈奴控制的新疆地区,或者从中国运往印度再到达中亚。无论哪一条路,我们都可以确定匈奴与新疆地区(他们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公元前2世纪)进行贸易,并且从中抽取贡赋。但是他们也控制了中亚的交流体系,并很有可能也获取贡赋。
在蒙古北部,公元前1世纪的诺颜乌拉(Noin-ula)墓地中所发现“羊毛织品、挂毯和刺绣,都是从粟特、大夏和叙利亚带来的。从汉帝国到南方,大量各种丝绸衣物、刺绣、含棉丝织品、漆器和青铜首饰都被运往匈奴王庭。”公元前2世纪汉朝运往匈奴的大量物品,大部分是两个政权朝贡关系确立后以贡赋的形式实现的。这也意味着,并非汉武帝而是匈奴的伟大领袖冒顿单于开启了公元前最后一个1千年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对新疆的控制真正导致的是丝绸之路当中的一条新的线路被开发了出来,这条路线避开了匈奴控制的蒙古。如同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中亚的占领,其实质依旧是农耕帝国企图控制更大范围的贸易路线的尝试。这些路线主要穿过欧亚内部的草原地带,往往也由游牧民所控制。农耕帝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利益增长,无疑活跃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无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是汉王朝都提高了其所控制之下的丝绸之路沿线的舒适和安全程度。
但是农耕文明没有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相反,甚至在公元前最后一个1千年,游牧民对于丝绸之路的运转依然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够直接控制丝绸之路的政权还是来自游牧民:安息,匈奴和月氏。此外,即使是在文明间贸易活跃的时期,依旧有大量的贸易经过草原进行。例如,在汉武帝破坏了匈奴对丝绸之路的垄断并且在新疆建立了自己的贸易路线之后,穿过草原的贸易路线依旧维持了下来。公元前81年,汉朝官员评论道(这篇文章中虚假地表示中国对于贸易不感兴趣):
“一匹朴素的丝绸就可以换取匈奴好几块黄金,因此也就消耗了敌人的资源。骡子、驴和骆驼沿着通畅的道路进入边疆;马、带有斑纹的马和枣色马也能够到我们手中。黑貂、旱獭、狐狸和獾的毛皮,多彩的毯子和装饰用的地毯,翡翠、幸运石、珊瑚和水晶充斥着帝国府库。”
草原在唐代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如我们所见,丝绸之路常被认为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实现复兴。事实上,唐代建立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复兴,并且要归功于强有力的游牧统治者,也就是突厥人。他们很可能继柔然之后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唐朝和突厥都与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粟特商人则从他们先辈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就控制了类似的跨生态交流。毫不夸张的说,在蒙古人的保护下,丝绸之路延续着繁荣。蒙古人绝不仅仅是中原王朝或者波斯的代理人。在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高原深处的帝国首都哈拉和林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停靠站。
向北扩张
关注丝绸之路的跨生态部分也表明了丝绸之路在最近一千年所具有的历史特点。
莫里斯· 罗萨比(Morris Rossabi)已经谈到,即使丝绸之路传统的跨文明路线从16世纪以来陷入衰退,但是跨生态的路线则并不如此。相反,跨生态路线继续繁荣了下去,也引导草原北部新路线的产生。这些更北部的贸易路线所具有的特质,在奥德丽·伯顿(Audrey Burton)那里已经被详细谈到。
罗萨比认为,北方的这种转变是由传统路线的中断造成的。但是聚焦于丝绸之路跨生态的性质,则可以发现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支配跨生态路线地理环境的生态边疆(ecological frontiers)自身发生了转变。这种生态边疆近两千年来所发生的转变,是与公元500年以后被我们称为罗斯人(Rus)的土地上农耕的出现紧密相关的。随后的一千年,进一步从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展。
正是农耕的传播以及大片的定居人口在草原北部的出现,正是新的、更偏北的丝绸之路支线得以出现的原因所在。游牧或者半游牧统治者发现,在北方有着和南方一样多的农耕群体,而部分人打算对这种公元500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开发。
这种生态边疆的变化是有着证据支撑的。
首先,乌拉尔山西部很长时间以来就与西伯利亚的森林群体有着少量的贸易。10世纪的中亚学者阿尔-比鲁尼(al-Biruni)描述道,这一“不为人知的贸易”联系着伊斯兰商人和“Yugra”(现在的汉特人(Khanty)和曼西人(Mansi)):
“在最远的地方,那些七重风土的人们,生活在Iura国(例如Yugra国)……(旅行者乘着)木质雪橇,装载着物资,由人或狗拖行;而(他们)也坐在其他骨制的(滑行载具)上(旅行),靠着它在短时间内进行长距离旅行。因为这里的荒凉以及商人的胆怯,Iura进行的贸易采用的是将物品放置在某个地方等人拿取的方式。”
然而在公元1000年结束的时候,罗斯人的大量增加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开拓的方向,从中亚穿过哈萨克斯坦和伏尔加河直抵波罗的海。
在近期的钱币学研究中,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已经发现7世纪时阿拉伯银币在上文提及的区域中流通。部分基于新的贸易系统所产生的收入,刺激了新的政治系统的产生。也正是在贸易扩张之下,7世纪中期可萨帝国才得以建立。以如今的达吉斯坦为基础,可萨帝国一路扩张成为9和10世纪最伟大的帝国之一。而该地区在此之前则没有一个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政权。
起初依赖于他们的游牧军队,其后逐步将权力的重心转向贸易。从途经中亚、高加索、庞蒂克草原、俄罗斯森林和波罗的海的商贸中获得收入。在公元8或者9世纪的某些时间里,可萨统治者改宗犹太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拉唐人”(Radanite)(译者注:即说拉丁语的犹太商人群体)控制着可萨帝国的贸易,甚至如伊本·库达德本(Ibn Khurdadbeh)所相信的那样,整个丝绸线路(Silk Routes)都被犹太人所控制。
在公元9世纪可萨人的北部出现了两个政权:伏尔加不里阿尔汗国和罗斯汗国。如同可萨帝国那样,这两个政权也是由对开辟贸易路线感兴趣的军事精英所领导的。这是因为贸易在农耕群体出现于北部出现之后就变得繁荣起来。两个政权都曾作为可萨帝国的属国,但最终都实现了独立。而随着公元10世纪罗斯政权的*,两个政权结盟实现了对波罗的海到拜占庭商路的控制,绕开可萨帝国,凭借自身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跨国力量。

罗斯全盛时期的疆域
在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金帐汗国——蒙古帝国后裔——控制了从中亚到东欧和波罗的海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
15世纪时,一个新的扩张时期开始了,实现独立的俄国向外扩张到乌拉尔山。俄国的扩张引发了农耕群体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向西伯利亚南部边界移民。这为该地区在之前小规模的森林劫掠者和草原游牧者的交流基础上,跨生态交流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公元16世纪以来,拥有长期内亚贸易经验的布哈拉商人,在与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亚商人从罗斯人的政权建立以来就沿着伏尔加河与乌拉尔西部进行贸易。并且在金帐汗国的穆斯林统治者控制这一地区时期,中亚商人就十分活跃了。在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中,他们也依旧活跃。在俄国分别于公元1552年和1556年控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布哈拉商人开始更为频繁地直接与俄国交易。
从公元16世纪商人的代理人就已经从中亚前往俄国,偶尔也有商人从俄国前往中亚。16世纪末期,当西西伯利亚在库楚可汗的控制下时,布哈拉商人就很愿意与这一地区进行贸易。17世纪早期,在该地区受到俄国势力控制之后,这样的贸易依旧延续。
公元17世纪,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通常以布哈拉商人为中介,他们对俄国到中国的主要道路很熟悉。部分路线是对传统路线的延续,从伏尔加到中亚之后再抵达新疆和中原就是如此。一些路线则重新与丝绸之路在中亚东部的道路相接,例如穿越西西伯利亚抵达额尔齐斯河。其他的路线则与传统路线没有关系,比如从蒙古去往库伦,或者完全从西伯利亚穿过,抵达涅尔琴斯克然后再穿过蒙古。
伯顿(Burton)列举了布哈拉商人的贸易路线:穿越花剌子模和哈萨克草原抵达阿斯特拉罕的进入俄国的路线,或者从里海航行到伏尔加河再到达撒马尔罕与喀山的进入俄国的路线;前往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克、叶尼塞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些西伯利亚城市的路线;通往伊朗和土耳其的路线;通往印度的路线;通往喀什噶尔和进入中原的路线;进入哈萨克与蒙古的路线。
丝绸之路网络向北方的扩展和密集化并不仅仅是中亚商人的选择偏好,从更深层次来看,它反映了欧亚内陆生态地理环境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出现了游牧民和农耕民之间的第二个跨生态边疆。这一边疆位于欧亚内陆草原的北部边界上。
结论:丝绸之路和全球史
本文对丝绸之路地理和历史书写的修正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超过了丝绸之路甚至是其所经过的众多社会的范围。对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跨生态和跨文明交流的探索,主要目的是表明由丝绸之路所维系的交流不仅年代久远,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比通常所理解的更广。如果这个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非洲—欧亚大陆的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这表明,非洲—欧亚的不同区域——农耕文明区域、游牧区域或者森林狩猎采集文化——都在进行着思想、语言、物品、纹饰图案,可能还有疾病的交流。
这一结论强化了弗兰克和吉尔斯对于非洲—欧亚可能在公元前2千年以来就属于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的理解。同时也表明,同霍奇森很久以前以及弗兰克最近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像传统欧亚大陆那样的历史编撰,也就是将视野集中在各个不同的部分或者欧亚的“文明”区域,是一个重大的误解。相反,为了理解欧亚大陆每一个部分的历史,就需要看到,在每一个部分的背后是一个单一的非洲—欧亚大陆的历史。这与诸如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或者大洋洲那些其他世界区域的历史是不相同的。因为非洲—欧亚众多社会共享了许多重要的因素,而这源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流。
非洲—欧亚大陆不同部分所共享的东西具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暂时性的初步清单。因为强调非洲—欧亚历史的一体性,我们就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历史地图。
作为草原之路沿线交流的结果,非洲—欧亚大陆共享了次级生产革命的许多因素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包括畜力在农耕、运输和战争中的使用以及对动物毛皮的利用。在随后的时期,包括复合弓和弩的使用,骑兵作战中盔甲的使用,围城作战的技术以及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使用,都在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广泛传播。
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同部分也共享着宗教文化,其中有可在拜火教、道教、苏菲主义、摩尼教、佛教和部分基督教形式(根据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中发现的萨满教因素。也存在着包括在拜火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为直接的宗教交流。
物质文化方面,非洲—欧亚大陆也共享了许多物品,包括丝绸、地毯、金属制品、陶器、毛皮和牲畜产品。
文化和艺术风格方面,斯基泰艺术或者伊朗文化模式都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萨珊王朝时期甚至远及日本,覆盖了非洲—欧亚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我们已经知道,印欧语可能从欧亚内陆西部的某个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传播到欧洲、印度北部、中亚、伊朗甚至新疆。在此后的两千年,突厥语从相反的方向进行传播,取得了相似的成果。
最近在新疆发现的明显是欧罗巴人种的木乃伊,显示人类和他们的基因也沿着丝绸之路广泛移动和传播。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指出的,非洲—欧亚各个社会,部分因为利用牲畜上的相似,感染了许多源自于牲畜的疾病,但是这种交流同时也确保了他们对这些疾病共享了免疫力。
麦克尼尔已经证明了十三世纪的大瘟疫是源于非洲—欧亚不同地区之间的病菌传染。事实上,这一周期性的病菌传播帮助解释了十分重要的欧洲人口变动问题,包括在公元1千年上半叶的人口下降和黑死病之后的人口下滑。这个共享的免疫系统也帮助解释了随后欧亚殖民主义的成功,尤其是在美洲和大洋洲。那里的人口由于对欧亚大陆的疾病没有免疫,所以在第一次与欧亚人群接触之后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最后,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至少在非洲—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就共享着贸易循环。
因为许多重要的事物并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交流,所以并不需要过度强调上面的结论。事实上,丝绸之路受到不同群体的控制,既有游牧群体也有农耕群体,他们参与到了漫长而又复杂的交流传播当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非洲—欧亚并未比之前更进一步整合在一起。其中之一就是精确的地理知识和文化知识并没能沿着丝绸之路很好的传播。这可能是因为在蒙古帝国之前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完整地走完丝绸之路。
关于丝绸主路两端相互之间的误解有着许多例子。
普林尼(Pliny)在公元70年的作品《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将丝绸描述为在中国的树上长出的羊毛,并称赛里斯人(Seres)有着红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也提到了丝绸之路的中间商——月氏人。
鲍桑尼亚(Pausanias)在公元2世纪写到,丝绸来自于一种蠕虫。
阿米阿努斯(Ammianus)在公元4世纪仍然坚持丝绸是在树上结出来的。直到公元6世纪拜占庭获得并开始饲养桑蚕的时候,关于丝绸的知识才传到地中海地区。
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对中国描述的广为接受也暗示了西方长时间对中国的无知。同时,中国的材料也同样显示出对地中海世界的无知。
我们知道,虽然从公元前100年以来中国和安息之间就相互派遣使者,然而在古典时期,没有一个中国旅行者完整走完丝绸之路。公元前97年,班超再次控制了西域之后,派遣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抵达了接近所谓的大海(great sea)(可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条支后,安息官员希望保持他们对与罗马之间的贸易垄断,以路程漫长为由规劝甘英。他们告诉甘英,到达罗马还需要至少好几个月甚至可能花上数年,许多人在思乡病中丧生。于是,甘英返回中国,史料中也没有别人继续他的旅程的相关记载。直到了蒙古帝国时代,商人穿过整个丝绸之路已经司空见惯。
奇怪的是,反而是由于丝绸之路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误解,才被现代历史编撰所保留了下来,才造成了对非洲—欧亚历史的根本性一体化这一观念的难以接受。
正是这些限制了非洲—欧亚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传统的历史编撰也都着力于关注非洲—欧亚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即使如此,对于诸如丝绸之路这样长时间以来连接非洲—欧亚不同区域对象的细致研究,表明了必须重视非洲—欧亚根本上的历史统一性,并开始建构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和连贯性的非洲—欧亚历史。这样的历史建构可以对历史编撰的许多领域构成影响。
弗兰克最近的作品已经说明了将非洲—欧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会产生怎样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编撰结果。正如其在《白银资本》中说到的,现代性的生成最好被视为丰富的经济和技术协同的产物,并且这一协同在欧亚大陆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而不是某一特殊地区文化或者“文明”的独特产物。这一协同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其巨大的范围产生于非洲—欧亚世界内部,是对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巨大体量和其多样性的直接体现。对此的理解将会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性是生发于这个体系之中的,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马歇尔·霍奇森在其1967年出版的作品中也表达了相似观点:
“第一座城市,文化生活(literate life)若是没有那些习惯各异、创意不同的社会中或主流或支流的无数人的积累,是无法出现的。所以现代文化的巨变是以东半球所有城市人口的贡献为前提的。不仅是无数生活所必须的发明和发现——其更早时期的基础并不在欧洲,也是许多相当稠密、城市人口占据主流的广阔区域,他们通过区域间的商业网络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是在东半球逐步形成的。也正是在这里,欧洲的命运被塑造,欧洲的想象力也得到了训练。”
对这番激烈的言辞所需的唯一修改就是,游牧民在霍奇森所描述的这个交流体系中一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游牧民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一16世纪之前最大的单一交流网络,并且在其运行中一直扮演核心角色。如果霍奇森和弗兰克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视现代性为一个复杂协同的产物,这个协同产生于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巨大的、古老的交流系统中。
(本文原名为“Silk Roads or Steppe Roads? The Silk Roads in World History”,中译文刊载于《西北民族论丛》(周伟洲主编)第14辑(2016年)。限于篇幅,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