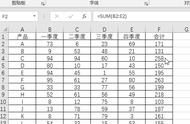正当人们的心情随着新冠疫苗的进展与挫折而跌宕起伏时,不妨看看另一种更加烈性的传染病埃博拉疫苗的历史。传染病无国界,但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却因暴发时间、影响范围和死亡人数而天差地别。
撰文 | 李一樱
责编 | 朱力远
来源:端端酱

在刚果(金)戈马,工作人员正测量一名年轻人的体温。(新华社丨法新丨图)
传染病的出现和消失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2020年6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于当日宣布,在西北部的赤道省姆班达卡市附近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该国卫生部提供的初步信息是,截至当日发现了6例埃博拉病例,其中4人已经死亡。谭德塞表示,这提醒人们,2019冠状病毒病并不是唯一的健康威胁,尽管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上,但世卫组织仍在继续监测和应对许多其他的健康紧急情况。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大暴发始于2013年底,这也是自1976年该病毒首次发现后暴发的最大规模且最复杂的疫情。疫情首先在几内亚一个小村庄发生,一名18月大的男童突发怪病,发烧、黑便和呕吐2天后便死亡。但直到2014年3月,才被确认为埃博拉,随后疫情通过陆路边界传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是一种罕见但往往可能致命的烈性传染病病毒,病毒潜伏期长达21天,通过野生动物传染到人,并在人际蔓延,平均致死率约为50%。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复杂,包括发高烧,伴有乏力、头痛、肌痛、咽痛等,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等,发病第3天后会出现持续高烧,中毒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出血,甚至会出现意识障碍、休克及多脏器衰竭。
自发现以来的四十多年间,埃博拉始终是全球的健康挑战,仅2013-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就导致了11300多人死亡。和新冠病毒一样,由于没有特效药物,接种疫苗才是保护所有人的唯一途径。
埃博拉疫苗的诞生看上去是一个传染病大暴发时期各界联合协作的完美案例。
被广为传颂的故事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再次在西非暴发,全球顶尖科学家再次开始讨论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应对方法,其中一位便是加拿大科学家盖瑞·库宾格(GaryKobinger)。他和团队潜心研究的埃博拉疫苗成果赢得了加拿大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认可,并被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临床试验。
疫情让临床试验超乎寻常地顺利:2014年至2016年,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末期,该疫苗开始在几内亚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证明免疫效果显著,只接种一剂疫苗的五千多人随后均无感染病例。
2016年12月,多个机构的科学家联合在《柳叶刀》(Thelancet)发表文章,公布对这款疫苗进行试验的结果:有效率100%。2019年11月,欧盟宣布这款埃博拉疫苗获得上市许可,成为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仅比欧盟晚了一个月,美国FDA便批准了这款名为Ervebo的减毒活疫苗在美国上市。
不仅如此,该疫苗还创造了世卫组织有史以来最快疫苗资格预审纪录,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一次重大成功”。
但背后的事实是,埃博拉病毒已经发现四十余年了,科学家们对病毒本身和疫苗研发早在多年前就已有重大突破。一切皆因埃博拉病例散发,又只集中在刚果、加蓬、苏丹等非洲的几个医疗条件基础极差的国家,没有公共或商业机构愿意投入支持,致使疫苗的面世拖延长达数十年之久。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曾有一种相当刻薄和带有歧视色彩的说法:“距离埃博拉病毒治疗方法/疫苗的面世还有五十个白人患者的距离”。这听起来对非洲人民相当不公平,但回顾这一疫苗的研发历史,的确如此。
1 从德国到加拿大,关键的疫苗载体被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发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1967年秋,德国马尔堡和法兰克福以及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的几所实验室工作人员同时暴发了一种严重的出血热疾病,31人发病,7人死亡。流行病毒调查的结果发现,暴发的病毒源头是实验室里从非洲乌干达进口的一种用来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带病毒猴。之后,这一出血热疾病以发现地命名为马尔堡病毒(MarburgVirus)。
9年之后的1976年,同属丝状病毒科的兄弟——埃博拉病毒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尽管十分罕见,但两种病毒均会引发后果极为严重的高致病性新发传染病。彼时,科学界尚未开始正式研究马尔堡病毒或埃博拉病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刚到马尔堡的学者汉斯·克伦克(Hans-DieterKlenk)注意到了这类新病毒,并建议他的学生海因茨·费尔德曼(HeinzFeldmann),可以试着把研究方向从流感等常见病毒转向这类烈性病毒,两人一拍即合,奠定了费尔德曼之后研究埃博拉病毒的重要基础。
到了1990年,耶鲁大学的一名科学家约翰(杰克)·罗斯试图以*水泡性口炎病毒(Vesicularstomatitisvirus,VSV)为基础,作为疫苗的载体平台。尽管水泡性口炎病毒(VSV)可以导致牛群患上口部疾病,但很少感染人,也不会让人感觉到不适,诱导抗体的水平出奇地高。
罗斯设想,如果可以将这一病毒作为流感、HIV等病毒的疫苗载体,教会人体识别有害的病毒,同时又对人没有伤害,将会在新疫苗研发上取得巨大突破。
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罗斯的天才设想。
有人把这种制作疫苗的技术形容为“披着狼皮的羊”,即把想要预防的病毒表面的蛋白加载到没有什么威力的病毒表面,无需额外的佐剂,便能让载体诱导产生人体的免疫应答。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利用病毒载体来研发疫苗是可行的,包括已经成功的登革热疫苗,但在当时这是极为创新的想法。
之后六年时间,罗斯和他的团队在反复失败之后,终于在以VSV为载体的流感病毒上取得了成功,他们以此为基础的流感病毒疫苗只一剂就让小鼠得到了免疫保护。“抗体表达太优秀了!”罗斯感叹。很快,将VSV作为一系列病毒的疫苗载体,用于包括禽流感、麻疹、SARS、MERS等,都取得了成功。
罗斯据此认为,从理论上说,这对埃博拉病毒也一样有效。
但实验始终未能开启——作为生物危害最高级别的病毒,没有相匹配的高度安全的实验室就无法对它进行研究,因而埃博拉相关的*病毒疫苗研究被搁置。
很快,这一载体专利被授权给惠氏公司,并和全球一百多个实验室共享。有了这一创新载体,科学家们有机会将单个的埃博拉病毒基因搭建在VSV上研究,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性价比高,极大地方便了研究工作。
到了1999年,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性不断升级,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开始筹建,其中包括研究埃博拉病毒所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前面提到的马尔堡大学病毒研究所的费尔德曼教授也从德国被聘请来领导旗下的特殊病原体研究小组——他正是当年在德国研究VSV载体的研究组成员,也是最早开始研究埃博拉病毒的科学家之一。
2 动物实验的成功费尔德曼离开德国前往加拿大时,被准许带走了一些病毒样本,为他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在温尼伯最高级实验室里,费尔德曼和他的团队终于有机会真正实验VSV载体在埃博拉病毒上是否有用,他们发现,未经注射埃博拉病毒VSV抗体的小鼠在面对埃博拉病毒时全部死亡,而注射了抗体的小鼠安然无恙。
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动物试验中首选会表现出与人类疾病相似症状和特征的动物,小鼠或猴是最常见的试验物种,特别是非人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的生理模型、组织结构和免疫应答等性状与人类十分相近。
小鼠试验成功后,费尔德曼他们本应进入到更高级别的动物试验时,新的威胁来临了。
2003年,一种全新的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后被命名为SARS的传染病,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出现,并向外蔓延。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立即加入进行研究。
但与费尔德曼合作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盖斯伯特 (ThomasW.Geisbert) 没有停下来,继续从灵长类动物身上找寻更多证据。他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的埃博拉病毒专家和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者之一。
之后,加拿大与美国两个实验室合作,证明了VSV载体的埃博拉疫苗在食蟹猴上获得了完全的保护,且疫苗诱导了明显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
2005年6月,这一研究结果在顶级期刊《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上发表,该研究成果首次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上验证了基于VSV载体的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可行性,而且只需免疫一次即可获得快速完全保护,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验证了,该疫苗在病毒暴露后预防的作用。费尔德曼等人发现在豚鼠和小鼠被攻毒24小时后接种基于VSV载体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可以实现50%和100%的保护,远超腺病毒载体疫苗30-60分钟的保护期,甚至在恒河猴被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暴露后20-30分钟内接种也实现了50%的保护,而被苏丹型埃博拉病毒攻毒后20-30分钟内接种可实现100%的保护。
关于这一研究的褒扬不断,至此,科学家们终于能确认,利用VSV装载病毒的模型不仅安全,还可以有效地作为多种疫苗的研发基础。
“埃博拉疫苗的大门真正被打开了。”盖斯伯特和整个团队都对此非常兴奋,并在当时对媒体宣布,这款被命名为rVSV-ZEBOV的埃博拉疫苗可能会在两年之内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等到2010年或2011年,就能走完全部程序上市了。
3 临床开发遇冷从科学上说,这一发现是让人极其兴奋的。但在现实中,这连开始都算不上。
很快,盖斯伯特就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
“我们的研究结果太令人兴奋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当被问到他们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时,费尔德曼略带无奈地回答媒体,“不过只是去隔壁酒吧喝了杯酒,然后再回去工作。”
“没人愿意投入开发这一疫苗。”他补充道。
在加拿大,特殊病原体研究项目一直被政府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每年预算季一到,这类研究总是属于政府节省开支精打细算的项目。从2004到2014年的十年间,每到预算季,加拿大温尼伯微生物实验室时任科学总监弗兰克·普拉默(FrankPlummer)不得不一遍遍回应政府的质问,为什么加拿大需要研究埃博拉这类本国根本没有的病毒。
业内人士承认,没能对这一颇有前途的候选药品进行后续研究,映衬出了更大的失败:穷国的民众饱受某些疾病的折磨,但针对此类疾病的药物或疫苗却无法被生产出来。
与治疗疾病的新药不同,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预防疾病的特殊药品,其安全有效性的评价将始终贯穿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中、上市后评价的各个阶段。
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线,一支疫苗从研发到上市,一般需要5到20年,例如流感疫苗(14年)、天花疫苗(26年)、脊髓灰质炎疫苗(20年)、登革热疫苗(20年),大部分疫苗的研制都超过了10年,花费则超过10亿美元。
加拿大温伯尼实验室所做的只是疫苗研发重要的前半段——利用不同动物验证疫苗的长期毒性、过敏反应、生殖毒性等安全性评价指标,也称“临床前研究”。但一种新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最大也最关键的步骤是人体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流程,一般需要由制药企业来推动完成。
对于制药行业来说,这是“注定赔本的生意”。2010年代,埃博拉病毒发现已经快三十年了,但造成的死亡也仅有上千人,且集中在非洲的几个小国家。且不说任何一种新药和疫苗都需要巨额的投入,即便进行了巨额投入,这些受到病毒侵害的国家也可能根本买不起疫苗或药物,需要制造这一疫苗的企业通过某些公益项目无偿捐赠。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很难对这样一种罕见且仅在贫困地区出现的传染病有研发意愿。
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丽敏等人的一篇埃博拉病毒研究论文也指出,疫苗接种为传染病常规的防控手段,但目前埃博拉病毒疫苗没有上市,其原因是该病发病稀少且受地域局限,研发疫苗缺少经济价值而无法引起疫苗研发企业的重视。
4 一场实验室意外德国实验室的一场事故,意外地成为埃博拉疫苗的人体试验和紧急使用的绝佳案例。
2009年3月12日,一名德国研究者在P4实验室接触埃博拉病毒时刺到了手指,尽管当时没有出血,但她戴着三层手套的皮肤被刺破了。她被紧急带往汉堡大学医学中心,并与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人员联系,看看是否有挽救措施。
经过多轮风险评估,研究人员列举了9个关键点,认为应该立即接种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研发出的埃博拉疫苗(rVSV-ZEBOV),她本人也同意。此前的一些动物试验表明,在接触病毒的48小时内接种,仍然会产生抗体,但在这位实验室人员之前,该疫苗从未在人体身上接种过。
因为烈性病毒的致死风险,加拿大政府同意提供这种实验室疫苗,装有疫苗的包裹在第一个电话会议结束后从加拿大发出,3月14日上午抵达汉堡。事故发生的48小时后,该研究员在隔离舱内接种了这一疫苗。她本人也随之成为研究人员密切关注的受试者。
3月15日,该研究员出现发热和肌肉疼痛,医务人员没有对她进行治疗,他们希望确认这是由于感染埃博拉病毒症状发作,还是注射疫苗后的常规不良反应。当晚她的发烧减退,之后被严密监测的21天内,她没有任何埃博拉感染症状,最终平安出院了。
直到今天,科研人员仍无法确认该研究员究竟是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还是有了感染但被紧急使用的疫苗拯救了,尽管多数人倾向于相信她没有感染。
但这场跨越国界的紧急使用给埃博拉的人体试验奠定了基础,也证明了该疫苗在人身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直到2014年,美加两国科学家研究出的VSV埃博拉疫苗始终没有走出实验室。对于所有为这一疫苗付出心血的研究者来说,这仍然只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科学想法而已。
其间,为了推荐这一研究最终上市,温尼伯实验室将这一模型申请专利,并将这一载体授权给了惠氏公司。之后,他们开始大规模寻找药企合作,希望推动疫苗进入到临床开发阶段。
谈了大大小小无数个公司后,只有一家名为BioProtectionSystemsCorp.的小公司(NewLinkGenetics的子公司)感兴趣,以20万美元的低价将专利权买走,宣称将推动这一疫苗进入到临床开发阶段。不过对于BioProtection来说,这只是一个增加他们资产组合的商业决定。BioProtection后来被LumosPharma公司收购,且它们从未推动过埃博拉疫苗的临床开发。
“埃博拉疫苗的市场需求一直不大。如果大量生产,他们要卖给谁呢?”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者之一盖斯伯特教授很明白,“有时候只有更大的危机来临,才能引发人们讨论。”
几年之后,盖斯伯特一语中的。
5 新的暴发来临如开头所述,最新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是在2013年底。一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霍乱,直到2014年1月,死亡男童的几名直系亲属也出现了类似疾病并随之死亡,多名医务人员也被感染致死。

刚果(金),一名埃博拉感染重症患者在当地创新性的隔离棚内。Finbarr O'Reilly 丨The New York Times
根据世卫组织的回顾,多个因素导致这次疫情被低估了。尽管病例已从几内亚输入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但没有人认识到这是埃博拉病毒,更没人正式报告给世卫组织,这两个国家的疫情都先是静静发生了数周,直到传播链大量增多、病毒进入首都和省会城市,并且由于感染人数众多已难再追踪时,才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014年3月21日,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法国里昂的巴斯德研究所确认病原体是一种丝状病毒,并将诊断范围缩小为埃博拉病毒病或马尔堡出血热。
第二天,实验室确认病原体是扎伊尔种属,是埃博拉家族中最致命的一种病毒。同一天,几内亚政府向世卫组织发出关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预警,当时对疫情的描述是“迅速发展”。
3月23日,世卫组织网站在公布了疫情,当时官方报告有49例确诊和29例死亡,在这一周结束前,疫情已经从乡村蔓延到了城市,几内亚的首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又一位关键人物盖瑞·库宾格(GaryKobinger)出现了,他不仅研发了一种埃博拉的治疗药物ZMapp,还推动了埃博拉疫苗真正进入临床试验,并最终走向成功。
作为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部门负责人,他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世卫组织,希望能将该实验室之前研发的rVSV-ZEBOV疫苗投入使用,帮助西非遏制疫情。
世卫组织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理由是实验室药物太不成熟,无法此时用于人体。之后,另一款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发并进入到临床阶段的埃博拉候选疫苗 (cAd3-ZEBOV) 也同样遭受了世卫组织的拒绝,“没有人对该疫苗表示出兴趣”。
但盖瑞·库宾格不想就此放弃,他试图找到支持者。
当时,除了世卫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欧洲联盟委员会等国际援助机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并不断和世卫组织及其他机构强调,西非当地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急需采取措施。
盖瑞·库宾格找到MSF的ArmandSprecher博士,说服他一同推动疫苗临床试验。
2014年8月,病例有增无减,世卫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几天后,加拿大政府宣布愿意捐赠实验室的rVSV-ZEBOV疫苗。
其间,还出现了反对使用该疫苗的插曲:一些人说,向西非埃博拉患者提供从未给人使用过的药物是不道德的,同时,因为西非地区薄弱不堪的医疗状况,临床试验的安全无法保障。有人还举例1996年那场导致11名儿童死亡、大量儿童失聪的脑膜炎药物事件支持此观点。
疫情规模不断扩大,世卫组织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埃博拉病毒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恶劣影响,专家组最终得出结论:尝试使用实验性疫苗和疗法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但前提是要开展安全性评估临床试验并确定出适用的剂量。
联合小组的规模很强大,从世卫组织网站查询可知,rVSV-ZEBOV的试验由世卫组织资助,并得到以下方面的支持:威康信托基金会、英国国际发展部、挪威外交部、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通过挪威研究理事会提供支持)、加拿大政府(通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外交、贸易和发展部提供支持)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
之后,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表示愿意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埃博拉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
盖瑞·库宾格的团队也开始往返西非,帮助当地构建临床试验的基础设施。
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rVSV-ZEBOV疫苗的持有者NewLink公司此前从未进行过一项临床试验。
当世卫组织宣布要在非洲进行临床试验时,他们完全傻眼了。很明显,NewLink不具备相应的专业度和能力来承担这项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其他机构,需要寻找一家更有经验的制药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潜在的候选人并不多。
据报道,几个有相关疫苗开发经验的大型药企中,赛诺菲没有合作意向,诺华也在当年早些时候将疫苗部门出售给了葛兰素史克,而葛兰素史克正在加紧研发自己的埃博拉疫苗,强生的疫苗部门虽然也在研发埃博拉疫苗,但进展太慢。最终,专家组选定了默沙东公司(在北美称为默克),它有与VSV疫苗类似的疫苗生产经验和相应的专业度,也了解如何规模化量产和管理整个规模化量产的过程。
“我们知道如何规模化生产疫苗,了解生产这一疫苗所需要的技术,也有能力去完成。”默沙东首席患者官朱莉·葛伯丁说。
6 建立人群免疫屏障2014年9月3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通过航空从西非输入了首例埃博拉病例。
埃博拉走出非洲到了北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事件的紧迫性,之后谈判进展迅速。2014年11月24日,默沙东公司和NewLink达成协议,将向NewLink支付5000万美元,以研究、开发、制备和分销疫苗。
与此同时,美国NIH和加拿大卫生局研发的两种埃博拉候选疫苗都在西非开始了人体试验。

埃博拉疫苗的环卫接种。WHO丨图
当进行临床I、II期试验的研究人员着手进行数据分析时,另外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准备关键性的III期临床。I、II期试验是为了确定疫苗是否安全,III期临床试验段将大规模检验它在人体是否真的有效。

2015年3月7月,rVSV-ZEBOV疫苗在几内亚开始III期临床试验,但随着疫情的减退,病例数不断减少,对试验方案的设计提出了严峻考验。
研发团队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临床试验设计,即所谓的“环围接种”方法——同样的方法曾被用于消灭天花。
即当诊断出新的埃博拉病例时,研究小组对过去3周内可能与该病例有接触的所有人进行跟踪,包括同住在一起的人,被病人探访过或与病人、其衣服或内衣裤有密切接触的人,以及某些“接触者的接触者”,总共确定了117个组(或“环”),每个组平均由80人构成。
一开始,研究者立即或在3周后对各“环”进行随机疫苗接种,并且仅向18岁以上的成年人提供疫苗。在发布中期结果显示疫苗效力后,便立即为所有“环”的人群提供疫苗,同时试验还对6岁以上的儿童开放。
随着试验的进展,相关的数据表明疫苗开始起作用,曾出现顽固传播的社区不再产生病例。2014年到2016年在几内亚进行的一项随机分组疫苗接种研究中,3537名实验室确诊的埃博拉患者的接触者,以及接触者的接触者接受了“立即”或“21天延迟”的疫苗接种。
通过对2108名立即接种组和1429名延迟接种组的病例比较,研究人员确定疫苗对出现症状未超过10天的患者100%有效。在“立即”分组中,未观察到埃博拉感染发作,而在“21天延迟”分组中,仅观察到10例发病病例。
负责进行该试验的WHO埃博拉药物研发组带头人肯尼博士(Marie-PauleKieny)公开介绍:“这一结果证明了面对埃博拉病毒的威胁,该疫苗具有100%的抵抗能力。”
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在将来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因为有了这个疫苗,我们准备好了应对的手段。”根据他的实验室推算,如果有新的埃博拉疫情出现,通过适时的疫苗接种,未感染人群有近90%的免疫率。
WHO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也正式得出结论:疫苗起作用了,并建议医务人员尽快为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人接种疫苗。
除了在那些接种疫苗的人中表现出高效力之外,该试验还显示,通过环围疫苗接种方法(所谓的“人群免疫屏障”)还可间接保护环内的未接种人群免受埃博拉病毒感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完成了从首个人体剂量研究到三期药效研究的全阶段试验——正常情况下,这一时间长达6至8年。国际艾滋病疫苗倡导组织的CEO芬博格(Feinberg)感叹,从未有过如此迅速的成功试验。
2015年7月31日,相关试验结果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该杂志的编者按写道,这一试验的进行,不仅证明了研究团队高超的技能,更证明了社会能为被疫情毁坏的国家带来希望,“在此之前,几内亚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临床试验”。
2016年12月,埃博拉疫苗临床试验最终结果在《柳叶刀》上公布,显示这一疫苗抵御致命病毒的高度保护性。
2018年春,当埃博拉病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暴发时,世卫组织将默沙东捐赠的埃博拉疫苗以“同情用药”的方式在当地接种,自那时起,已有超过26万人接种了疫苗,其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南苏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6万多名卫生人员和一线工作者。
2019年底,该疫苗分别通过了欧盟和美国FDA的药品批准程序,最终上市。
“虽然这些令人信服的结果对于那些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丧生的人而言已经太迟,但当下一次埃博拉疫情袭击时,我们将不再毫无防御。”WHO埃博拉药物研发组带头人肯尼博士说。
2020年3月,当全球都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刚果(金)宣布了该国(也是当时全球)最后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玛西克(Masiko)出院。
然而一个月后,庆祝埃博拉疫情结束的活动还没展开,4月10日,贝尼市又确认了一例新的埃博拉病例,接着变成了6例,其中4人已死亡。6月1日,刚果(金)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暴发,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1次发生埃博拉疫情。
“疫苗是消灭疫情最好的手段,也是未来预防疫情的重要手段。”Marie-PauleKieny强调,对全世界来说,埃博拉疫情带来的启示是,需要更多关注目前主要影响穷人和贫穷国家的疾病,因为当大流行开始时,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置身事外。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2020年6月10日,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端端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