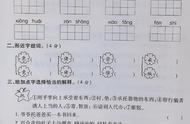作者:陈志扬(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姚鼐精湛的文章体性说以“天、地、人”同构的民族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为背景,容纳了儒家的伦理情怀、道家的自然崇拜、释家的超脱人生、辞章家的美学追求,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他对古代文学体性风格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姚鼐有关文章体性美学论或曰风格学的阐述主要见于其所撰的《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两文中,前者论文,后者论诗,大意相同。姚鼐的风格阴柔阳刚二分法简便易识,是抽象思维的思辨结果。以刚柔论风格可以溯源到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章有“清气”和“浊气”之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有“刚柔迭用,喜愠分情”之词;刘勰《文心雕龙·镕裁》有“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之说。至宋明时期,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将诗歌风格分为“沉著痛快”和“优游不迫”两大类;明人屠隆《文论》把文章风格分为寥廓清旷、风日熙明和飘风震雷、扬沙走石两大类。清代桐城前辈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质相类”之论;刘大櫆有“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之见。以上论述都是姚鼐风格学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前人的基础上,姚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立论,对阴柔阳刚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海愚诗钞序》云:“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姚鼐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强调文学创作是发乎自然合乎神明的精神创造。天地万物禀阴阳二气而生,人又为万物之灵,故其个性气质便有阴柔阳刚之不同,并会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文学之阳刚与阴柔风格便应运而生。《周易》将“阴阳”视为推动宇宙生命互动的两种基本因素,柔与刚分别是阴阳所具有的两种属性。姚鼐探讨文学本源以此宇宙观为哲学基础,从而使其阴柔阳刚二分法由以前的感性描述上升为一种哲学观照。
姚鼐风格说的价值,就在于对千姿百态的风格现象高度概括,并归纳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基本风格类型,从而使纷纭杂乱的风格现象在两大基本共性的统摄之下变得系统化,成为一种易于被认知把握的对象。姚鼐说:“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他并非没有认识到风格的无限可分性,只不过认为没有再作具体区分的必要。
在姚鼐看来,诗文最理想的审美境界应是刚柔相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尽管在理论上姚鼐要求阴阳兼胜,但在具体运用中他又常常打破这种平衡:“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他又以天地作比,认为“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故“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在阳刚美与阴柔美二者间,姚鼐更偏爱“阳刚之美”,他认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天下之雄才尤为难得。
以程朱理学为宗是桐城派的特色,姚鼐终身遵循宋学,其《程绵庄文集序》云:“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他甚至说“程、朱犹吾父、师也”,诅咒诋讪父师者会“为天之所恶”“率皆身灭嗣绝”(《再复简斋书》)。姚鼐秉承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推崇阳刚之美,同辈朱孝纯(子颍)、王文治(禹卿)和谢启昆(蕴山)的豪迈之作均得到他极力赞赏。年轻时候的姚鼐充满雄心壮志,极富报国热情,他说:“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自南来,意气颇纵横。”(《阜城作》)他以“偶向人间结豪士,击筑和歌燕市秋”的豪气自许(《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渴望报效国家,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姚鼐对阳刚之美的推崇,是一种对青少年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回忆。朋友朱子颍至老豪纵之气不衰,尤其是他企慕的对象;当姚鼐本人的豪纵之气不再时,这种敬羡就变得愈加真诚。此外,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对阳刚美的推崇也体现在该书对众多作家作品的评语上。
但是,姚鼐认为阳刚风格非勉力可为,而自然平淡阴柔的文风更易企及。他说:“夫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伟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后人勉学,觉有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与王铁夫书》)姚鼐本人所作诗文亦偏于阴柔一路,曾国藩就曾批评其文“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清史稿》谓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姚鼐为文净洁精微,此与其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多年的官场生活磨去了他富有棱角的个性,青年时代的豪气也日渐消歇,他曾说:“自从通籍十年后,意兴直与庸人侔。”(《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入四库馆不足两年,正值壮年的姚鼐便乞病辞官,据《姚惜抱轩先生年谱》载:“于是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治学路数与众不同,毅然辞职,自此选择了授徒讲学的道路。姚鼐自幼羸弱多病,壮年又连遭正妻、世父、继室相继而亡的打击,并黯然辞职,老庄、佛家思想由是滋生。宋学本身就融合了道、佛的血液,姚鼐接受道、佛思想自然亦无须较多曲折。姚鼐曾著《老子章义》《庄子章义》,对老庄之学有较多体悟。他在《庄子章义序》中说:“《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王文治又教之以佛学,《食旧堂集序》云:“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进。尝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旧堂内。其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原本排斥佛教的姚鼐由是渐信佛学:“鼐以衰罢之余,笃信释氏,佞佛媚道。”(《与朱石君》)在他看来,佛学与儒学看似相悖实则相通:“夫儒者所云为己之道,不待辩矣。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氏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学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为不必。”(《王禹卿七十寿序》)本土化的佛学与道学无甚差别,道、佛思想亦成了姚鼐的行为准则之一:姚鼐示佛书佛理于陈用光,葬亲而观形家之学数十家,退隐后知山乐水,视奇山为天地之至文而广游天下名胜。道、佛思想的滋生促使姚鼐性格趋于内敛,创作上由此形成了阴柔之风。
《清史稿》评价姚鼐的为人特点:“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总体说来,姚鼐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刚柔并济的处事风格。在诗文创作实践中,姚鼐不自觉地偏向了阴柔。姚鼐虽以恬淡闲适示人,但他绝非“佛系”老人,儒学才是他立身之根本,积极进取是一生的内在精神信念。姚鼐致仕后孜孜不倦地创建桐城派,较好地阐释了这股内在的坚韧与刚劲。更何况“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是一条自古而来悠远、深邃的文化潜规则,他尚阳刚而以阴柔为次的观念,显然是受了古代“天尊地卑”思想的影响。《易经·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图上首尾相合的阴阳鱼预示着阴阳相生的道理,但在八卦图中,纯阳卦在上、纯阴卦在下,男为阳而女为阴,尊男而卑女的意思十分明显。姚鼐所处的乾嘉盛世,刚健文风尚不迫切;道咸以降,危机四伏,经世之风盛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姚鼐这一倾向对其弟子们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为清末古文注入了雄奇、遒劲之风。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3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