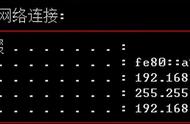优美散文|你听,夏日那些虫鸟的鸣唱
作者 崔洪国
草丛氤氲了夏日的雨露和清凉,它们就在无边的草丛中高声鸣唱着,与那些鸟儿的欢歌交响在一起,或如行云流水,或如银珠落盘,或如清风明月,或如山青谷翠,带给你无穷无尽,难以言尽的视觉听觉体验。
——题记
一
每年的夏日,实在是无数虫儿和鸟儿的天堂,它们欢快的鸣唱是天地间最美的交响。你也许听不懂它们鸣唱的是什么,但它们就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田野,在山岗,在你的窗前,在楼前的银杏树和绿草地上放开了喉咙鸣唱。时间久了,你夏日里的浮躁和心烦意乱很快就被那万千种声音合奏成了一种童音般的快乐和绿荫里的清凉。
岳父和妻子对这些虫鸟的鸣唱都很有研究。不久前的一天,楼前的绿草地上有了一种虫的鸣唱,妻子一听就说是有麦哨了。我问她我们熟悉的几种虫儿的鸣唱有啥不一样,妻子还给我普及了虫鸣的知识。她告诉我,春夏之交,田间最早鸣唱的是麦哨,那是端午前后最先能够听到的。日头高了,天热了,哨钱,也就是蝉就上场了,大约在芒种前后,麦收时节,蝉鸣唱的最是尖锐和清越,这个时候,村前村后的树上到处都是蝉蜕和振翅鸣唱的蝉。待到秋凉犹热,夏日的酷暑还没有散尽,便听到“都了”的鸣唱了。

其实,每年的春天最先报到的是那些鸟儿。在老家经常见到的麻雀、老鸹、山大头、喜鹊,一年四季它们是都不会缺席的。那些麻雀,老鸹和山大头大多都把温暖的巢筑在村前村后的杨树上,随便走到一个地方抬头望,几乎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大大的鸟巢,那些被鸟儿们捡了来搭巢的树枝看似没有规则,七出八进杂乱无章,其实也是一根插着一根,一根摞着一根,构筑了一个圆圆的完美造型,仔细看不亚于一件精致完美的艺术品。那些鸟巢建造的过程你是看不到的,你所能见的就是早晨或者黄昏,一只鸟儿,两只鸟儿衔着树枝飞回了,一根,两根,在喷薄的晨曦里,在夕阳的暮色里,用不了多久,一个圆形的鸟巢就在高高的树上落成了。任凭你再大的风雨,那群鸟儿在巢里也能安然无恙,每天早出晚归,早上你还在酣梦中呢,她们就在那巢中,在树梢对唱着了。
二
人有人言,鸟有鸟语,虫有虫音。每天的早晨,那些鸟儿万千的鸣唱其实就是鸟儿们交流、求偶、择食,分享它们之间快乐的语言和秘籍。不管在城市的街角,还是在乡村的田园,我们都能听到那些让我们心情快乐舒畅的鸟儿的鸣唱。日暮黄昏,有鸟儿立在枝头,一声一声呼唤着,那是让在外飞翔的鸟儿们归巢回家,它们听得懂彼此的关心和问候,很快,那一家的鸟儿就聚在了自己家的巢穴里,有调皮的小鸟还从巢穴边上向着四面张望着,叽叽喳喳闹嚷着,夜色深沉,当人们进入了梦想,它们也渐次静息了。
每天的早上,天还早,还是繁星满天,那条群星璀璨的银河在宇宙的远处闪耀着弯弯曲曲的光芒,那些鸟儿就醒了,沉不住气了,就在树梢的巢穴里蠢蠢欲动着。那时间也就是四点,五点钟的样子,它们就开始婉转,悠扬,清脆,悦耳地鸣唱了。霞光万道,当金色的朝霞越过了远处的山峦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开来,那些鸣唱的鸟儿叫得更加欢畅了。那时它们就有了明确的分工,有的要一跃飞出巢穴,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它们长大了,要在飞的同时学会向着更远的远方飞翔。有的很优雅的在树梢上下蹦跳着,踱着步,偶尔也和同类分享着梦里醒转来的那份欢欣和喜悦。还有的飞上了小区院子里高楼的顶端,和远处青山翠谷中的鸟儿对唱着情歌,在歌声中传达和寻觅着美丽的爱情。很多会情歌对唱的鸟儿都是谈情说爱的高手。

只要你能静下心来,你就仔细听吧,那些鸟儿的鸣唱有时会汇成一曲抑扬顿挫的交响,每一种音调都在高低起伏间不停地转换和律动着。有时又是一支单曲,就如同在吟咏和诉说,反复变换着用几种不同的发音鸣唱着,那其实也是一种宣示和表白。因为很快就有另外一种清幽的声音在窗前的树梢和远处的树林,在村子的林场应答和唱和着。很快,你就能看到它们集齐了,如同一簇射出的箭一般,向着同一片密林飞去,那里成了它们彼此表达爱慕的天堂。
有时,那些声音你虽然听着像一种声音,难辨其详,但其实所有的声音都是鸟儿们不同的叙事和表达。甚至在晴天和山雨欲来的时候,那种表达也是不一样的。碧空如洗的日子,它们的鸣唱不急不躁,让人赏心悦目;黑云翻滚,风卷雨集,它们就一声一声急促地鸣叫着,是为久旱的甘霖欢歌,抑或是呼唤着在外的鸟儿们赶紧归巢,那遮风挡雨的鸟巢才是风雨中安阑的家。在老家的农村,滴水鸟对风雨的感知最为敏感,它们的叫声也很独特,每当雨天来临,它们就在自家巢穴的树梢上“滴水,滴水”的鸣叫着;倘若几天连阴的雨天,一直不见雨住风停,它们就在巢穴的边上换了一种声音“晴天,晴天”的叫着,第二天,天也就真得晴空万里了。
三
春夏之交的虫鸣是伴着鸟儿的欢唱在不知不觉中登场的。最先出来赶场的是在农村中经常听到的“麦哨”,在我家前边小区的草丛里也有。俗话说“清明到,麦哨叫”,听老人讲,“麦哨”其实也是蝉的一种,是早蝉,每年的清明前后,天还是非常温润凉爽的时候,它们就破土而出了。“麦哨”的叫声很尖很直,那种声音听上去不刺耳,农村的话说就是很“受听”。因为个头很小,它们就藏在田间地头的麦地里,草丛里,不走近了,你很难发现它们,只是听到它们连续不断的鸣唱。我小的那会,哥哥姐姐还经常用一段麦秸削孔,放在口中吹,能发出和田里的“麦哨”一样清脆的响声,教几下,我也也就会了,用麦秸杆做的“麦哨”成了童年我最喜欢的玩具。
气温上来,天热了,就能听到夏日的蝉鸣了。时令大约在芒种前后,正是割麦种豆的夏忙时节,在那些“麦哨”尖削的叫声中,你能听到混合了一种相近的声音,但是断断续续,粗粝嘈杂,缺少虫鸣所具有的那种音乐质感,而且每年都很熟悉,那就是蝉鸣了。蝉在我们那地方叫“哨钱”,夏日每天的傍晚,我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村前屋后的树林和田园里等待破土而出的“爬叉”(蝉的幼虫),回家腌制好了,炸出来的金蝉是最下饭的佳肴,也是如今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我在散文《清风半夜鸣蝉》中详细叙说过儿时扣“扣爬叉”的情景,如今农村的蝉也少了,那提了灯笼,拿了铲子“扣爬叉”的情景怕是只能到流金岁月中寻觅了。那些漏网的“爬叉”最终就蜕化成了蝉,留了了蜕皮在树上,早上起来,树梢就有震颤着羽翼高声鸣唱的蝉了。夏日的蝉也有一个很不为人知的特点,就是在夏日最热的时候,那些蝉都在树的最高处不住的鸣唱着,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在由夏向秋的季候转换里,蝉便从树的高处逐渐向下转移,到最后也是蜕化成了一个蝉壳,就此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至于夏秋之交的“都了”就是寒蝉了。同样是蝉,早春和立秋后就不一样,这学问还真是蛮多的。“鸣于秋者曰寒蝉。”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鸟语》中也说过:“齐俗呼蝉曰稍迁,其绿色者曰都了。”也就是柳永在《雨霖铃.寒蝉凄切》中说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中的寒蝉,那个时节已经是秋风渐近,秋意渐凉,草木万物变易,季节开始渐次更替了。“都了”的叫声不似夏蝉和春日的麦哨,是一声一声“都了,都了”的叫,听着声音就有些底气不是特别足,已经约略听出入秋后的一些收敛和肃*了。不过,“都了”在入秋后生活的时间很长,有不少的“都了”一直到了霜降还能听到它们在田野和草丛一声一声地鸣叫着。
四
夏日是万物勃发和荣盛的季节,也是万千的虫儿和鸟儿交响的王国。有很多的虫鸟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但能感觉到这些年虫儿,鸟儿在绿树青山中是越来越多了。我住的小区今年一入春以来的虫儿鸟儿就多得不计其数。开始是那些鸟儿在楼上的空调挂机、树梢、山林筑巢安家,不久就每天早上在小区的楼前楼后,树林山谷来来回回飞翔着,欢歌着,即便被它们早早吵醒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碧空清澄,听着它们的喧哗,那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享受。再后来,就有了无数的虫儿参加了进来,每天晚上星光闪烁,草丛氤氲了夏日的雨露和清凉,它们就在无边的草丛中高声鸣唱着,与那些鸟儿的欢歌交响在一起,或如行云流水,或如银珠落盘,或如清风明月,或如山青谷翠,带给你无穷无尽,难以言尽的视觉听觉体验。

今日早上,岳父岳母早早就起来,到了楼前的广场上,牵着手坐在木制的长廊上,听着那些优美的虫吟鸟鸣,细水流长地说道着他们这么多年的风雨和不离不弃的爱的往事。他们年龄大了,我们说的很多话他们听不见了,但是他们彼此的对话和表白他们自己能够听得懂,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场景。我过去给他们拍了一张执子之手的最美照片,岳父岳母微笑着,很腼腆的样子。
岳父用手指着银杏树稍正一对欢唱的鸟儿,对我说:“这是一对白头翁,每天很早就在这棵上不住声的叫。还有一对黑色的喜鹊,就是在我们五楼的空调那里安家的那一对,今天大概到别的地方过周末了,没有过来。”“喜鹊也过周末,那些虫儿和鸟儿大概也在过周末呢!”我说得声音很高,岳父岳母都听到了,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吱—吱”“啾—啾”“嘟—嘟”“啾啾,啾啾”,你听,夏日,那些虫儿,鸟儿又在起劲地鸣唱了。
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部分图片来自笔者行走中的发现和身边的亲情互动,一并致谢!

崔洪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烟台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寻找灵魂的牧场》《与海阳最美的邂逅—崔洪国散文精品集》。在报刊、媒体、平台发表散文、书评300余篇,作品多次在省市征文大赛中获奖。散文《济南的桥》入选齐鲁晚报“青未了”优秀征文荐读篇目,《四哥走了》被齐鲁壹点评为月度“爆款文章”,《在农村吃大席》《崔健,让我想起歌声里的过往》收录于壹点号3月,4月电子月刊《清泉录》“2022清泉计划获奖长文”,获评优秀散文。
壹点号 风过林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