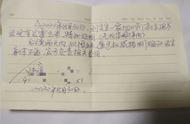我出生的地方,是滹沱河icon故道。滹沱河是标准的汉语称呼,我们老家的人都称作蒲涛河(音)。由于滹沱河改道,所以我们村的土地具有了冲积平原icon的一些特点,也就是沙质土壤。我们村向南三里地,就是黏土,向北十里地,也是黏土,只有中间这十来里宽的地方是沙质土壤。沙质土壤的特点就是表面甚至一米厚的土层基本都是沙土,下雨后雨水很快全部渗漏,所以在我们村走路骑车是不怕下雨的,别的地方下雨后道路泥泞的情形,我们村基本不会出现。这也决定了一些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于那些粘质土壤的地方。比如,修改房屋需要的土坯和砖瓦,需要用黏土,粘质土壤的地方就地挖掘就可以,我们却需要把一米后的沙土挖开后,才能得到黏土,黏土层的厚度也就一两尺之间,小时候玩弹弓搓泥球用的胶泥,那更得在粘土下面才会有十公分左右薄薄的一层。这样的土质,能让我们在雨中或雨后正常的玩耍和出行,不用担心自行车挡泥板被泥团填塞车轮转不动的尴尬,不必害怕雨后走路鞋被泥粘住拔不出脚来把鞋丢掉。
这样的土质,也决定了地上的植被与其他平原地方不同。当地有句俗语形容我们村:村南米粮川,村北花果山。也就是说,村庄南面,大概有四百米左右的厚度是梨树、枣树、杏树等,果树之外,才有大片的土地种植庄稼蔬菜;村庄北面,从住宅开始,一直到邻村的村界,几乎全是果树。据老人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骑兵追八路,八路就专往我们村这一带跑,只要跑到树地里,骑兵就没法了,果树枝会划伤士兵和战马的。老人们说,刚开始进来的日本兵是很傻的,他打开你家的门,你藏在门的后面不出声就可以,日本兵都不知道看一下,后来有汉奸告密才没有了这个脱险办法。
我们那里最适合生长的农作物就是红薯和花生,但为了果腹也种植小麦、玉米、黄绿豆、谷子和少量的高粱,不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因为人均地只有七分,沙土土质产量低,除了日常生活必需的油料类和蔬菜,其余的都种小麦玉米等口粮,即使这样还不能自给自足,我们村不仅没有交公粮的任务,而且自我记事开始一直到1978年分田到户,基本每年都吃统销粮和返销粮,也就是国家从粮库调拨给我们村一部分口粮,蚕豆,豌豆这些都是从这个渠道才让我品尝到的。我小的时候还没人种植土豆,也没有见过更不知道有土豆这种作物。由于不是黏土,所以生长的红薯和花生很干净,很顺溜,含水量低,好吃。另一个适合种植的就是水果。我没有考证过我们村种植果树有多少年的历史,反正我小的时候梨树主干直径达到一米左右的很多,分枝也和我现在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梨树主干粗细差不多,据我父亲讲,他小的时候梨树就差不多这么粗,所以三五百年的历史应该是有的。说具体点,一棵鸭梨树,用汽油机喷洒农药,喷完需要一个多小时,枝叶覆盖面积大于20平方米,秋天摘梨的时候,三个人需要一天是个小时左右才能摘完,一棵树就能产梨三千斤左右。
当时出口的天津鸭梨,我们村就是主产区,砂质土壤长出来的水果品质好,口感好,当时没有套袋的措施,每个鸭梨icon都黄澄澄的,非常细腻可口,含糖量高,用手就可以把一个鸭梨掰成两半,可见多么酥脆。当时出口的鸭梨是按大小分等级的,一箱21-22斤,分为28、32、40等规格,也就是一箱里面有28个、32个、40个鸭梨,要求重量达到21斤。鸭梨不同于雪花梨,皮很薄,很娇贵,要求摘梨的时候必须要剪指甲,防止指甲划伤梨的表皮,那样装箱后那个地方就会出现一道黑痕,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腐烂。摘梨的时候是用手掌拖住梨果icon,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头向斜上方一推,梨果就和树枝分离了,绝对不能和摘苹果一样攥住梨果揪下来,那样会挨骂的,因为梨把受力后会从那里开始腐烂。梨摘下来装箱封箱后用大马车或拖拉机送到县城,然后转移到火车送到天津港口。但是在转移到火车之前,县里果品站要抽查质量,一个是重量是不是足,一个是不是有腐烂的,如果抽查中发现了问题,整个这一批是要重新返工的,所以在村里面从摘梨到装箱,都严格要求。
农作物不同于工厂量化产品,不同批次质量基本一样。出口创汇的梨,连三分之一都达不到,大量不能出口的梨,就要摘下来由生产队储存、销售。当时没有冷库这样的储存设施,摘下来的梨就是放在梨戳里。梨戳是老百姓创造的一种储藏工具,就是在梨树地里用箔在地上围一个筒,直径大概两米多,高一米七左右,圈里面底下放几根木方,木方上面铺上绵纸一类柔软的东西,然后就把梨果一层一层的小心码上去,一直码到接近上面的边缘,最上面覆盖一些防雨的东西就行了。用秫秸(高粱的杆)和麻绳,结成类似于凉席一样的东西,我们那一带叫“箔”,用芦苇结成的叫苇箔,用秫秸结成的叫高粱箔,用来储存水果和粮食,它的好处是通风,水果粮食不会发热腐烂。所以深秋或初冬,我们村会有很香的梨果味道。这些东西就放在村外,不必看管,当时是没有人敢偷窃的。一旦被抓住,是要游街示众的,然后就要免费打扫村里的街道,这个这个震慑力是非常大的。
我小的时候农村是没有暑假的,放寒假和农忙假,农忙假是两个,一个是五月底六月初麦收的季节帮助收小麦,一个是秋天九十月份帮助摘水果和秋收。收小麦的时候,正好是杏子熟的时候,两者相冲突,所以我小的时候不能割麦子,就去地里看杏树。所谓看杏树,任务有两个,一个是用锄把杏树底下的土弄喧腾,也就是弄得很软,这样长熟的杏掉落下来不会摔坏,然后由生产队的老人捡回去制作杏干icon或分给农户吃。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是没有体验过熟透的杏子的滋味的,杏肉有弹性,可以剥下来一层很薄的皮,只有甜的滋味,没有酸的口感,类似于现在我们买了葡萄不吃,常温下放个四五天后葡萄粒的感觉。另一个就是怕别的小孩不懂事“偷”杏吃,小孩子嘛,不懂事,大人都去田地里干活了,孩子们到树地里找成熟的水果吃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看杏的孩子,没人的时候也是会偷吃的,而且是挑着拣着顺眼的吃。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根横着的树枝的尽头有几个又大又红的杏,我个子小,在地上够不到,只能爬到树上,再爬到那根树枝上去摘,够不到,继续顺着树枝向前端爬,手也接触到红杏icon了,那根树枝也在我屁股后面接近树*地方断了,我抱着树枝从两米多高的地方平着趴到了地上,多亏那会儿瘦,干活的时候没有偷懒,树底下很软和,所以只是吓了一跳,没有把我摔坏,嘻嘻。
农村的孩子午饭后是没有午休的,大人上午干活,下午还要干活,中午自然要休息一会儿,这个时段孩子是没人管的,自由自在,想干啥就干啥。杏子成熟的季节,我中午一般都是到树地里到处跑,目的是踅摸哪棵树树上的杏好吃又个大,好吃容易理解,为什么还要个大呢?目的是要杏核,因为只有个大的杏子,里面才有大个的杏核。这既和杏的品种有关系,也和同一品种的不同个体相关。我们村最大的杏叫大红杏,类似于邢台巨鹿的串枝红icon,但是比那个还要大,还要甜,单个杏就有一两多重,尤其是熟透了以后,用嘴一咬顺嘴流蜜。上午和下午地里都有人干活,落下来的杏基本都被干活的人吃了,只有中午大人都在睡觉,天气又热,落下来的多数的又大又熟的杏子。挑选大的杏核,是为了和村里其他孩子赌杏核。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供销社卖的食盐是三分钱一斤,收购的鸡蛋是六角钱一斤,杏仁也同样是六角钱一斤。孩子们不能到地里帮大人干活,就在家砸杏核卖杏仁。砸杏核也是个技术活,有锤子的用锤子,没有锤子的用一根修自行车换下来的旧车轴,一手拿杏核,侧立着放在一块砖上,另一只手用铁锤适当用力敲打杏核上侧,杏核会爆开,取出杏仁,接着砸下一个。供销社收购杏仁品质要求很严,破碎的肯定不要,就是杏仁尖的那头掉下一小块,露出白色的也不要,所以砸杏核的时候要分外小心。刚开始砸砖面是平的,杏核不好固定,砸十来个以后,砖上就会被杏核侧面硌出一道凹槽,类似于中药铺的药碾子icon。把杏核放到那个凹槽里,就容易多了,既不会被砸的崩跑了,也不会砸到手了。
任何年龄段的男性,都是有赌博心理的。十来岁左右的小男孩不会赌别的,就赌杏核。方法是每个人衣服兜里都带一部分杏核,一般也就是二三十个,不管几个人参与赌,大家每人出一个杏核,放进事先在地上挖出的锥形坑里,然后锤子剪子布决定顺序,按序由每个人用自己的法宝杏核,也就是最大的那个杏核向坑里砸,这样会让一部分杏核从坑里蹦出来,只要出来的就归自己所有,如果自己的法宝杏核陷在坑里出不来,就要用两个杏核把自己的法宝杏核换出来,有点类似于台球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个大的杏核自然沾光,所以大家就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大杏核。还有的把杏核的偏平的一侧在石头上磨出一个小洞,用小勾子把里面的杏仁掏出来,然后往里面灌入锡水(那会儿农村烧热水、喝酒都是用锡壶,街上经常有锡匠icon加工和修理锡壶,所以锡的下脚料很容易得到。把锡放在熬中药的砂锅把里,放在煤火上很容易就熔化了),这样会比一般的杏核重很多,惯性会更大。其实从坑里往外砸杏核,也是有技术的,这就是法宝杏核的入坑角度,技术好的经常能一锅兜。赌杏核既有输赢的刺激,更是孩提时代男孩子们一个很大的乐趣。
与劳动付出相伴随的,就是各种农作物的成熟,这个时候大人和孩子们的口福就来临了。春天到夏季一般没什么吃的,但一进入秋季,各种烧烤就开始了。
最吸引人的当然是烤花生。从生产队的花生地里,挑选那些叶子发黄甚至脱落一部分、花生秧根部隆起的(这样的才有饱实的花生)花生拔起来,抖落掉泥土,把花生揪下来。然后挑拣一些枯树枝或庄稼秸秆,找一个背风处或者挖一个浅浅的坑,找一些柔细的干草作为引火,用火柴把一些干草点着,再引燃庄稼秸秆或干枯的细树枝,然后把花生秧架在燃烧的秸秆或干枯树枝上面,然后再把揪下来的带皮花生放上面烧烤。等十几分钟,一顿可口的烧烤花生就完成了。由于花生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没有经过晾晒,且带皮烧烤,所以烧烤好的花生豆不同于油炸、水煮的滋味,口感是很丰富的:成熟度老、离火近、烧烤时间长的有一些焦香,成熟度适中的基本是面的,比较稚嫩的则里面还带着一股水,吃起来软软的,带点甜头,但是要小心别被花生壳里面的水烫伤。还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由于是火焰直接烧烤,难免一部分花生皮icon会烤焦甚至碳化,所以吃的时候要注意别弄一脸黑。虽然孩子们都怕弄一脸黑带幌子(大人一看就知道偷偷烤花生或玉米或红薯吃了,是要挨揍的),但人多花生少,而且家里基本上都是玉米饼子、豆瓣酱、咸菜条和照见人的稀粥果腹,所以一旦花生熟了还是争先恐后的抢着吃,这时候如果当君子,就只有看吃的份了,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的道理。当然等花生大批成熟、生产队统一刨收的时候,花生叶子基本落完了,花生秧也基本半干了,这时候烧烤就可以直接连花生秧带花生直接放柴火上烧烤,不必再事先揪下来了,这个时候的烧烤也基本是大人完成的,孩子们赶上了也能分一杯羹。
另一个吸引人的烧烤项目就是玉米和红薯,和烧烤花生的方法不同,因为直接烧烤会把玉米粒烤黑,而红薯不像花生那么容易成熟,就要改用焖烤的办法了。红薯简单,看看红薯秧根部的土地隆起、且有手指头宽的裂缝的,下面就有大的红薯。适合烧烤的要挑长形的,圆蛋子不容易烤熟。掰玉米有些讲究,如何能保证掰下来的玉米棒子不老不嫩?要看玉米棒最上端的玉米须,干透了的就是太老了,烤熟了玉米粒也咬不动;玉米须还是黄绿色、有一定水分,就是太嫩了,烤熟了基本是一股水。一层皮,不好吃也吃不饱;要挑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右手按一下玉米棒子不太硬(这样的老了)、不太软(这样的嫩)、包皮基本发黄还带一点绿色的就是正好适合烧烤的。
在准备玉米或红薯的同时,就要做焖窑了。找一个坎,用铲子从断面出横向掏一个洞,洞要挖成穹隆形,也就是底下宽、上头小,顶部挖出一个略小于洞的直降的口子(只有上面的洞口小于洞的直径,才能延续后面的工序—搭穹隆icon)这样有利于通风和有较好的抽风效果,符合物理原理,哈哈,书面语言叫烟囱效应。然后用挖出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的两头尖、中间粗、长十公分左右的土疙瘩,把这些土疙瘩绕着上洞口一个挨一个的砌起来,每上面的一层要小于下面的一层,最后形成一个松塔状的圆锥状。然后就找一些细软的干草、小树枝、秸秆等,点着火,从洞的侧面口子塞到洞里,持续的烧十几分钟或二十分钟,会看到捏的那些土疙瘩由湿变干,由土黄色变成灰白色,手靠近会有炙热感,这时候就到火候了(玉米可以剥去一部分包皮,留一两层用来保护玉米粒不会发黑发苦,红薯直接用就可以),把准备好的玉米或红薯放入洞中(未燃烧完的柴火和灰烬不必清除),由一个年龄大的孩子用脚把那个烧的很烫的土疙瘩做成的松塔踹到洞里,然后在用别的土盖在上面,然后,然后就去干活或割草去吧(踹那个土疙瘩松塔也要注意,假如把脚伸到了洞中会被烫伤,所以要由年龄大、有经验的大孩子完成)。四十分钟左右,干活也累了,草也割满了筐子,这时候回到烧烤窑,把土扒开,一顿喷香入鼻的大餐就等着吃了。由于不是明火烧烤,而是用烧烫的土把红薯或玉米焖熟,所以基本不会出现焦黑、焦苦的事情。这样焖捂而熟的玉米和红薯,不同于蒸煮的玉米红薯,也和爆玉米花、城市里的烤红薯不一样,别有一番滋味在口头。
如果是秋天,还可以加入红枣,当然得在玉米红薯之上的热土上加,否则接成乌枣了,烤熟的枣香而甜,消食暖胃,除了果腹,还有一点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