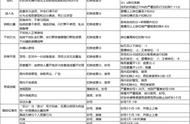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发达国家日本至今仍然面临鲁迅近百年前发出的永恒追问。过着小康的“中流”生活的人,会不会重新坠入生活困顿的社会“底层”?为避免下坠所做的竞争,有效吗?如何避免在竞争中落败?关键是,能不能避免坠入“为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境地?日本著名学者山田昌弘对日本社会的这一现象以数据为支撑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分析,写出了《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一书,可供现代社会的人们参考、反思。

《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 [日]山田昌弘著 胡澎 杨雪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曾做过一个“国民生活意识调查”,认为自己生活水平达到“中流”的人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历经济危机、泡沫经济破裂,当时出生的“70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逐渐开始分化,出现了“啃老族”“寄生族”“单身族”等现象;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这批日本“70后”全部步入中年,被称为“40世代”(四十多岁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当初被诟病的“单身寄生族”一代,他们如今的生活如何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世界迎来了全球化浪潮,随后许多新社会现象在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加……战后日本积累的繁荣和快速发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历了坠落,如今陷入停滞,增长缓慢,日本学者山田昌弘在2004年出版了《希望格差社会——“失败一族”的绝望感将撕裂日本》一书,当时就提出了对日本劳动状况发生变化的担忧。
“格差”这个日文名词意思是指差异、不平等、贫富差距,“格差社会”的意思就是社会阶层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近二十年来,大量日本学者就提出过许多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观察,如曾经轰动一时的《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该书曾引进中国,在讨论中争议很大。在日语中,“中流”和“下流”指的是中层和下层,意思是“中游”“下游”;日本社会曾经流行过“一亿总中流”的概念,意思是日本社会三亿多人口中,有超过一亿人是“中流”,大部分的“中流”人群却失去了安全感,努力维持着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的中层生活水平,从而跌入“下流”。日本社会学家佐藤俊树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社会——再见总中流》一书,提出在竞争中落败而不得不与中流说再见的人不断增多,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1987年3月,日本泡沫顶峰,安田火灾保险时任董事长后藤康男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以近4千万美元价格标得梵高的《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
为什么不结婚了?
为什么日本社会面临如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妨把问题聚焦,看看年轻人担心的是什么,如果再细化一些,可以从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这件事入手。日本“二战”之后持续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其实也是一个标准化模式复制成功的结果: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家庭是这样的“标准家庭”——男性毕业后找到一份“正式员工”的工作,多数在大企业中工作一辈子,收入稳定,年轻时足够娶妻生子,老年后也有一份优渥的退休金;而女性则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嫁给一个“与自己父亲赚钱能力差不多的”,有稳定工作体面收入的男性,生儿育女。在四十年前,这样的“标准家庭”是日本最主流的生活模板,而四十年后,这一代人生育的子女所过的生活,却不再“标准”。
1989年,日本的总和出生率为1.57(即每个女性一生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创出生率新低,因此出现了“1.57冲击”一词,媒体开始讨论“少子化社会的到来”,1991年被称为“少子化元年”,当时的讨论大部分认为,少子是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而结婚年龄推迟是因为“想要工作的女性不想结婚”。《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中,作者山田昌弘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晚结婚、少生育的现象既不应该归咎于女性,也不应该归咎于年轻人,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与上一代年轻人相比,这一代年轻人从小的生活环境多在大中型城市,衣食无忧,他们的父母是上一代通过自身努力留在(如首都圈、大阪圈、中京圈等)大城市的一代白领,是前文所述的“一亿总中流”,他们多数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企业工作、凭借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度,收入不断增加,为儿女创造了稳定富裕的成长环境。这一代年轻人成年后发现,自己工作的收入不一定有父母的多,如果结婚成为全职主妇,那么生活条件将急剧下降。山田昌弘采访调查了许多至今未婚的“40世代”(出生于1970到1979年之间),其中有六成男性和八成女性与父母住在一起,享受着宽裕的生活。作者提到在引发日本社会争论的《隐形贫困——即使是中流以上阶层也存在生计*风险》一书的观点,上一代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衣食住行“非高档品不要”的消费习惯,而现在的年轻人消费上追求的是物美价廉、性价比优先。
作者提出,如今大量年轻人就职于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为了效益违反劳动制度,让员工加班加点,迫使员工不断离职。从书中所调查的参与相亲活动的女性中看,女性最担心的确实是结婚后的生活水平下降,不能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准,这样女性大多会选择继续工作、不当全职主妇、不生育两到三个孩子而是只生一个或干脆不生育。她们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就降低寻找配偶的标准,如果不能实现“买房买车、把孩子送进大学深造、全家去度假”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那么他们情愿不婚不育,以不降低自己的生活,继续享受现有的生活——父母提供基本的吃住,自己的薪资当作零花钱——这似乎确实是现有局面中的最优选择。

日剧《我选择了不结婚》海报
害怕掉队的年轻人
日本社会有个比较有特点的情况,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要马上进入大企业做员工或进入政府机构做公务员,一旦错过毕业“校招”的那一年,就很难再有机会通过“社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此前,大部分日本年轻人都过着一辈子毕业即工作、一生只做一份工作的生活,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令他们面临着更多选择,很多人成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派遣制员工。这种“应届毕业生整体录用”的现象,让年轻人一旦脱离了正式员工的队伍,再想回去是非常困难的,书中写道:“对应届毕业生最重要的是,能否成为正式员工,能否一直不被解雇,从最开始没有跟上队伍的,是很难再从头开始的,这件事无关性别,但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作者还认为,婚姻也是如此,尤其是女性,一旦结婚后离婚了,就很难找到比前夫经济条件更好的再婚对象,这也是当代年轻女性对结婚过于慎重的原因之一。
作者提出了“共时多样性”和“历时多样性”两个概念,分别是说从时间的角度或某一时间段的剖面上,年轻人需要面临的各种各样家庭模式和就业模式的抉择。这代年轻人的父母一代,大多数经历的是一旦结婚就很少离婚、一旦工作就很少辞职的生活,但到了2010年,日本的就业调查中正式员工只有六成,30岁以上的人群失业率超过了10%。
研究家庭模式的共时多样性把目光聚焦在了未婚群体和离婚群体的增多上,日本一次调查中显示在35到39岁的人群中,1995年时他们中的近百分之八十有配偶,而到2010年,拥有配偶的概率大为降低,仅有65.3%。从婚姻形式上来说,日本社会经历了从“只要遇到理想对象就结婚”到“即便谈恋爱也不结婚”,再到现在的“即便结婚也分开居住”的爱情婚姻观的剧烈变化。不管是工作还是婚姻,看上去人们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多样了,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多样性导致了差距的扩大。作者看来,这种“是我自己不想结婚”“是我自己想当自由职业者”的回答只是台前的故事,而幕后是“想结婚却结不了”“想生却没条件生”“想成为正式职员却无法转正”“想工作一辈子却在35岁碰到职业天花板而中年失业”……年轻人的焦虑其实归根结底是当代日本人对于风险的厌恶,在可能的麻烦前面,多数人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微妙的心态是很值得琢磨的。
但是这背后还有更需要深挖的经济原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化背景下,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劳动开始两极分化,附加值高的“创造性职业”和只要求熟练度的“简单劳动”的两极分化开始,再往深究,就是“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一些新兴产业(如互联网产业或金融产业)中,一部分年轻人收入非常高,而同时在一些工厂、商店的临时员工收入却非常微薄,两相比较,这两类人群薪资差距动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前者为了维持“中流”的生活水平、害怕掉队而过度竞争,就是“为避免下坠而竞争”。

日本的上班人群
老年人社会的未来
如果这样的社会现实继续发展,作者担忧的是这一代年老之后会面对的事情:对于那些单身族或丁克族来说,年老后患病住院需要看护,他们能拥有足够维持生活的养老金、存款和资产吗?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罕见了。
在日本私立养老院,如今每月接受看护的费用约是25万日元(约合14000人民币),如果是两个人,就需要50万日元。“养老金和存款能够支付这些费用的人有多少呢?我猜恐怕不到两成。”作者说。如果是去公立养老机构的话,目前日本公立养老机构数量不足,且质量低下,作者看来,这些年的“健身热”恐怕也是因为“一旦失去工作就只能从中流掉下去”的忧惧。
怎么办呢?作者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改变方法,希望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探索,其中之一便是“拓宽家庭形态”。作者看来,要想从制度上保障“老年人不再孤立”,可以进行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互助生活”,比如两位年轻人在城市工作,租住在老人的房子中,老人以提供居住为条件与年轻人合住,“我认为,社会应该建立能够支持这种尝试新生活方式的制度结构,例如单身生活的老年人把自己家作为‘老年集体之家’招募房客,自己住其中一间,这样老年生活便不再孤独了。”作者写道。这种“共享式养老”显然需要更加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来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
此外作者还提出一个解题思路,那就是具有共同爱好的“兴趣小组”人士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现实化”,比如一些单身的年轻人常提议“若是咱们以后一直单身的话,老了之后大家搬到一起住吧”,如果这些口头约定在将来付诸实施,理想能不能变成现实呢?显然这里作者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日本以往的仅凭血缘上的亲子关系要求子女负担赡养义务,显然对于过度老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已经不够用了,不能只号召大家献爱心,还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比如“最低养老保障金”或“拓宽家庭成员的界限”。
“要让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互相照顾,那么构建使他们能够安心生活的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考虑到,比如照护问题和遗产继承权、养子等问题,“由于当前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被延后了,所以没有家庭成员的老年人无法安心地和别人一起生活。”2016年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后妻业之女》就因反映了以遗产继承为目标*害再婚对象、欺骗老年人收入等,可见一些看似未来的问题已经发生。《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一书在结尾处提出建议,只有建立更完善的、符合当下社会情况的新制度。作者希望,“40世代”的理想未来,是一个即便经济不宽裕也能够“和喜欢的人一直愉悦交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