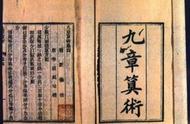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焄
《酉阳杂俎》的“吴洞”,讲述吴洞之女叶限遭受继母虐待,有一次乘其不备,参加洞节集会,被发现后仓促逃归,不慎遗落一履,被陀汗国国王辗转获得,国王经过百般寻访,最终找到叶限,“以叶限为上妇”。尽管灰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疑惑恐怕仍将悬而不决而未能遽下断语,然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妙的关联。
多来源的灰姑娘故事
在欧洲流传已久的灰姑娘故事存在不少版本,细节各异,近代以来更出现多个不同的汉译版本。此外,在漫长而曲折的流传演化过程中,灰姑娘故事陆续衍生出大量同型变异的作品,不仅在细节上多有分歧,在形式上也略存变化,其中一些也不乏相应的汉译本。以下略摭一二,以资谈助。
除了使用白话编译过《玻璃鞋》,孙毓修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载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中还以文言翻译了一篇17世纪法国作家“爵夫人安娜”(Countess D’Aulnoy)的《辛度利拉》(Cinderella),故事情节与《玻璃鞋》大致相仿。而由于使用文言,孙氏乘便夹杂了大量中国典故。开篇就介绍说,“辛度利拉者,波斯女子也。有姊二人,并丰容盛鬋,俊妙如大、小乔”;当舞会的消息传来后,又说“辛度利拉固不暇与俱,亦不屑与俱也。从此月夜穿针,花前顾影,画铜雀之黛,织天孙之锦,向鲛人以泣珠,指洛妃以要佩”;等到舞会召开当天,“长、次二女兄容饰并盛,如巫山之云,赴高唐之会。辛度利拉嗒然独处,作候门之稚子。霜天月夜,万籁俱寂,独坐而悲,继之以泣”;随后模拟其口吻感伤身世,“已矣!勿复言矣!无衣无褐,安能入争妍斗媚之场,此岂淡扫蛾眉朝至尊之时耶!”而借题发挥、大发议论的癖好也相沿未改,说起王子为选妃而举办舞会,他就深有感触:“少读汤玉茗《还魂记》,有云‘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盖相须甚殷,相遇偏疏,凡事类然,而于才子佳人尤甚。如有波斯太子之豪举,则可不作是叹矣。”这些内容并不算太艰深,但预设的读者无疑是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成年读者,和先前编译《玻璃鞋》主要为了满足儿童的需求已经迥然不同了。
由适夷(楼适夷)翻译的三幕剧《灰姑娘》,收录在同名剧作集中(开明书店,1931年)。据《译者小引》介绍,全书六个剧本均以世界语写成,作者鲁意司·勃理格斯(Louise Briggs)的生平已无法考知,但译者坚信此书“一定可以使我们许多可爱的小朋友们,得到大大的欢悦”,“可以使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在家庭中,多一个快乐的游戏”。出版社在宣传中也格外强调“儿童剧本的需要,已为现代教育家所公认”,而此书“极合儿童心理,情节简单,场面紧凑,表演时极有兴趣”(载1931年8月7日《申报》)。其中《灰姑娘》剧本取材于佩罗童话,而精简了不少人物和情节,以便于儿童排演。原作中为交代灰姑娘得名的来由,有不少她遭受欺凌虐待的描写,而剧本开场就是姐姐登台大呼:“阿灰,阿灰,你在什么地方?”自然是因为观众对故事早已熟知而毋庸赘言。原作中灰姑娘连续两晚去参加舞会,第二次才丢了鞋。而剧本中灰姑娘只去了一次,当晚匆忙逃归时就丢了鞋,直接让王子赌咒发誓“我一定要带了这鞋子去找她,即使要走遍世界也好”。想来是因为剧本篇幅有限,相似的内容不妨压缩省略。不过为了适应舞台表演,某些简略的叙述也会被适当扩充。原作里仙女教母最后出场,只是让灰姑娘再穿上漂亮衣服。剧本则另外安排她在众人面前陈说前因后果:“我来作媒人吧,灰姑娘是我的义女儿,她到跳舞场是我送她去的;王子,请你接待她吧,她将是你最亲爱的王妃。”全剧落幕时则上演众人齐声高唱:“啊,我们亲爱的灰姑娘,我们大家都爱你。现在你是我们的王妃殿下。祝你万寿无疆!王子,王妃,祝你们万寿无疆!”在现场表演时肯定更容易烘托欢快热闹的气氛。
同样是根据佩罗童话改编的作品,吴墨兰翻译的苏联作家特·加贝的四幕剧《灰姑娘》(立化出版社,1950年)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虽然也减省了原作部分情节,可同时又增添了不少出场人物和具体内容,因此篇幅反倒有增无减。灰姑娘一登场就有大段的独白,庆幸“姊姊不在家,家里就清净得多啦”,“现在我可以做半个钟头……甚至于整整一个钟头的主人啦”。随后她苦中作乐,将扫帚、火棒、烙铁、火钳等想象成到访的客人们,期间不断转换角色,模拟众人的口吻,商量着是否该去参加舞会,最终感叹:“算了,算了,这样看来,不管怎样都是去不成的了,还是留在家里吧,反正我们的命是注定了待在家里的。那么,这样吧,扫帚太太,请您代我们向王宫里的人问个好吧——替我,替火棒,替火钳,还有替烙铁向他们问好。请您告诉他们,我们身体都不大舒服——烙铁在发烧,火棒在脚抽筋,还有火钳在发风湿症。”时而欢欣雀跃,时而消沉低落,将她复杂纠结的心绪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形象较诸童话显而易见更为丰满鲜活。在改编过程中,剧作家也融入了新的主旨。当真相大白后,继母和姐姐们为了讨好灰姑娘,发誓不再让她继续撒灰,可那位入乡随俗改名叫作“柳静娜姨妈”的仙女却不以为然:“撒灰又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只知道烤炉子,不知道撒灰的人,才是最可耻的。……灰姑娘!你就让这个名字留给世界最好的姑娘们做外号吧。让人家说:(指着台底下观众里某一个小女孩。)你多么可爱呀!跟常常打扫灰尘的灰姑娘一样。(向另外的小女孩。)你多么光荣呀!跟整天劳动的灰姑娘一样。”将童话原先着力宣扬的善有善报,改换成对劳动最光荣的颂扬,大有与时俱进的意味。
吴墨兰的译本此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5年改版重印,可知很受读者们的欢迎。时隔多年此书另有叶小铿的新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而且似乎是依据经过剧作者修订后的版本,所以情节内容多有增饰。比如在原有的四幕前又添加了序幕,让宫廷小丑、大臣、市民代表、宫廷历史家及国王、王后相继出场,通过众人的交谈来交代故事背景;待四幕剧情结束后,小丑又再次登场,边弹边唱,简要归纳故事内容。有些情节则做了重要调整,吴译本中被仙女变成马车夫的是一只大耗子,和佩罗童话所述相同,叶译本中则改为仙女随身带着的大黑猫,因此仙女在临行前对他的仔细关照,也从原先的“今天半夜以前你不是一只大耗子,而是一个马车夫,你的马呢——也不是小耗子,而是最好的阿拉伯马”(吴译),改变为“这些骏马在前不久还害怕您的爪子呢,——可是以后它们就要听您的缰绳的指挥了”(叶译),恐怕更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逗引起读者尤其是儿童的勃勃兴致。此外还改易了部分译名,如两个姐姐在吴译本中仅作“大妞儿”“二妞儿”,叶译本则改为“绣球花”“百灵鸟”,透露出几分特殊的反讽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吴墨兰的译本中附有导演阿·葛洛斯蔓的《怎样上演“灰姑娘”》,对演员表演、舞台布景、音乐配曲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解说和指导;叶小铿的译本在最后也提到,“多年来,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曾多次演出这个剧本,收到良好的效果”,并“附有剧照多幅,供专业剧团演出时作参考”。与此类似的还有英国剧作家布赖恩·福布斯的《水晶鞋与玫瑰花》(陈国荣译,富澜校,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原先就是根据其参与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改写的。由此足见灰姑娘的故事并不只供读者在案头阅读,还可以在舞台上搬演以供观众欣赏。
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递嬗
随着各式各样灰姑娘故事的翻译和推介陆续问世,人们对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也越来越感兴趣。赵景深的《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系统讨论了童话的意义、源流、类别等问题,在第五章《童话的人类学解释》中还以灰姑娘为例,介绍了人类学派童话研究的方法。他根据英国民俗学家哈特兰德(Edwin Sidney Hartland)的研究,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变型式样,除了耳熟能详的“法国贝洛尔的灰娘”,另有“苏格兰的灰娘”“俄国的灰娘”和“苏格兰的印佛尼司的灰娘”。通过分析彼此的异同和关联,他指出“俄国和两个苏格兰的童话是一张下降的表格,一个比一个野蛮。但我们如把次序翻转过来,便可寻出这童话渐渐上升的径路,一直升到贝洛尔的童话”,可知出现各种灰姑娘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结果,佩罗童话并不是真正的源头,在此之前还存在更为古老的式样。
意犹未尽的赵景深随后又在《童话学ABC》(ABC丛书社,1929年)中特意设立了一章《柯客诗论灰娘》,简要介绍了英国学者柯客诗(Marian Roalfe Cox)的巨著《灰娘》(Cinderella: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Variants of Cinderella,Catskin,and Cap O'Rushes)。该书搜罗了流传在欧洲各国的345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分成“灰娘类”“猫皮类”和“芦衣类”三种类型,每一类又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各式变型。经过细致周详的考察,柯客诗“替各种《灰娘》发表的先后排了一个年表,时间是从一五四四年到一八九二年”。尽管蒐集材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就是这样多,还没有包括净尽,最多只到一半”。赵景深由此感慨万分:“《灰娘》的故事简直没有一个完,可以当作童话进化史来看。”
杨成志和钟敬文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是从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概论》(Handbook of Folklore)中翻出来的”(钟敬文《付印题记》),原由英国民俗学家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据前人研究结果修订而成。其中第二十种类型即“辛得勒拉式(Cinderella type)”,简明扼要地归纳出灰姑娘故事所含的四个要素。与此相似而更为细致的则是美国民俗学家翟孟生(R.D.Jameson)著、于道源翻译的《童话型式表》,其中的“灰女(Cinderella)型”(载1936年《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将这个故事拆分成六大要素,每个部分又涵盖了不同的变异情况。比如第四个要素是“她的被证实”,除了“用鞋去实验”,还可以“用她失落在他的汤里或是面包里的指环”,或者“用她的能力去作几样艰难的工作,如去摘金苹果等事”。
这些类型学方面的研究显然会给中国学者带来不少启发和借鉴,正如钟敬文所期盼的那样,“在想略解欧洲民间故事的状态,或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思加以整理和研讨的人,它很可给予他们以一种相当之助力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付印题记》)。既然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各地流传如此广泛,形式又如此纷繁,那么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荷兰学者田海在近著《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赵凌云等译,黄宇宁等校,中西书局,2017年)中提到:“欧洲文化中另有一种广为人知的传说,而早在9世纪中国就有与之相似的文字记录了,这便是‘灰姑娘’的故事以及‘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的一种变体。”(见第六章《妖妇与邪帝》)他所说的源于中国的文字记录,出自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他在注释中还特意提醒读者“阿瑟·韦利是第一个指出这个故事的存在的西方学者”,并补充说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在七八十年代的论著中“有细致的研究”。这些介绍确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也不可讳言忽略了其他中外学者在此前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早在1914年——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阿瑟·韦利才刚刚开始自学汉语,周作人就发表《童话释义》(载1914年《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七号,后改题为《古童话释义》,收入《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已经指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认为在晋唐小说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童话的作品,只是前人未加抉剔甄别罢了。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还举出数例,略加诠说。第一个例证就是出自《酉阳杂俎》的“吴洞”,讲述吴洞之女叶限遭受继母虐待,有一次乘其不备,参加洞节集会,被发现后仓促逃归,不慎遗落一履,被陀汗国国王辗转获得,国王经过百般寻访,最终找到叶限,“以叶限为上妇”。周氏在摘录原文后附有按语,称这个故事“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式。坊本《玻璃鞋》即其一种,辛特利者,译言灰娘,今叶限之名谊虽不详,然其本末则合一也。中国童话当此为最早”;还指出“今世流传本始为法人贝洛尔所录,在十七世时,故柯古此篇应推首唱也”,认为段成式(字柯古)的记载,才是灰姑娘故事的真正源头。这个发现很快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于道源在翻译《童话型式表·灰女型》时有一段《译者附记》,提到柯客诗虽搜集到三百多个同型式故事,但并不知道最早的记载当推《酉阳杂俎》,“这在前几年已经是经周作人先生提到过了”。
不过周作人还不能算是首位发现叶限与灰姑娘经历相似的学者,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在此前写过一篇《公元九世纪中国典籍中所记载的辛迪瑞拉故事》(《西歷九世紀の支那書に載せたるシンダレラ物語》,载1911年《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二十六卷第300号,后收入《南方隨筆》,岡書院,1926年),已经发现《酉阳杂俎》的这段记载。他不仅将全篇译为日语,还和欧洲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做了比较,指出人们都误以为灰姑娘故事是欧洲所特有的,段成式的叙述将有助于开拓大家的研究视野。早年留学日本且喜好民俗学的周作人,对南方熊楠并不陌生。他后来在《我的杂学》(收入《苦口甘口》,太平书局,1944年)中回忆,“我的杂览从日本方面得来的也并不少”,其中就有“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周氏弟子江绍原撰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曾寄呈南方熊楠请教。南方不仅回信商讨,顺便也恳请江氏解答自己读书时的疑惑,由此还引起周作人的回应(见江绍原《日本南方熊楠翁来信和我们的回信》,连载于《北大日刊》1931年1月28日、29日、30日),可见周作人与南方熊楠应该还有过交往。尽管在写《童话释义》时,周氏未必读到过对方的论文,很可能只是殊途同归的暗合,但南方熊楠的研究还是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谢宏徒在《中国的灰娘故事》(载1928年《青海》第一卷第五期)中就曾介绍:“灰娘故事的转变很多,读日人南方熊楠的《南方随笔》上卷,有一段谈到西历九世纪时中国书所载的灰娘故事,他在《酉阳杂俎》卷一,发见一段故事,与欧美流行的灰娘故事相似。”
在南方熊楠、周作人相继发现《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后,另有学者继续研究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递嬗。赵景深在应邀为刘万章所编《广州民间故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撰写序言时喜出望外,他发现书中《牛奶娘》《疤妹和靓妹》两篇居然糅合了灰姑娘故事的因素,“这简直是一个发现!”“这不但我高兴,恐怕那位搜集了三百四十五个大同小异的灰娘的柯客诗姑娘知道了也要高兴呢!”然而在兴奋之余,他还是怀疑这些民间故事并非原创,而是受了外来童话的影响,“因为我总不相信灰娘是我国本来就有的童话”。在序言的最后,他提到另一位民俗学家张清水正在编录一部与此相关的“蛇郎故事转变集”,“我祝他做中国的柯客诗姑娘”,“能给我一个参证的机会”。很可惜,被寄予厚望的张清水英年早逝,计划编订的故事集并未正式出版。所幸在《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一文(载1929年《民俗》第七十五期)中,张清水(署名“清水”)还是对此有过简略的讨论。他也认为佩罗版《灰姑娘》“与流传广州、东莞、鹤山等处的蛇郎故事,多么相似”。在逐一比对过情节后,他还指出两者“所相似的,是首
段,中段以后,的确相差太远了”。在此之后,钟敬文先是参照《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另行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一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列有“蛇郎型故事”一类,归纳总结其叙事要素。不久他又专门撰写《蛇郎故事初探》(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指出“除了西部外,其他如北之直隶,南之广东,东之江、浙、鲁、闽、皖等,都有同母题的谈讲流传着”,并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考察其复杂的构成,分成“原形的”“变态的”和“混合的”三大类,最后一类中就包括“与灰娘式及螺女式混合的”。经过这些学者的搜集和研究,可知灰姑娘故事在近代中国也有变型流传。
编撰过《童话型式表》的翟孟生在二三十年代时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对中国民间传说做过一些专题研究。他在《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1932。按:此书有田小杭、阎苹中译本,改题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文均据此译本)中,率先讨论的就是“Cinderella in China”(《中国的“灰姑娘”故事》)。他同样注意到《酉阳杂俎》的记载,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许多细节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围绕那只丢失的鞋,他介绍了流传在印度南部、埃及、安南、希腊等地的类似传说,认为“鞋和结婚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的,这在各地都是一样,尽管由于地方的差异而不尽相同”。通过反复比较,翟孟生认为唐代的叶限就是灰姑娘故事的一种变型,“至于讲是叶限传到了欧洲,还是我们的灰姑娘在九世纪到了中国,或者她们最初都是在埃及或印度,都还是些难以确定的问题”。尽管没能对起源问题做出最终判定,但这个中国版故事无疑已经引起这位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此书出版后也得到中外学界的充分肯定,有一篇书评盛赞其“分条疏证,解释详明,每用比较方法,参证西方故事以研究中国传说”,“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采薇《中国民间传说三讲》,载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六号)。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研讨灰姑娘故事时,提到“公元9世纪有《灰姑娘》的优秀的中国文学文本出现”(《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参考的也正是翟孟生的研究。
早年留学英国且精通多种外语的杨宪益对灰姑娘的流传衍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中国的“扫灰娘”Cinderella故事》(载1946年《新中华》复刊第四卷第九期,后收入《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中根据段成式的自述,认为故事的源头仍然应该在西方,“至迟在九世纪或甚至在八世纪已传入中国了。篇末说述故事者为邕州人,邕州即今广西南宁,可见这段故事是由南海传入中国的”。可惜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杨宪益虽然知道柯客诗(他译作“柯各斯”)搜集过大量同型故事,却因“现在无法找到”而未能对自己的推断做全面深入的论证。不过他还是凭借渊博的语言知识,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佐证。他发现在格林童话中,灰姑娘 的 名 字是Aschenbr觟del,“Aschenl一字的意思是‘灰’,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鲁萨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酉阳杂俎》中的女主角名叫叶限,“显然是Aschen或Asan的译音”。不仅如此,在法文本故事中,灰姑娘穿的原本是“毛制的鞋Vair”,流传至英国时被“误认为琉璃Verre”,于是她又改穿了玻璃鞋;而在中文版中,叶限穿的是“金履”,却“其轻如毛”,“大概原来还是毛制的”。周作人在考察《酉阳杂俎》时,已经对“叶限之名谊”感到困惑,又发现“其履或丝或金,或为玻璃”(《神话释义》),而未能获得确解;在上文提到的各家译文中,这只关键的鞋子也确实质料不一而千变万化。杨宪益的分析要言不烦,既足以释疑解惑,又能够以小见大,为追溯灰姑娘故事的缘起和流播提供线索。
对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做过全面系统调研的斯蒂·汤普森认为,“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不仅因为它被收入很多有影响的故事集,更因为围绕着它“还有一段悠久的文学加工史”(《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而正是有赖于众多中外学人的旁搜远绍,才对这段加工史的不少重要环节做了启人深思的研讨。在此之后,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等又参考国际通行的AT分类标准编码,对这个故事加以著录和分析,使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得以借此沟通交流,并发现了更多来源各异的同型作品。尽管灰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疑惑恐怕仍将悬而不决而未能遽下断语,然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妙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