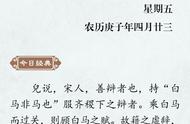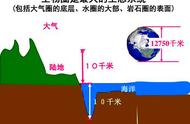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代以降,独尊儒术。自此儒教成为显学,配合释、道,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撑。然而在先秦诸子中,有这样一家,虽然名不见经传,其学说历来也饱受批评,但是即使今天看来,其中所蕴含的理性光辉和思辨张力,却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那就是名家。名家一派,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就著作而言,仅有《公孙龙子》之书尚存,而惠施的观点,多散见于《庄子》。因此公孙龙的地位较惠施更为重要。而且,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公孙龙可以算作是我国的国产柏拉图。
《庄子》的《秋水》记载,公孙龙称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里当然不是《庄子》要夸公孙龙,而是先树立靶子,再对其进行嘲笑的套路。但是公孙龙的学说的特点及其为人的口才,却可以从其中窥见一斑,即“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
所以名家也称诡辩家,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爱抬杠”。公孙龙抬杠的著名案例,当属于“白马非马”了。
相传,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秦国严防瘟疫传入国内,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禁止赵国马匹入关。这天,正巧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
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
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
关吏说:“白马是马”。
公孙龙说:“我公孙龙是龙吗?”
关吏一愣,但仍坚持说:“按照规定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不能入关,管你是白马还是黑马。”
公孙龙微微一笑,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说,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你要马,给黄马、黑马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由此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
关吏越听越迷糊,被公孙龙这套高谈阔论搞得晕头转向,被侃晕了,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骑白马过关。于是公孙龙的《白马论》名噪一时。
在公孙龙上述的论证过程中,主要有两个论点:(为确保论据的真实性,这里不再以故事中的对话为依据,而以《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为依据)
第一,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者非命色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一点是在强调“马”、“白”、“白”、“马”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里是强调,“马”、“白马”外延的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由于“马”和“白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虽然有这样的论述,但是“白马非马”的结论却与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是相违背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对“白马非马”中的这个“非”字,或者说“白马是马”这个“是”字的理解上。
我们平时说“白马是马”,其实是在说“白马属于马”,这里的“是”,是“属于”的意思。但是公论龙论证“白马非马”,并不是在论证“白马不属于马”,而是在论证“白马不等同于马”。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感觉自己是被骗了,因为公孙龙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非”的概念,来跟我们进行抬杠。因此,历史上许多人一直对名家的这种做法很不屑。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之言,其中论“名家”曰: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
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这种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功利性的价值评判,认为其无助于生产力的解放、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因此是无用的,是“治怪说,玩绮词”,是哗众取宠。
冯友兰先生认为,名家的辩者所持有的论调和我们的感觉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辩者是在用理智观察世界,而我们是在用感觉观察世界,理智所见与感觉所见固然不同。另外,研究一种学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对其的价值评判,而非对学说本身的研究之上,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这也提醒我们,对任何一种学说,一定要多方求证,深入查看之后,再做出价值判断,否则我们将会错过许多极有价值的知识和智慧。于我个人而言,了解名家的意义,恐怕在于,与别人斗嘴扯皮时,战败的次数大为减少。(笑)
关于白马到底是不是马的问题到此应该算是结束了。但是人类对于思辨的追求,对于语言的探寻,对于存在的认识,却永远不会终结。而我们了解过去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从古人的位置中,了解今人的处境。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眺望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