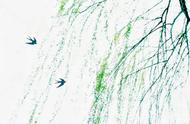作者:黎荔
您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
杜拉斯回答说:“这很容易回答,爱。”
爱是故事的唯一真相。在她眼里,没有爱的时间是无权被记住的。

这是我喜欢的一位法国女作家,她的文字温柔而野蛮,优雅而诡谲,总有一种动荡不安、摄人心魄的力量,如梦呓般的倾诉,被膨胀的情绪所推动,不顾一切,向前向前,有时超速,急刹车,有时峰回路转,奇险迭出。她的小说始终重复一幅画:一个男人朝一个女人走去,一点一滴靠近,贴紧,稍稍挣扎,再靠近,贴得更紧……然后,消逝。
“即使到了八十岁,我也还能爱。”她在小说《情人》开篇这样说——
“当我年华已逝的时候,一天,某个大厅里,一位陌生男子朝我走来。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来是特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比从前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这是缠绕她一生的图景,爱和被爱,永不停歇。“我喜欢你。真好。我喜欢你。突然又那么缓慢。那么温柔。你不会明白。”

爱就是旋涡,投身爱就是要把时速、狂风和浪尖创造出来。疲惫、暧昧、*、死亡,她的讲述似乎没有章法,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但那些诡秘的逼视与穿透力,总是意味深长,让人陌生和不安。
杜拉斯作品中,每次发生的爱,都是为了冲上浪尖——从读第一行起,你就能嗅出那股令人屏息的酝酿爱的气味,如同一列黑天鹅绒般的弯曲楼梯,它使你情不自禁地踩上去,有种危险,有种亢奋,有种腥红的类似唇膏和纤细脚踝的刺激。她邀你随她的身体和灵魂一起去冲浪,一程程颠簸,一程程焦虑、渴念和恐惧,爱如此迷乱,一如那不可期的未来的风。
杜拉斯15岁之前出生在越南南部,18岁迁居法国。她少女时代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此后闪烁和飘忽的词语气质:茂密的椰子树,暴雨中的三角洲,自卑的窝棚,死亡和*的母亲和哥哥。惊惧,幻想,怀疑,逃脱。深不可测的丛林,威严空旷的河流,海潮和海水的涌入。她一生的小说似乎都在补充和绵延自己的少女经历,渴望陌生的邂逅,迷乱的凝视,以及不详的离别,她说*是人身上最专横的东西。

恋爱是行动,一次,数次,无数次,都还是行动;而爱情,则是生命的本质,是某种形而上。恋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老,而时间的沉淀只会升华爱情,令爱的更爱,恨的更恨,知道的爱得透彻,了解的变得澄明;恋爱是故事,爱情则是故事的可能性。爱情之于一些人,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杜拉斯如是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去爱、将爱坚持了一生、完全遵从内心和人性态度的人。
举目望去,流星雨一样短暂的爱情游戏,在现代社会早已司空见惯。在这充满猜妒的生活空间里,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变得像一座座城堡,强弓硬弩、装备精良,生怕被人伤害,受伤了首先想到的也只有以怨抱怨。爱情的高贵气质正日益枯萎,纷飞的花瓣如雨在风中凋零。
“人生易老天难老”,时光的流逝,也许是最能引起普遍共鸣的宇宙性思索了,所以我们要在无穷的时空中确定出我们自己。假如生命无穷,人生没有丧失,我们是否还会有激情,还会有感动呢?假如人身有如金石,人类是否还会有艺术,还会有创造呢?从人们心中召唤出热情来的,是人要求肯定自身,在无区别的流逝中,区分出自己来的最强烈的渴望。

失恋、失意、伤逝、幻灭、孤独,这类感情,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无谓的——人反正是要衰老和死去的,现存的一切反正都要毁灭,生命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偶然组织起来的结构和短暂过程,恐惧和伤感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元的一些不自主的活动而已。然而,当这一切都得到解释之后,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恐惧和伤感依然存在。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有了期待,才会不得不面对,时光无情的摧残。其实,由爱故生怖,也是某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无法释怀的情感,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神奇的种子,它开出了红艳的花。每天心中开出一朵花的人生,是与精明计算、铜墙铁壁的心完全不同的人生。去爱吧,如同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样。爱中根本没有成败输赢,爱给每一个人带来了生活的崭新道路,让我们发现以往无法发现的自我。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