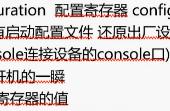◎唐山
很少人想到,今年是《源氏物语》正式进入大陆的40周年纪念。
1974年,台湾译者林文月的全译本最早问世,当时未引入,因此前丰子恺在上世纪60年代已完成全译。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回忆:“编辑部的先生对此不感兴趣,大包大包用毛笔字写得恭恭正正的原稿,却在编辑室的柜子里沉睡到十年之久。”
直到1980年12月,《源氏物语》全译本第一卷才出版(第二、三卷于1982年6月、1983年10月出版),到1986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总印数已超25万册。
我国学术界对《源氏物语》的正式研究,乃至普通读者真正接触这一名著,均以1981年为开始。2001年,学术界为此还举办了引进20年的研究会议。
与20年庆比,40年庆可谓冷清——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了叶渭渠、唐月梅的译本(以下简称叶唐译),它在15年前已面世,插图略丰富。
对于《源氏物语》,最常见的提法是“日本的《红楼梦》”,其实它比红楼梦早了近800年。周作人曾说:“(源氏物语)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的‘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代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部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紫式部本姓藤原)抢了过去了。”
丰子恺的译本长期被忽视,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争议。
周作人曾问负责校阅的钱稻孙,钱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
周作人的评价则苛酷得多:“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丰子恺主要参照的底本是谷崎润一郎、谢野晶子的现代日语转写本,谢野晶子又认同“豪杰译”,她说:“勿需一一沿袭原著的表现方法,勿需遵循逐字逐词的翻译方法,以原著精神为我物,敢作译者自己的自由译。”
丰子恺译本流畅生动,语言精美,但没有原著中古日语的味道,引起周作人不满。
此外,周作人对丰子恺有误解。1950年,周作人刚出狱,迫于生计,将《儿童杂事诗》交《亦报》,化名东郭生发表。《亦报》找丰子恺配图,此时丰子恺已不甚作画,碍于旧情,还是出手帮助。发表时,画大诗小,似成周作人给丰子恺的画配诗,致周作人的自尊心受挫。
周作人晚年靠在香港媒体工作的曹聚仁到海外发稿、赚稿费,曹聚仁与丰子恺曾是好友,抗战时交恶,可能也影响了周作人对丰子恺的看法。
从普及看,丰子恺译本已成经典,对中国“源学”有开拓之功。
丰译招致批评,因钱稻孙本想译《源氏物语》,第一帖译出后,引起轰动。以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为例,来看钱译、丰译、叶唐译的区别:
钱译:是哪一朝代来,女御更衣好多位中间,有一位并非十分了不得身份,却出众走时的。从开初就自命不凡的几位,都道刺眼儿,褒贬嫉妒于她。
丰译:且说天皇时代,某朝后宫妃嫔众多,内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却蒙皇上万般恩宠。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刚入宫时,便很是自命不凡,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便十分忌恨,处处对她加以诽谤。
叶唐译:且不知是哪一代皇朝,公众有众多女御和更衣侍候天皇。其中有一位更衣出身虽不甚高贵,却比谁都幸运,承蒙天皇格外宠爱,缘此招来其他妃子的妒忌。
三者比较,丰译文采颇佳,叶唐译更接近原文,钱译则明显高出一个档次,属于逐字逐句的直译,甚至和原文的标点都一样。钱稻孙依照的是山岸德平的校注本《源氏物语》,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版本。
可惜钱稻孙译得太慢,一个月才完成4000字,原本交给他做,后来转给丰子恺。但责任编辑文洁若多次表示,希望重译《源氏物语》,第一帖保留钱译,从第二帖开始继续译。
文洁若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丰译本重普及,语言模仿了《红楼梦》,所以许多读者是用读《红楼梦》的方式读《源氏物语》,认为它也是以爱情为表,目的是“揭露贵族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
对此,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曾批评:“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一样,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日本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源氏物语》有两大难懂:
其一,故事性差、节奏拖沓;
其二,作为爱情小说,为何要拉拉杂杂记那么多政坛琐事?
这与日本文学的特色有关。
在《源氏物语》的时代,日本主流文人用汉语,平假名是女性专用,物语也只是闺阁读物。通过小说,紫式部寄寓了身为“第二性”的自我追寻之路——在看似琐碎、无聊的记录中,她努力在挽留自我。她将悲愤、无奈、苦痛、失落,转化成对生命本身的怀疑,即物哀。
紫式部的触景伤情,与当时日本文人在中国文化压力下,无法找到自我的迷茫相激荡,于是,物哀成了“日本性”,被格外发扬光大,形成独特的写作传统:不讲故事,少发评论,只用絮絮叨叨的白描来寄托自己,妙在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取舍中,隐含了作家的真情感。
只有深入这种细腻,才能被《源氏物语》那微弱但无边的忧郁击中。
明治时期,黄遵宪与日本学者源辉声曾在笔谈中,谈到《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源辉声不仅读过《红楼梦》,还准确指出两书“作意能相似”,黄遵宪却没读过《源氏物语》。
精英视野对一个民族的命运,必有微妙的影响。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几乎同时被译介到西方,但《红楼梦》最早的介绍者都是外国人,而将《源氏物语》节译成英语的,却是日本驻英外交官末松谦澄,他得到了德川氏的资金支持。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参加巴黎世博会,造访英法,引起轰动。翌年《源氏物语》出版,逆转了英国人认为当时日本“如同黑暗的中世纪般愚昧落后”的印象。
末松谦澄在译本的前言中,特别塑造了两个神话:
其一,它是现实主义小说,与当时英国文学主脉契合;
其二,它是爱情小说,当时英国人也将爱情视为贵族的高贵情感,日本女作家几百年前就能写爱情,成了文明的象征。
有了末松谦澄的铺垫,1925年—1933年,英国著名诗人阿瑟·威利历时8年,将《源氏物语》全译成英文,译本质量极高,使《源氏物语》成了世界文学经典,胡适先生曾读过这一版本。至于《红楼梦》,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英文全译本。
越深入了解世界,越能更好地表达自己。《源氏物语》堪称文化营销的成功范本,而中国读者至今还无法看到更忠实于原文、更有学术价值的《源氏物语》译本。好在时光流逝,还有一家出版社愿重印《源氏物语》,为40年节点留个纪念,也算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