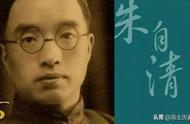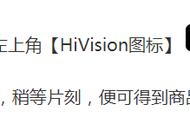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句式结构相同,原句似有省略“志于”两字,完整表达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志于)立;四十而(志于)不惑;五十而(志于)知天命;六十而(志于)耳顺;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虽然文句噜苏但意思明确,不至于歧义。
结合上下文,释义就是:我(指孔夫子自己)十五岁开始以学习为志向;到了三十岁以确立一整套道德理论体系和个人修身标准为志向;到了四十岁以对这套理论体系和标准不再疑惑为志向;到了五十岁以知晓理论体系和标准的自然天道来源为志向;到了六十岁以对于舆论评介好坏都宠辱不惊且坦然接受为志向;到了七十岁以处世为人行事追随心性,契合自然天道不出格为志向。
今天只谈“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的“惑”,到底是什么惑?
《论语》通篇有九个地方提到了这个“惑”,筛选出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地方来辅助解读这个“惑”。一个是崇德辨惑,原文1、原文2。一个是知者不惑,原文3、原文4。
原文1《论语·颜渊第十二》:「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袛(音同之)以异。’」
原文2《论语·颜渊第十二》:「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音同特)、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原文3《论语·子罕第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原文4《论语·宪问第十四》:「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关于“崇德辨惑”,有两个人向孔夫子请教。一个是子张,一个是樊迟。本着“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方针,夫子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
颛(音同砖)孙师,字子张,孔夫子学生十二大贤之一,生于公元前503年,比孔夫子小48岁,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他勤学好问,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的人和事。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过”是因为子张交友多广,但有点过头了。子张的秉性偏激,因此“师也辟”。荀子在《非十二子》说:“弟佗(颓唐的样子)其冠,衶襌(音同重单)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意思是说,头上胡乱戴着帽子,嘴里说些淡薄无味的话,走路还学着禹、舜的样子,子张氏之儒就是如此。这里从反面清楚了解到子张不拘小节过于豁达的栩栩如生形象,和喜欢广交朋友的特点一致。子张终身未仕,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对孔子本人是崇敬的,对孔子的思想是认真学习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忠、信思想的态度上。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樊迟(前515--?),名须,字子迟,比孔子小36岁,樊迟名字中有个“迟”字,反应迟钝,人如其名。他未拜孔子为师之前,已任官职。孔子回到鲁国后他才师从孔子四五年,他勤学好问,曾三次向孔子问仁,孔子给他做了解答,都不一样。孔子讲的是治天下的大事,是仁,是爱,是宏大而高深的问题,而樊迟更喜欢细小而具体的事,比如养花弄草种庄稼。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理解不了孔子的思想,只能做些小事,并且是孔子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种庄稼并不等于没有未来,他最后成了农家的著名人物。唐赠“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樊迟并不聪明,他对孔子的学说理解得很慢,也达不到老师孔子的高度。樊迟是我们大部分中下根性普通人的代表。
子张心高意广,交友广泛,“师也过”,“师也辟”,对于这样聪慧并且有性格的学生,夫子有高度有深度从正面直截了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崇”当“高”字讲,“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也可解为使动用法,使其德行崇高。崇德强调忠信,忠信是德之本,“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无惮改”。“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信是什么?忠信就是《中庸》说的“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什么?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给“诚”定义为“一念不生是谓诚”。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别人,真诚面对这个宇宙。所有浮华表面的东西全部去除,能够剩余下来并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再会有变化的,才真正可贵。内心真诚,真诚到极处,一念不生,连生这个一念不生的念头都没有,那就是佛菩萨了,境界高啊!不贪不嗔不痴,那也只是人天福报,一念不生就是如来果地境界,真正的不可同一日而语。徙义:向义迁移,唯义是从,闻义迁善。改变,向善的方向改变,并且“择善固执”,“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退转境界不跌落。忠信就是一个基本人生态度,一种立身处世的心态,徙义就是好的东西我能够随时随地去模仿学习并持之以恒向好的方面改变不再回头。以忠信为本,能闻义即迁而从之。这样有什么一个效果呢?《周易》讲“日新之谓盛德”,每日不断更新叫崇高品德。《论语》里面同样强调“见其进也,未见止也”。所以崇德从来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这个德一定给人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动力,让人生生不息,一直都在砥砺前行。当樊迟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樊迟较为愚钝,这时候夫子首先表扬了:善哉问!好问题,问得好!夫子没有没有更多的说教,关于“崇德”就是“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事后得就是先致力于事,把利禄放在后面。孔子在回答樊迟“什么是仁”时,告诉他“仁者,先难而后获”,此处“崇德”就是“先事后得”,也就是首先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有耕耘才会有收获。
理解了“崇德”,“辨惑”就容易了。“辨惑”就是在“崇德”中遇事迷惑颠倒,纷纷扰扰各种迷惑,拿不定主意,此时就需要拿标准来对照,标准就是标尺,标尺就是“崇德”。标尺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得清清楚楚。
1.不困于私情。夫子针对子张大大咧咧,快意恩仇的性格,孔子并没有就“辨惑”明确讲怎样做,而是从事相上举出“惑”的一种现象:“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意思是同样的一个人,喜欢他的时候,恨不得什么好东西都给他,让他过得最好,讨厌他的时候呢,恨不得当场就弄死他算了,对于一个人到底是爱还是恨都搞不清楚,“惑”是感情上的困惑,情绪上的障碍,私情就是爱和恶,私情就是自私情欲,若为私情所困,那肯定是“惑”。生活中,我们难道没有这样的经历吗?在理智的角度,这样的荒诞就是“惑”。当我们缺乏情感管控能力,当出现爱与恨的两种极端情绪时,无所适从,进退失措,这就是失守中道。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恶,去声。爱恶,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爱恶而欲其生死,则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则惑之甚也。”爱和恶都是人之常情,用自己的主观爱恶来作为判断标准,那就是“惑”了,既要想让人好好生活,又要讨厌想让其消失死亡,走情绪的两个极端,这个“惑”就更加明显了。净土宗祖师藕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中禅解:“四个‘其'字,正显所爱所恶之境,皆自心所变现耳。同是自心所现之境,而‘爱欲其生'、‘恶欲其死',所谓‘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非惑而何?”爱和恶都是自己的意识心所变现的,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真心非幻,一念妄动亦即成幻。古来圣人贤者都认为有爱有恶为人之常情,不可一概而摒弃。人情之偏执、迷执,以爱、恶之私为甚,乃至心智蒙蔽,放纵私情,无清醒冷静之明。为情所困,此即为凡夫俗子。爱恶能有所节制,则可克己修为以使之回复至中正无私,若情绪走极端,不是“惑”是什么呢?‘诚不以富,亦袛(音同之)以异。’这句是引用《诗经·小雅·我行其野》,就算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吧。说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对变心的丈夫一会恨得咬牙切齿,一会又割舍不下,这种爱恨交加的心情就叫做“惑”。这里用举例强调来进一步说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样爱恨交织的矛盾认知心理就可以称为“惑”。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惑”,明白了这个例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饮了这杯水就知道了。有些古籍里推论说这句话是“错简”,以前的记录都记录在竹子做的“简”上,以为这个竹简搞错了位置,甚至指出了应该在哪里,其实没有从整体上来考虑这一句话的用处。
2.不堕于私忿。夫子针对樊迟喜欢做“小事”,理解思维有点“延迟”的性格。相对于子张,夫子给樊迟的答案就比较直接了。夫子和樊迟的关系在《论语》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开始就是樊迟向夫子请教种庄稼,夫子说不如老农,樊迟请教怎么种花弄草,夫子说不如种花农。等樊迟退出去了,夫子就直呼其名,说他是“小人”,做小事的人。后来一直到“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此时樊迟已有明显的进步了,夫子夸奖说:善问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先事后得,犹言先难后获也。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专于治己而不责人,则己之恶无所匿矣。知一朝之忿为甚微,而祸及其亲为甚大,则有以辨惑而惩其忿矣。樊迟麤(音同粗,也是粗的异体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接下来,朱熹又提到:“范氏曰:‘先事后得,上义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动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于细微,能辨之于早,则不至于大惑矣。故惩忿所以辨惑也。为私忿而争斗,便是忘其身和忘其亲的行为。'堕落于私忿中,内忘其身而外忘其亲,岂非人生的一大昏惑?古往今来,人之情欲易发却难制,尤其是爱恶和忿怒为甚。情欲和忿怒会遮蔽、迷惑人的双眼,扰乱人的心智,使我们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让我们分不出是非对错,固执己见、固塞偏执、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等等。樊迟并不是孔夫子第一流的学生,不够聪明。针对樊迟的根性,孔子没有告诉樊迟什么高深莫测、云里雾里的玄妙理论,而是平实浅显,切实可行的生活道理。孔子说做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要问自己的利益得失,这就是“先事后得”。自省己过,而不是攻击别人的过失,不就是修慝吗?《孟子》在《离娄章句上》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遇到了挫折和困难,人际关系处得不好,就要反躬自省,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但是我们在平时的做法却往往与圣人之道南辕北辙了。而私忿对于人危害极大,互骂伤感情,互殴伤身体。假如忍不住一时的气忿,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安危,乃至忘记自己的父母亲属,牵连并让他们遭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不就是“惑”吗?樊迟正值青年气盛,容易受外界刺激引诱而意气用事,《论语·季氏》的君子三戒之一“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一个有修养的人,能够自己管理好驯服好自己的气血之动,如果让气血涌动的情绪引领掌控成心志的主导,那无疑就是一件自己迷惑自己的事情。孔夫子“辨惑”的说法是对人心迷执所注入的一剂清醒良药。看问题考虑事情,贵在保持客观冷静,而冷静重在“辨惑”。《论语·子罕》中告诫“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要凭空猜测、不要主观武断、不要固执、不要自以为是。这里的“毋我”,并不是佛家的“无我”,佛家的“无我”,那是“五蕴皆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所有组成“我”的种种要素都是刹那生灭,都是“一合相”,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存在。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就不一样,明天的“我”哪里会和今天的“我”一样呢?那么哪里有一成不变的“我”呢?这就是佛家的“无我”。真正契入到佛家这个境地,就非常好理解孔夫子在这里说的“毋我”,以及循循善诱式地教导樊迟不要“一朝之忿”,佛家的“无我”,没有这些情识,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迷惑呢?
当我们一起学习了上面很多内容,这里的“辩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点——情绪管控。没有其他了,也就是说,只要情绪管控妥当,保持必要的清醒和冷静,才能有机会真正做到“无惑”,这就是“辩惑”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辩惑”不就是为了“无惑”吗?子张以及樊迟向夫子请教“辩惑”,夫子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用不同的方式,谆谆教导了相同的道理,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参照佛家说法,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情识不仅仅只有夫子教导的“爱”、“恶”、“忿”,还有其他的情绪反应,难道就不需要避免吗?确定要做到情绪管控,当然也需要控制自己的“喜”、“哀”、“惧”、“欲”,答案显而易见。《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有:“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进一步补充说明了这个道理。凡是情绪的东西,只有做到了切实管理和控制,那么此人和真正的君子就相距不远了。
生老病死,喜、怒、哀、惧、爱、恶、欲,哪一个不是苦?佛家有:苦苦,坏苦,行苦。人生哪里没有苦难呢?世态炎凉,岁月静好;往事悠悠,弹指一挥;回首之间,恍然大悟。一旦做到了管控情绪的“四十而不惑”,这样的人是理智和清醒的,只有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才是真正的“不惑”。而真正的拥有“不惑”那才是智者,那么《论语》里面说的“知者”就是这个意思,“知”就是“智”的通假字,读音就是读“智”,第四声。
如何真正做到“不惑”?唯有“知者”。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智、仁、勇”。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两次,详细见上面原文3、原文4。有智慧的人能洞察真伪并且知道世界的本源,不会被假象所迷惑,有知亦有不知。故知者不惑,非无所不知,乃不惑于知与不知的界限也;仁德的人心怀天下,没有私心,没有忧愁。故仁者不忧,非无忧无虑,乃无私忧,其有忧者,则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勇敢的人有舍生的勇气,不会畏惧。故勇者不惧,非狂妄自大,实乃义所当为,无畏无惧也。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分别注疏了,1.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2.知,去声。自责以勉人也。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犹云谦辞。尹氏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南怀瑾的《论语别裁》里是这样说的: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仁者不忧”,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
藕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中禅解:卓吾曰:使人自考。方外史曰:三个“者”字,只是一人,不是三个人也。仁者、知者、勇者,三个“者”字,正与“道者”“者”字相应,所谓一心三德,不是三件也。夫子自省,真是未能。子贡看来,直是自道。譬如华严所明,十地菩萨,虽居因位,而下地视之,则如佛矣。
一般我们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一切的事物认知的状态:知或者不知,亦知亦不知,非知非不知,若能了然那就是智慧超群聪明绝顶了。佛家有类似的论断,“离四句,绝百非”。这四句就是:“有”一句,“无”一句,“亦有、亦无”一句,以及“非有、非无”一句。举个例子,一、“有”,这是树叶;二、“无”,这不是树叶;三、“亦有、亦无”,可以说是树叶,也可以说不是树叶。四、“非有、非无”,这不可以说是树叶,也不可以说不是树叶。佛家认为这四句包含了宇宙的万有、一切人事物的森罗万象。儒家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儒家只有知和不知。儒家的知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可见可闻。可见可闻,便会形成知识,知识之知,很简单、很分明;第二是不见之隐、不显之微。隐微之知,思维之知,入于智察,是对前面知识之知的反省,此二者合并,就是知之为知之;第三是不可见,不可闻。子曰:不知为不知。人往往对于自己所不知的,以经验,传闻,主观臆测等来充填为已知,用已知覆盖未知,轻易给出符合自身经验以及自身利益的判断,无法做到不知为不知,这就是愚昧的开始。
儒家的“不惑”,不是事事皆知,而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承认这点,难啊!此时的儒家端的是个铮铮铁汉子,棱角分明,斩钉截铁,哪有迂腐痕迹?绝对没有丝毫拖泥带水。那么儒家的“知者”不就是能够践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吗?“儒”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员,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一飞冲天,“儒”就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史载《论语》前后共有三个版本,即《齐论语》《鲁论语》《古本论语》。其中《古本论语》和《鲁论语》合并成现今传世版本,而《齐论语》相比传世版要多出《问王》、《知道》两篇。令人惊喜的是,2011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出土了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竹简版本,并且发现了《知道》篇。按照《论语》各篇的命名原则,《知道》即为首章“孔子”之后的两个字,从“知道”两个字来推测,“知”通假于“智”,那不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智道”吗?相关内容令人遐想连篇,那么拥有“智道”的人不就是“智者”吗?
何谓佛家“知者”呢?佛家的“知者”就是“佛”。佛就是指觉悟的人。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在佛学进入中国后,发现中文中没有和梵文的“佛”相匹配意思的字,于是我们聪明的老祖宗另外特别造出来这个“佛”字。何谓佛之知见?如来藏妙真如性、般若波罗蜜多、常住佛性、诸法实相,等等,都是同一法义的不同表达方式。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见,无所不见。般若,妙智慧也,能照见一切,觉知一切,所以无所不知。《楞严经》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我们若在知见上再立一个知见,就相当于头上安头,那就是无明了。佛之知见就是佛性,如果知见上又建立我们的知见,我们的妄想意识心执着分别个不停,那就把无所不知的般若智慧给遮盖住了,假如放下分别执着妄想,般若智慧就显露出来,那就无所不知,圆满智慧显露出来。百丈禅师开示门人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弘一法师圆寂前暗示:花枝春满,天心月圆。道理如此,文字不能表达出这么多玄妙无量意,仿佛就是多余的。佛家的东西需要慢慢品,你要品,虽然不是很好理解,无关文字。
何谓道家“知者”呢?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著有《道德经》。其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老子哲学的基础与核心。这里的“道德”和我们生活中的道德不是同一个意思。老子的哲学被称之为道家哲学,就因为这“道”。“道”是一种自然法则,天地万物都起源于“道”。万事万物的背后看不见的规律和本源称为“道”,而万事万物在“道”的支配下,显现出来、得到的东西叫“德”。因此,道是内在实质,德是外在表现,道是看不见的,德是感受得到的。显而易见,道家的“知者”就是契合“道”最圆满的人,也就是最符合规律本源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就是在于这个契合度。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版《老子五千言》甲乙两本,也就是《道德经》,该版和传世版有很大的不同。1993年10月,在湖北省郭店村又出土竹质楚简版的《道德经》,此为成书最早的《道德经》版本,与帛书版内容和思想差异很大。比如楚简版中是“绝智弃辩”、“绝诈弃伪”,传世版与帛书版都否定仁义礼,提出“绝圣弃智”、“绝义弃仁”。帛书版与传世版有一句狠话,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极其容易被人曲解。楚简版无该句。楚简版应为更接近老子原版《道德经》,没有掺水,没有夹带私货。
行文到此,我们回到篇首,四十岁的“惑”,到底是什么惑?四十岁的“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情绪管控,“喜怒哀惧爱恶欲”都需要管理控制。如果不能管控好,那么“喜怒哀惧爱恶欲”每一样都是“惑”。如果管控得好,那么哪里还有惑呢?有人发牢*,没有这些情绪那还是不是一个人呢?那不就一个木头人了?对了,所以,孔夫子还要告诉我们,“知者不惑”,这不就撇除了愚痴吗?
佛家认为“贪嗔痴”就是众生所染的三种根本毒害,三毒烦恼是俱生烦恼,与生俱来,简称三毒。一个有修养的人,有学问的人,学习过圣贤之道的人,是能够控制这样的烦恼发作,不是这个烦恼没有,只是不让它随意发作,让它有限度的发作,发作的程度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有意缩小这个范围,假以时日,只要这个范围足够小,那么断了这个烦恼的人就是我们说的圣人了,这个有意缩小范围的行为就是我们说的修行,本质内容就是减少贪嗔痴。贪就是贪爱,贪恋,贪着。贪里面必然有一个“我爱”,只有“我爱”了,才会有贪。因此凡是因“我”对事物喜欢而产生了占有、追求的*都叫贪,贪着名闻利养是贪,贪着五欲六尘也是贪,贪着亲情、友情、爱情一切感情都是贪。贪是产生一切痛苦和烦恼的根本。嗔正好和贪相反,是对违逆不顺的境遇或者事情,不能忍受,产生愤怒、暴躁、嗔恨、仇视的情绪和心理,甚至损害他人。佛法常讲“火烧功德林” ,这个火就是嗔恚之火,功德指定慧,一发脾气,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定慧都烧掉了。《华严经》上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里面必然有一个“我慢”,只有“我慢”了,才会有嗔。“我慢”就是傲慢的自己。傲慢者容易发脾气,看别人不顺眼,若无傲慢,绝对没有嗔恚心。痴就是愚痴,缺乏智慧,主次不分,是非不辨,黑白不明,好坏不知。痴里面必然有一个“我疑”,只有“我疑”了,才会有痴。正因为愚痴,不明事物的真相,才产生对自以为是美好事物的妄求贪恋,求之不得,即又产生嗔恚心。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执着一个“我”,如果没有了“我”,那么何来“贪”?何来“嗔”?何来“痴”?这个“我”就是“我执”,破除“我执”,就可脱离六道轮回。仔细观察上述原文1说的就是爱和恶,全是情执所致,贪图私情,本质就是“贪”;原文2说的一时忿恚之下忘记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危,这个就是“嗔”;原文3和原文4说的都是知者不惑,说的就是不“痴”。这几句话不就是佛家极力劝戒的“贪嗔痴”吗?
你看,《论语》的这几段话不就和佛家的要点接驳上了,真的是无二无别。儒释道原本就是一家,之所以分开,那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不相同,有的人适合儒家,有的人适合佛家,有的人适合道家。凡是提起中华传统文化,就出不了“儒释道”这个范围,根只有一个,枝条有三个罢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朝成化帝朱见深登基不久,依照“虎溪三笑”之意将陶渊明、陆修静、慧远法师三人相拥一体,绘制的《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一首,构思独特而巧妙,展现和睦氛围,期望社会和平,民众团结。
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志于)立;四十而(志于)不惑;五十而(志于)知天命;六十而(志于)耳顺;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人前进的指引牌,或者说就是人生在世的修行线路图。多了“志于”两个字后,变成了开始年龄段,没有这两字时往往解读成完成年龄段。比如“四十而不惑”字面意思就是四十岁就要达到“不惑”这个境界了,“四十而(志于)不惑”的意思就是即使到了四十岁,只要知晓该收心,需要开始志力于“不惑”,只要开始,就走对路子了,不着急,这就是悟,当然这是解悟,不是证悟。这样的解读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中下根性的钝根人忽然额外多提供十年修行时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至于是不是符合老学究的义理,那不是我们的事,不管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显然,不仅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们都是修行人。我们生而为人,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不是为了贪图各种色声香味触法而来的。我们来只是为了修行,为了提高自己的心性,来这个世界就是历事练心,无他。
我不是解读《论语》的专家,我甚至不是儒学爱好者。我也不是来讲经说法的,确定无法可说。这些不是分享的分享、不是记录的记录,文字只是表面功夫,文字后面的那些才是真实的智慧,才能真实受用,否则,这些看下来,你会头痛,一个字都看不进,也看不见。假如契合了你,你又能看见无量义来,淡淡的喜悦充满你的身心。没什么,善巧而已。你到了这里就知道了,到了就知道,文字就是多余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人生只有一个四十岁,我的四十年龄段已经过去了,下回要写《五十知天命》,能让我静心修行的就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大护法。
谨以此文献给朝夕相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