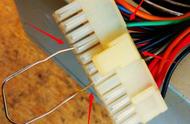作者 雷扬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杜樊川悠悠地望向深秋的峻岭,那儿群峭碧摩天,云雾绕山巅,连绵的林海中竟依稀露出深褐与火红,那不是深秋的枫树与人家的柴扉吗?诗人喜上眉梢,吟咏出这千古名句。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钟情高山流水,喜作闲云野鹤,逍遥快活于这如诗似画的山林。
陶渊明辞官重返山岭: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李白,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更惬意的还是,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

我们插队的村落,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好去处。
它,藏在林中,隐于雾里。
但,那些时日,我总以为:
它很高,很高,人们无论从哪里来,都要一步步艰难地向上攀登,直至深山更深处。我常疑心,眼前之景可为: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
它很远,很远,几近与外界隔绝,村里有长者竟然一辈子没走出那崇山峻岭,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它很静,很静,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孤寂永远如影随形。
其实,它不过是公社一个荒僻的小山村。
那年,我十七岁,花样年华,耕耘山巅,蹉跎岁月。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似乎弹指一挥间,又似乎漫漫如无尽的长夜。
知青的小家热闹过,旋即就冷清了。
恐惧、迷茫、厌弃……,说不清,道不明。总之,姐妹们陆续走了,最后,剩我独守空楼。
我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返城后,回首往事,总有一种述说的冲动。
于是,不揣浅陋动了笔。没有文思泉涌,更没有下笔成章,妙笔生花。总期期艾艾,磕磕绊绊,词不达意,言难由衷,几经修改,也颇不满意。
有时读大家经典,以为临阵磨枪,或许能略微博路人眼球,可实在多是东施效颦之举。
蒋勋说,有成见的读写,很难跳出主观臆断的藩篱。我很想较真实地再现当年的生活,但也知道自己终难摆脱情感的羁绊,看来我的愿望与实际会有一定的距离。
照说,面对古今大师,我应自惭形秽,缄默钳口,因为自己实在才疏学浅,除了平淡的经历与肤浅的感受,一无所有。可回望走过的路,曲曲弯弯,深深浅浅,脚印始终依稀可辨,不思量,自难忘,实在不愿辜负心的诉求。
于是,拉拉杂杂,拣印象最深的着笔,将近七年的知青生活表述一二,并努力照实道来。
一心只想为那默默无闻的中国闽北小山村,留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模糊影像,当然,其中隐约可见一个不谙世事,幼稚可笑的女知青的身影。
路过的看客,如能稍稍驻足观览,则是我莫大的荣幸。
离 愁---山居笔记(一)
我的离愁始于何时,已无从知晓,但印象深刻的却是那一刻。
1969年1月24日下午。我们,福州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们,徒步赶往火车站。大家三五成群,一路上乱哄哄的。天,阴沉,大家的脸也晦暗。有几次,太阳似乎想从云层里挣扎出来,但最终都失败了,好在雨没来助兴,北风劲吹,路旁的桉树时不时颤抖着。
路上、站台、车上都是人,分不清哪是出行的,哪是送行的!
“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的《兵车行》开篇描绘的场景,我不只一次地想象过,今天面对此景,正慨叹它到底不及先贤所见惨痛,火车缓缓启动,瞬间,失控的情绪,如钱塘江潮铺天盖地而来,车上车下哭喊声汹涌一片。那是久违的人间真情:不是义士远行的悲壮;是痛别亲友的凄怆!
我,没有可告别的对象,没有泪,没有思想,没有魂灵,木讷地盯着窗外缓缓移动的房屋,树木,农田……
别了,福州!不知谁在我的身后,小声地说。
顺昌县郑坊公社丰岭大队,那儿离公社仅几步之遥,分到郑坊公社插队的知青先都聚在这,美其名曰:集中整训。印象最深的是,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粗砺的糠皮加青涩的野菜。
冻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没了,萧索的木屋,深褐晦暗,石板路湿漉漉,雨中白晃晃地刺眼,闽北深冬的冷,寒彻心扉。
终于定下去向,分派我们去尚坊大队。
那,山高,路远,人少,疫病流行,没公路,没有电灯,是仅次于榜山的荒僻山村,榜山没分派女生。
不去!是仿佛抽中下下签的同学们作出的第一反应。
不行!似乎没有一点商量余地!工宣队和公社四个面办的干部态度更生冷坚决!
时乖运蹇,大家抗争,开始绝食,可,后来……女生经不住种种威逼,终于妥协。
男生最后也没顶住,但提出唯一条件:不和女生在一村!这样,尚坊七个女生,夏坊九个男生。好男儿自然不能和背叛者为伍!
告别熟悉的同学,眼馋地望着驶离村子的公社往返县城的班车,依依不舍地踏上公路边一条羊肠小道。
一路空寂,冷清,山风阵阵,无情地扫荡过茫茫芦坡;老林阴森、潮湿,古木参天,枯藤缠绕,狐臊熏人……
上坡、上坡再上坡,村民们挑着我们的行李,喘着气,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走,我们精疲力竭地紧紧相随。
近两个小时,大家登上又一道山梁时,有人叫:到了!
俯视树荫浓密的绿谷,那若隐若现立着几栋灰褐色的木屋,幢幢呈风雨飘摇的颓态。走近了,山村全景就尽收眼底: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长约百来米,路的两边,高高低低,稀稀疏疏散布着十来栋残破的木屋。
知青小木楼,在村边,两层,楼上两间,一大一小,楼下两间,一间是厨房,一架木梯上下相连,还有一间和厨房不相通,门开在外边,起先是队里堆放化肥的仓库,后来养鸭。楼上竟有一窄窄的回廊,将小楼上方的半边围住。
屋内有新制的杉木床,没上油漆。一人一张,昏暗中白生生得晃眼,大屋摆五张,小屋两张。
华和莉选了小屋。
“油灯!”大家默默地收拾,突然有人叹到。我愣了下,灯早看到了,只是当时没反应过来。“那堪独坐青灯”《柳梢青》中的诗句,蓦地冒出,又无端地想起《红楼梦》中的妙玉。如果心如古井,这儿倒是修行的好地方,我戚戚地想。
多少年过去了,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床。

(一)
不足半年,小屋的一张床空了。
华走了。
丰岭时,我们打扑克,唱样榜戏,排遣无聊与焦虑。到山村,大家偶尔也苦中作乐,华永远是主角。她文静,白白净净的脸,一副棕框的眼镜,恰如其分地衬出她略带书生气的甜美。华有极强的识谱能力,陌生的歌,她一边看曲谱,一边哼出来。样榜戏中的京剧,凡老旦、青衣、花旦、小旦、女角唱的,她都会,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她唱青衣,不仅音色纯美,还韵味十足,《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段,我常以为她唱得并不比洪雪飞逊色。那时我正迷京剧,自然和她如影随形。
山村生活开始了。
晨曦微露,我们荷锄下田。林密草深、山路坎坷,水田冰冷,烂泥没膝,栉风沐雨……生活的琐屑,也得样样面对:柴、米、菜,盐,油……第一位是砍柴,大家最惧怕,回回被异常的艰辛折磨得死去活来。近山干柴少,要往深山去,山路崎岖陡峭,迢迢上坡路,云遮雾障,到了林子,人早精疲力竭,钻入密林深处,搜寻枯枝败竹,笨拙地挥刀砍伐,好容易砍满一担柴,看看回去那九曲十八弯的前途,没有人不倒吸一口凉气,未举足,内心已瘫软。
生活之痛其实才刚刚向我们袭来。
华病退走了。
来小屋,瞥见空床,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怅惘。随后的日子,有几次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地上楼,似乎听到华美妙的歌声,虽柔声细语,却珠圆玉润,急急进屋一看,方知是错觉。古人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看来这话不假。
(二)
翠和我是同班同学,她比我略长数月,好喜欢她的为人和性格,总是那么温文尔雅,热情随和。她不高,微胖,脸略圆,大大的眼睛,弯弯的柳眉,脸上常泛着健康的红晕。
我们曾是邻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翠早早地就承担了许多家务。早上,我找她上学时,她却常刚刚买菜回来,母亲给她五角钱,让她买全家七口人一天的菜。放下菜篮,她匆匆抓起桌上一块芋头粿,背上书包,就和我一起出门。其时,她的母亲在饮食店工作。踏着长街窄巷清晨的静谧,我们说说笑笑,学校竟然很快就到了。
上学与无学可上的日子,我们总形影相随。她对我永远是长姊般的关爱与呵护。母亲被打倒,家门被封,她同情而大胆地陪我回去取衣物;明知我是“狗崽子”,却毫不顾忌地与我厮混:坦荡荡地拉着我,满大街地看大字报,钻入集会人群凑热闹,懵懵懂懂跟在医大那些革命斗士后面打杂:抄写大字报,拎浆糊桶,贴标语,发传单……
我们还一起走南闯北。67年,已是半夜凉初透的秋季,我们竟又一次来到北京,蹲守在清华大学荒僻小院一斗室中,油印传单,接听电话……9月3日半夜竟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听取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那时,我们不知已几天不曾认真梳洗,听说要见大人物,慌了神,进入会堂就急急寻觅卫生间,胡乱地将自己收拾一番,想去,我们草草修饰后的模样一定很古怪,那些大人物见到我们后惊讶的眼神即是明证。那年头,种种荒唐,样样出格,我竟毫不忧惧,因为有翠。
翠是随我跟姐姐来的,其他的人都是姐姐高二的同学。她的父亲不久亦下放在县城边上的洋口镇。他知道她的境况执意要她转过去。
要走了,我在一边看翠细细地收拾着小小的藤箱,箱子很小,装不了多少东西,她将东西拿进拿出,不知该放什么,犹犹豫豫、磨磨蹭蹭,这种箱子我也有一只,那是我们一起步行串联时在长汀买的。从入中学相识后,我们还没长时间分离过。
深秋的村口,依旧绿树掩映,竹影婆娑,我们相互道了珍重,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很快就融入无边的绿野中,人去山空,我却没有一点点离去的意愿,一味望着翠消失的方向,任由泪水朦胧了视线。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也许从此便天各一方,没有翠的日子,我不知自己会否,客愁乡梦乱如丝。
紧挨着我的那床也空了。很长时间,都觉得它空得很突兀。

(三)
尚坊五人世界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一天,莉问我,可想搬来与她同住,“空空的床,看得人心慌。”她并不看我,只愣愣地盯着那张空床说。
莉身材高挑,但不失丰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美貌精明。她很健谈,是女生中唯一读文科的,她的博闻强识让我惊讶,我想,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可到大学中文系当个教授,因为她还有很强的推理和辨析能力。和她在一起最大的快乐,就是听她讲故事,听她整首整篇地背诵古诗文。当然那都是在她心情好的时候。她给我讲福尔摩斯,高老头、唐吉柯德,甚至安娜.卡列尼娜……“那是种令人惊艳的东方美。”当莉说到安娜的相貌时,脸涨得通红,双眸也泛着光;那情景仿佛她亲眼见过这绝世美人。
寒风冷雨的晚上,熄了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柯南道尔笔下的小生番似乎就在我们门外徘徊,听莉也辗转反侧,有时,我轻轻地叫她,说出心里的恐惧,这时,她总像长者那般宽慰我,“那都是故事,何况还有我呢!”我有她,而她有谁呢?
那年初春从福州归来,莉穿了件新毛衣,殷红耀眼,宛如初夏雨后新熟的杨梅,本来就长得白白红红的她,更衬出脸颊的红润,脸上的笑容也多了。随后,莉回城的频率高了,可秋天来时,莉却病了,人懒洋洋的,无精打采,村里的人悄悄地议论,说:不会是怀孩子了吧!听他们这么说,我很为莉不平。最终,还是让她们说中了。莉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要走了,男友在城郊,家里经济条件较好。莉的体态渐渐臃肿起来,行动笨拙,她腆着肚子,为自己办理了所有调动手续,忙忙碌碌好一阵子,走时,凌乱的发丝遮掩着满脸的疲惫,苦笑中藏着似有似无释然的神情。
莉走后,我独居小屋,清晨醒来常以为她还在屋里。但掀开帐子,瞥见那空荡荡的床,才渐渐醒透,想,莉回去了,现在她可以为夫君讲故事了。
(四)
梅离去之快可称之为,迅雷不及掩耳。
“招工!”听她向我们“招供”,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她嘿嘿笑着,一脸得意,又有几分的神秘,我不知道,她怎么就有了招工名额。
提到梅,我至今难忘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梅不高,略胖,眼细小,皮肤细腻白净。每每听人说话,她总微笑着眯着眼,脸颊上现出两深深的酒窝,一旦听到可笑处,她便爽朗地开怀畅笑,笑声清脆悦耳,似秋晨空中飘来的一串银铃声,你不知不觉地沉醉了,你会觉得心胸开阔,萦绕心头的愁云惨雾消散开了,露出了瓦蓝瓦蓝的一片天。她不喜唱歌,但爱哼歌,真有些曲不离口,出工前,她常倚着楼上的栏杆,一首接一首地哼着歌,眼睛则四下张望,想早些知道当天干什么活。她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快乐的小女生。华走后,就数她能营造气氛。
那天,她倚着栏杆哼歌,我们村的拖拉机手小陈终于出现了,我们将梅送到村口,她笑得很动人:我们福州见!这是祝愿,可我觉得这祝愿邈远得迅疾随风消失在茫茫的天地间。
(五)
小屋一张空床,大屋三张空床,小楼空多了。
姐姐仍似既往,默默地辛勤劳作。她事事苛求自己,竭力而为,农活家务没有什么能难倒她!她的勤快,能干渐渐地就闻名乡里,闻名大队,闻名公社,成了模范知青的典型。善良的山里人觉得要给她的付出一个交代,于是,我们来尚坊的第五年,姐姐有了一个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推荐、考试、政审……,曙光在望时,张铁生的反潮流的试卷在报纸上登出,我的心悬了起来。是不是又要有一场革命风暴,那年头可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走白专道路被视为一种反动。终于,有消息传来,虽然姐姐考得很好,但还是被录取了,而大队有一个考试成绩出类拔萃的男生竟然名落孙山。不久,他便黯然地转往外地。
姐姐走了,我为她高兴,这是上苍的公道。

(六)
姐姐就如粗壮挺拔的一棵大树,我是偎依在她枝叶下的一株小苗。一旦大树被移走了,天空似乎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有一阵,我发现风雨变得肆无忌惮,连阳光也格外刺眼。我懵懵懂懂,举目四望,惊见姗站在山边,微笑着望向我。
楼上两屋变得各剩一主。
我和姗不久当了民办老师,不用常常下田,但我们还得为生活自给自足,还得领着学生勤工俭学。我仍像以往一样跟着不善言辞的姗上山、下田。
姗说,我砍柴吧,你种菜;大家再轮流做饭。几年来,姗总默默承担较重的活儿,从不计较。
校长魏老师很同情我们,他怜悯的举措是给姗介绍对象。他把公社医院的于医生说给了姗。姗应允了,不久他们就结婚。开始是于常到我们这儿来,后来姗*了,她就调到了公社。
姗走时也是秋天,午后,于来接身怀六甲的妻子,空气中飘散着稻谷的甜香,山林变得五彩斑斓。知青能有什么东西呢?很快他们就打点就绪,姗笑着小声对我说,我们走了。我愣愣地站在一边,含糊地应答着。
他们走后,我在小屋桌前枯坐,不知过了多久,屋内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可我眼前却清晰地现出那熟悉的山路,那是通往张坊的,通往公社的山路,珊在前,于在后,夕阳淡淡的金光,涂满姗的脸,很好看,只是有些汗涔涔,嘴角笑意微微。瘦瘦高高的于也笑着,阳光在他的眼镜上活泼地跳跃。山野,积翠如云,转瞬,空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真是一幅美丽的夫妻晚归图。
我一味让遐思腾云驾雾,远处有一两声犬吠,孤零零的,天地间显得那样的空旷,大得万事万物没了踪影。
那晚,我没有做饭,在人去楼空的两屋走了走,木然地抚摸着六张空床。
夜好静!
后来阿黄来了,那是只不知谁家走失的小狗;再后来,民教莹来了,她也是福州知青,先前在别的大队插队,她年龄和我相仿;住在大队部。我一直以为,莹是我在尚坊上苍赐予我最好的礼物之一,她热情、开朗,活泼、宽容。和她相处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自在。
离去,离去……多少年一直是我的朝思暮想。

(七)
1975年,来山村第七个年头的夏末,我真要离开尚坊了,但不知怎么竟心如止水:感觉似火车到站,小船抵岸,弃车船,下站台,登码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淡。
回望空空的屋,空空的七张床,不由地又想到来时的情景,众姊妹青春洋溢的脸与黯淡的神情。要走了,行装很轻,前几日让几位走得近的农民朋友,将我这他们需要的东西拿走,其实,除了几本书,我还能有什么,已然身无长物。
莹没来送,前一天晚上她就对我说了。是啊,为什么要送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送别对身处异乡的人只能徒增悲凉!
别了,生活七载的山村,第一批来尚坊插队的知青,都走了,来时何其热闹,走时,形单影只,虽有人相送,可内心的孤寂却难以言表。想想夏坊的炎,他将成为山村,乃至全大队一中知青孤独的山村守望者。当然,队里还有后来的,别校知青。我背负着他们的人情债走了,无论如何,他们把上学的机遇让给了我,今生我该如何偿还?我能偿还吗?还有已上调公社的修,几年来如兄长一般的呵护,我连谢谢都很少对他说。那天他们又都聚到县城为我送行。
其时,我真希望自己孑然一身,悄然离去,只需心中暗暗地和顺昌和艰辛的过往道一声别。
火车开动了,站台上的身影模糊了。同样是别,现下冷冷清清……我不由打了个寒颤,窗外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远了,淡了。
我虔诚地祈祷:无私的队友们,愿你们早日还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