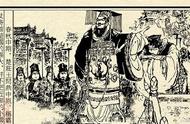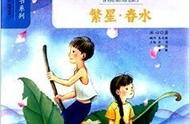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于城濮之战重创楚军,阻挡了楚国蚕食中原的步伐,并且获得了霸主的地位。在之后的数十年里,逐渐形成晋攻楚守的争霸形式。前613年,楚庄王继位,面对晋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他只得哀叹说:“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大夫们看到君王如此愁苦,也相争说:“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楚庄王大受感动,他声泪俱下地起身拜谢众大夫。从此之后,楚国上下励精图治,日益强大起来。
此时的晋国虽然经历了灵公的虐政,但在正卿赵盾的治理下,依然强盛无比。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洛阳,使人入周问九鼎之轻重,震慑得郑国请服。同年,晋成公继位,晋师伐郑,郑国又倒向晋国一边;夏季,楚庄王也领兵伐郑,这让郑国苦不堪言。两年之后,楚军再次入侵郑国,晋军便通过讨伐陈国来警告楚国。前600年,晋成公会盟诸侯于扈,陈国畏惧楚国,不敢去会盟。于是晋成公命郤缺率师伐陈,楚庄王也相应地领兵伐郑,最终晋郑联军在柳棼之地击溃了楚师。郑国之人皆欢喜雀跃,只有子良忧心忡忡地说:“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

春秋之时的“晋楚争霸”
楚国再度伐郑,晋军徘徊不进前599年,晋成公离世,其子晋景公刚继位,郑国又倒向楚国,为此晋国率诸侯之师伐郑。楚庄王再次引兵来攻,晋将士会将楚师驱逐到颍北之地。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楚人感到很沮丧,但楚庄王不肯就此罢手,第二年春季,趁晋军退去之时,楚军再次进攻郑国。此时的郑国人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原来晋楚两国都把郑国当做进行角力的缓冲带,双方为了避免直接大战,就通过讨伐郑州来间接争雄。于是,子良向郑国人建议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于是不肯坚守以待晋援,而是直接臣服于楚国,以此来迫使晋军直接与楚军较量。
谁知晋国正忙于讨伐北方的狄人,未能兼顾南方的战事。于是“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这个小国为了避免兵乱之苦,便极力挑起两个大国之间的争端。前597年春季,楚庄王再次围攻郑国,郑人通过卜筮来决定是否要坚守,结果显示为投降不吉利,于是郑国一边求援于晋国,一边坚守不出。
晋国人接到消息后,迟迟未发兵。晋景公才刚为父亲守完丧,国事初定,又得卷入南面的战事,显得力不从心。一直拖延到六月份,晋景公才命荀林父将中军,先毂佐之;士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前去救援郑国。晋军才刚抵达黄河,郑国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
原来,郑人已经坚守了三个月,迟迟不见援军,在穷困之下,郑襄公只好肉袒牵羊,出城去向楚庄王投降。楚庄王宽宏大量,亲自释放了郑襄公,并且下令退军七里。左右之人都劝阻说:“得国无赦”,请求兼并郑国。但楚庄王不同意,依然同意了郑国人议和的请求,复其社稷。

楚庄王问鼎中原
晋军犹豫不决,楚军也无意作战在听闻楚庄王不肯灭亡郑国之后,晋国上军主将士会赞许说:“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他认为如今楚国人理直而壮,晋军驰援已晚,既然郑楚已经签订合约,那么就没必要继续前进了,不如“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整军而还,以待将来。
谁知中军佐将先毂却不同意,他认为晋国之所以称霸于天下,靠的是武力。如今不能救郑,是为不力;不能攻楚,是为不武,他声称“由我失霸,不如死。”认为出兵救援,却因听闻敌国强大而撤退,这是一种胆怯的行为,会令晋国丢掉面子。于是先毂擅自率领中军渡过了黄河。
韩厥看到先毂已经渡河,便对主帅荀林父说:假如先毂战败,那么您作为主帅,罪过就大了。一来不能战胜制敌,二来不能约束下属,与其如此,还不如挥师挺进,即使战败了,也是大家集体的责任,而不会把罪责全归给主帅。荀林父见势已如此,只得下令进军。他的弟弟荀首知道后,感到很担心,《周易》里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先毂违反军律,荀林父非但不能约束他,反而还跟着他一起渡河挺进,违反了《周易》中的作战原则,“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楚国人正准备罢军归国,忽然听闻晋军已经渡过了黄河,十分震恐。楚庄王想避开晋军,取道回国,伍参却坚决主站;令尹孙叔敖也不想打,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则嘲笑说:“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在晋军,可得食乎?”孙叔敖依然决定回国,令军士皆南辕反旆。伍参见状,急忙向楚庄王分析形势,他说:荀林父才刚被任命为主将,未能行令;先毂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晋军的上层指挥官都是各自为政,众人皆无所适从,故而逢战必败。况且楚庄王是君,荀林父是臣,“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庄王被他说动,急令孙叔敖回辕返辙,严阵以待。眼看晋军将至,众将都请求应战,子重则劝阻说:“晋,大国也,王师淹病矣,君请勿许也。”楚庄王却回答说:
“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
认为欺软怕硬并不是霸主的行事风格,不如先驻扎在此,看看晋军的动静如何。

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郑人挑拨离间,大战最终爆发晋军驻扎在敖地,并未主动出击;郑国人皇戌使入晋军,对晋国人说:“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
先毂听罢,认为战机已经来了,既然郑国人肯合作,那么“败楚服郑,于此在矣”,请求荀林父应允。栾书引狐偃的名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楚国伐郑,郑服而舍之,如今楚军将要回国,晋军救援不及,却还要挑起战争,这是楚直晋曲,不可谓老。其次,郑国的重臣子良已经作为人质进入楚国,可见郑楚已经亲密有加,郑国人的算盘在于“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因此不要答应郑国人。赵氏家族里,赵括、赵同袒护先毂,赵朔则认为应该听从栾书的建议。
两军对峙一段时间后,楚国派使者来对晋人说此行只是为了让郑国臣服,“岂敢求罪于晋”,并劝晋人罢兵回国,以免战祸。晋将士会也客气地说:“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侯人”,表示出友好的态度。双方的大部分人都很克制,极力想避免战争。谁知先毂却使赵括更改士会的回信,说晋军就是要来把楚军从郑国驱逐出去的,挑衅意味很重。
楚庄王又派人来跟晋军议和,晋人许之,谁知和谈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于是楚国将领许伯等就前去向晋人挑战,砍其军旗,夺其良马。晋将魏锜、赵旃也请求出去挑战,主帅不许,于是他们又请求当使者,得到了允许。士会担忧地说:“二憾往矣,弗备必败”,认为这两人是坚决的主战派,此去不是出使的而是去挑战的,应当预先做好战斗的准备,先毂却不答应。
魏锜、赵旃抵达楚军营帐之后,果然发起了偷袭,不料被楚人发觉。楚将潘党追*魏锜,楚庄王也驱逐赵旃,晋人害怕二将被擒,便出兵救援;楚人则担心庄王陷入敌阵,于是也集体出动,大战就这样突然爆发了。孙叔敖见状,立即号令三军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于是楚人趁晋人还在犹豫之际,就直接主动出击、*奔而来。晋军面对忽然爆发的战争,显得手足无措,前有敌人追*,后有黄河拦阻,主将荀林父“不知所为”,只得击鼓于军中,说:“先济者有赏”,于是晋国两军皆乱,中军与下军互相争夺船只渡河逃命,船中尽是被砍落的手指。楚庄王见状,感叹说:“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于是主动撤退,让晋人渡河。
士会见晋军阵脚大乱,失了章法,认为一旦应战肯定会全军覆没,于是他带领上军退出了战场,众军见状也纷纷败退。到了黄昏之时,楚军驻扎在邲,晋军依然在争相渡河,到了半夜之时还能听到渡河之声。
惨败而归之后,荀林父向晋景公请死,晋景公鉴于楚成王*子玉的教训,故而赦免了他。到了第二年晋景公才追究先毂的罪责,族灭其家。

战斗忽然打响,令晋人惊慌失措
《春秋》为什么褒扬楚国而讽刺晋国?邲之战后的第二天,楚人打扫战场,潘党建议收晋军尸体筑成京观,以此来向后代炫耀武功。楚庄王则说:“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认为武功的内涵在于禁暴、偃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以及丰财,而不是单纯地*戮与掠夺。楚国虽然打了胜仗,然而庄王却说:“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况且晋国只是战败,并未灭亡,如果把晋人的尸骨堆成土山来夸耀武力,那么以后两国之间仇恨日深,将永无和平之日了。
在《春秋繁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议论:有人问董仲舒说《春秋》内诸夏而外蛮夷,楚是夷狄之国,可是在邲之战时,《春秋》、《左传》却都侧面强调楚直而晋曲,这是为何?董仲舒回答说《春秋》无通辞,在这场战争中,“晋变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蛮夷华夏不是简单的地理、血统、民族概念,还需要兼顾道义。
楚庄王伐郑而舍之,有可贵之美;晋人不及时援救盟友,假装出兵又徘徊不进,待郑国力屈而降之后,为了保住面子又主动挑起战端,“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所以《春秋》并不因蛮夷华夏之见而掩饰晋国在道义上的短处,通过“移其辞以从其事”来谴责晋人身为华夏之人却行夷狄之事,深为后世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