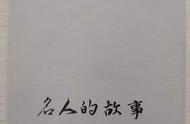一、是借物抒情,更是托物言志
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的名作《落花生》虽篇幅短小,且显得平淡无奇,就是围绕着全家人一起种花生、尝花生等过程,借物喻人,谈了一番做人的道理。但因其娓娓道来的口吻,那种“豪华落尽见其真”的朴实清新风格,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成为入选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
晚近的2019年版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上册依然选入此名篇,把它和名家郭沫若的《白鹭》、琦君的《桂花雨》和冯骥才的《珍珠鸟》安排在一起,组成了第一单元。在单元导语中,提出的阅读总要求是“初步了解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而在《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建议”中,又提出“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语句,认识落花生的特点,明白父亲借助落花生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初步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等。这样的要求,细细玩味会令人感到困惑。

语文课文里《落花生》一篇的插画
因为其所谓的“做人的道理”是偏于一种理性的认识,而“了解”“方法”云云,虽然也同样可以纳入到认识的范畴,但是“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却更接近于感性的体验,两者之间似乎难于达到真正的自洽。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教材编者或者“教学用书”的撰写者似乎没有自觉意识到,《落花生》这一篇,虽然也写到了具体的物,但跟其它三篇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要在“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单元目标中整合起来,其实是比较生硬的。也因为此,有教师提出,把《白鹭》《桂花雨》和《珍珠鸟》三篇归入“借物抒情”,而把《落花生》这篇独立出来归入“托物言志”(朱小云《从“做人的道理”突围——<落花生>一课教学新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如果对借物抒情作进一步细分,究竟是抒情主人公在看到物之前已经有了一份情感,所以只不过是借助一种客观存在的对应物来抒情,还是情感本身主要是被客观之物所感发,这里不是我所要讨论的。这里要讨论的是,就《落花生》来说,如果将之归入“托物言志”以强调其中的说理性质,那么“言志”本身,虽然也有学者将之与“载道”并列,把它等同于抒情,但我更认同于“言志”与“缘情”可以区分开的说法。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教师教学用书》中,提供了许地山儿子周苓仲的一个说法是值得重视的。他说:“《落花生》是我父亲写的散文,文中那些孩子是我父亲那一辈,是我父亲讲他父亲那一辈的事,而且是虚构的。”一方面说这是散文,一方面又说这是“虚构的”,那么,把《落花生》作为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托物言志的寓言性故事来看待,大概也不会太令人惊讶的吧。
当然,“托物言志”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们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所托之“物”如何和“言志”联系的,换言之,这种思维推进的桥梁是什么?这就把我们的理解推进到由《诗经》开启的传统“比兴”手法了。具体到《落花生》来说,这是把落花生这样的物,与特定的某种人加以跨类式比较,是以物喻人,然后再进一步表达了要做这样的人的志向。换言之,从“托物”推进到“言志”,是以“喻人”为思维演进的中间环节。不过,这里的以物喻人,作为一类修辞手法,还是有一点特殊性,我们下文来讨论。
二、比兴中的就近取比
一般认为,比喻的目的是通过用一个熟悉的类别之物或人去理解或者指称一个相对陌生的类别之物或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经验来理解或称述外在的、异己的事物,不少词语的构成,就积淀着拟人的含义,比如用人的头部“顶”来表示物体的上部,用人的眼来表示物体的洞与孔等。尽管在今天,眼依然作为人眼被普遍使用,但如果说针眼时,其小孔的含义已经固定下来,我们不会再认为说这词语的人在使用比喻。即便当初有使用比喻的意图在,这种比喻,也已经被人称为是死掉的比喻。但比喻虽然“死掉”,作为一个表达的重要原则还在使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贴近自己的“就近取比”。这个“近”,是空间、时间上的,也是心理、情感上的。比如李白的名篇《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人说,这首诗著名是因为汪伦踏歌送别的方式,与众不同,却又深得李白之心,把它写出来,成就了千古名篇。也有人说,是因为李白就在桃花潭与汪伦告别,这样拿眼前深深的潭水,来比喻汪伦送别的深厚情谊,把不可捉摸的抽象的情感,用眼前景来表达,其直观和生动,正是就近取比的灵活运用,且不落任何斧凿痕迹。如果用这样的原则来看《落花生》中的描写,那么当作者着重写“父亲”的两段对话,所谓:
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其把花生的生长状态和特点比喻为人的“不好看”而“很有用”,正是在就近取比了。因为花生就在大家面前被食用,也是“我们几个姐弟”一起栽种的,是“母亲”把它做成了几样食品,提议放在花生园里作为收获节来一起品尝。以花生为喻体,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来说都是贴近作者的感受,是再典型不过的“就近取比”。

落花生
不过,比喻往往是取喻体和本体的一点来维系,在文中,当这一点经由苹果和石榴来加以衬托后延伸出做人的道理时,也会给学生带来一些困惑。他们可能会提出疑问道:“难道苹果和石榴就没有用吗?”话当然不能这么说。苹果和石榴当然也有用,但是相比于苹果和石榴让人易生爱慕心,埋在地下的落花生容易被人忽视,才得出了“我”紧跟着父亲的话而有的一段结论,也是该文的卒章显志: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当然,这种为人志向的提出,还只是一个方面。
细细推敲下来,我在文章开头区分“借物抒情”和“托物言志”时,其实是把作为思想意义的“志”与情感作了区分,但这样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必须承认,情感的因素是无法从文章中完全清除出去的。作者借落花生来比喻一种朴实有用之人时,其实是跟内心喜欢落花生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就近取比”的近,也是情感的接近。这样说来,作者对落花生本来就有喜爱之情,才乐意托这个物来言志,或者说,借物抒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托物言志的情感推动力。说明了这一点,教材对原文开头一段的修改,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
三、教材删改的得与失
语文教材对选入的名家名篇,出于学情、课程和语言规范等要求,都有或多或少的删改。编者对这种删改当然可以提出种种理据,但也会因为改动不当留下一些遗憾。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这里还是以原文第一段为例,做一点深入的分析。
先看教材中的课文: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2019年版2023年第5次重印)
而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许地山选集》,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家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种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①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②
两相对照,改动还是比较大的,我先以表格形式列出大致比较的内容,然后评析。

先看改动的合理性。
把“几个小丫头”删除,可能是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时期,官宦人家都会有仆从丫头,涉及到社会阶层的不平等问题,向小学生解释可能要费一些周折,因为不影响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的理解,所以干脆删除了。还有,原文直到交代开辟荒地种花生时,才提到“园”,是所谓“辟来种花生园”,但“种”与“花生园”搭配,表达就缠夹不清。课文把“屋后”改为“后园”,是强调先有园,再从园中开出荒地种花生,这样不必再提“园”,表达就比较顺畅。另外,把“隙地”改为“空地”,把“荒芜着”改为“荒着”,把“辟来”改为“开辟出来”,把“动土”改为“翻地”,等等,表达也更通俗,是适合于小学生阅读的。
改动的不合理也依然存在,甚至可说是一种败笔,就是把 “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当然“底”字应该用更规范的“的”来替换)一组排比,改为“买种,翻地,播种,浇水”,看似交代完整,把原文所缺的“播种”的环节也补上了,而且都是两字句,显得节奏紧凑,却忽略了,作者写这一内容,固然是交代大家参与的种花生的行动,但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参与过程中的一种兴奋的态度,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喜欢。所以写时间意义上贯穿前后的行为,就远不如表现大家也能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在分工合作式的忙碌中体现出的兴奋劲头。正是有这种喜欢、兴奋的劲头,所以作者在写大家“都很喜欢”后面,是用破折号来把这种喜欢进一步展开出来,说明出来。但是课文既然把这种表达“喜欢”的句式改变成劳动流程的概述,所以与此相应,就把“都很喜欢”改成“都很高兴”,把破折号也改成了逗号,把强调种花生的前因“既然”也删除了,其自身的逻辑倒是自洽的,但是那种满溢于文字的欢喜劲,却被一次次弱化了。这种弱化情感的逻辑贯彻得那么彻底,最终也是以句号,替换了原文首段结尾具有情感力度的惊叹号。
然而,段落内部的貌似逻辑自洽,却是以造成更大范围的逻辑不自洽为代价的。
我们看到,课后的练习设计是,首先要求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课文围绕‘落花生’写了哪些内容”,其次要求学生思考:“从课文中的对话可以看出花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父亲想借花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这样的设计本身,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是让学生用代入的方式,通过切身感受的比喻来体会一种做人的道理。而分角色朗读,正是共情代入切身体会的很好方式。但导致的总体结果却又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一方面,课文的整体单元目标,提出“初步了解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但另一方面,课文把第一段原文中能够充分抒发情感的文字和标点,多处删改以削弱作者渲染的感情力度;既然弱化了情感表达的力度,却又在课后练习设计中,要求分角色朗读以引导学生进入共情体验。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难道编者真的是想把原文表达的情感弱化后,再让学生来体会、来把握借物抒情的方法吗?还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原文的有些删改是对情感表达的一种弱化?反正如此处理,还真是让人读出了一点反讽的意味。当然,笔者的上述种种见解,也很可能有自己没意识到的缺憾,还请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