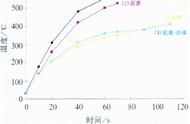致中和
文/冯友兰
“致中和”三个字出于《中庸》。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宋明道学中,这几句《中庸》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程明道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圣人的心,如明镜,如止水,是廓然大公的。因为它是廓然大公的,所以亦无所偏倚,无所偏倚谓之中。因为它无所偏倚,所以遇到事物,当喜即喜、当怒即怒、当哀即哀、当乐即乐。此即所谓发而皆中节,此即谓之和。
朱子说:“喜怒哀乐,各有攸当,方其未发,浑然在中,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及其发而皆得其当,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所谓中的意义,是无所偏倚,不是无过不及。已发的喜怒哀乐,可有过或不及,而此所谓中,是“未发”,所以不但无过不及,且亦无无过不及可说。未发已发,后亦成为宋明道学家所常用的名词。他们又常引《易·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语。圣人的心,未发时如明镜止水,是“寂然不动”;已发时,喜怒哀乐,各得其当,是“感而遂通”。
以上是宋明道学家对于《中庸》里中和二字的解释。我们于此篇所说的中和,与宋明道学家所说者不同,或与《中庸》所说者亦不尽同,不过我们于此篇所说的中和,确是中国思想中两个重要的观念。
和与同不同。《国语·郑语》引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以他平他谓之和”,如以咸味加酸味,即另得一味。酸为咸之“他”,咸为酸之“他”,以“他”平“他”,即能另得一味,此所谓“和实生物”。咸与咸是同,若以咸味加咸味,则所得仍是咸味。此所谓“以同裨同”, “同则不继”也。推之,若只一种声音,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音乐。若只一种颜色,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文采。必以其“他”济之,方能有成。
《左传》昭公二十年引齐侯问晏子云:“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此又提出过、不及二观念。不同的原素,合在一起,可以另成一物。但合成此物之不同的原素,必须各恰如其分量,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若太多或太少,则即不能成为此物。不太多,不太少,即是无过不及。无过不及即是中。所以说和必须兼说中。此所说或不是晏子的本意,但说和必须兼说中,这是一定的。
以上所说,可以说是有现在所谓辩证法的意思。甲的“他”是非甲。甲与非甲合,能成为乙。此可以说是相反相成,由矛盾到统一。成为乙之甲与非甲,必各恰如其分量,不多不少。甲或非甲,若有一太少,则不成为乙,若有一太多,亦不能成为乙。甲及非甲的量变,可以造成其所成的物的质变。此可以说是由量变到质变。
一个人生理的、心理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各方面底要求,都要于相当程度内得到满足,然后一个人才能保持一个健全的身体、健全的人格。有许多生理的或心理的疾病,都是由于人的某方面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太被压抑所致。这是我们所都知道的。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怎样算是“于相当程度内得到满足”呢?怎样的满足,算是在相当程度内?又怎样的满足,算是超过相当的程度呢?
一种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的满足,若达到一种程度,以至与别种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发生冲突,此即是此种要求的满足超过相当程度。超过相当程度,即是太过。若此种要求的满足,尚未达到此程度,而即受压抑,或此种要求,根本即未得任何满足,此即是此种要求的满足未达到相当程度。未达到相当程度,即是不及。此种要求的满足,若到一恰好的程度,既不与别种要求冲突,亦不受不必要的压抑,无太过亦无不及,则其满足即是得中,即是中节。
例如,对于有些人,喝酒是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在普通的情形中,一个人喝酒,若至一种程度,以致其身体的健康,大受妨碍,则其喝酒即为太过。若其喝酒,有一定的限度,并不妨碍其身体的健康,而却因别种关系(例如美国政府行禁酒律之类),而不喝酒,则其喝酒的要求,即受到不必要的压抑。如此则其喝酒的要求的满足,即是不及。此所谓不必要,是对于此人的本身说;此所谓不及,亦是对于此人的本身说。喝酒的过或不及,本都是因人而异的。若一个人喝酒,只喝到恰好的程度,既不妨碍他的身体健康,亦不使其喝酒的要求受不必要的压抑,则其满足即是得中,即是中节。
若一个人各方面生理的及心理的要求,都是这样中节,都各得到相当的满足,而又都各不相冲突,这种状态,即谓之和。一个人在生理方面,若得到和,则即可有一健康的身体;在心理方面,若得到和,则即可有一健全的人格。旧日谓人有病,为“身体违和”。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都可以说一个和。这和中有许多不同的原素。这些原素,在其适当的分量下,是“相成”的。但若一过了适当的分量,则即“相反”了。若其相反,则和即没有了。例如在普通情形下,一个人一顿吃三碗饭,是有益于他的健康的,但若他一顿吃十碗饭,则不但不能有益于他的健康,而且有害于他的健康了。饭的增加,对于他的健康说,是由量变到质变。各种要求的满足,在恰好处是中,不到恰好处,或超过恰好处,是过或不及。这其间亦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情形。
或可问:本书曾说尊理性,岂非教人使理性压抑其他各方面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于此我们说;理性的功用,并不是压抑其他各方面的生理的底、心理的要求,而是指导,或节制那些要求,使其满足,无过不及。我们说,有道德的理性,有理智的理性。先就理智的理性说,其功用是如上所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要喝酒,到哪里去喝酒,用什么方法去买酒,这都是要靠理性的指导。喝多少不至于妨害身体、妨害事业,这亦要靠理性的节制。如果一个人喝十杯酒,可以得到快乐,而不至于妨害身体,妨害事业,理性对于这种满足,只有赞助,决不禁止。所以孔夫子亦说;“唯酒无量,不及乱。”我们于以上说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的冲突,只是就一个人的本身说。
就社会方面说,一个人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亦可以与别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相冲突。道德的规律,对于人的要求,制定一个界限,使人与人不相冲突。就这一方面说,则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合乎此界限者,是合乎中,是中节;其超乎此界限者,是太过;不及此界限者,是不及。
《诗序》有几句话,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是就人各方面的生理的、心理的底要求说,“止乎礼义”是就道德的规律说。发乎情是人之性,止乎礼义是社会的制裁。社会中的人,每人都应该完全如此行。所谓道德的理性的功用,即在于使人知道这些界限,使人的各方面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都合乎这方面的中。一个社会中人的各方面生理的、心理的要求,如皆合乎这方面的中,则这个社会,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社会,亦可以说是一个和。在这一方面,各人的各方面生理的、心理的要求,亦有相反相成,由量变到质变的情形。
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的满足,在其本身看,是合乎中者,但在社会方面看,不一定是合乎中,而或者是太过,或者是不及。如其是太过,则社会必须制裁之,其个人的道德的理性,亦应制裁之。因此,常有些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受到压抑。这压抑,就这些人的本身方面看,是不必要的。但在社会方面看,则是必要的。这一点常引起许多思想上的混乱。有些人常把这两方面的必要或不必要弄混,以为在一方面是必要或不必要者,在其他方面,亦是必要或不必要。这“以为”是完全错误的。
例如一个人的所谓领袖欲特别强,但他的才能,都很不配当领袖。就他本身方面看,他的这欲若得不到相当的满足,他或者要疯。在其个人方面看,他的领袖欲的相当满足是合乎中,但在社会方面看,他的领袖欲的相当满足是太过。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只能向他说:你的才能,不能当领袖,你若因不能当领袖而疯,我们只好把你送入疯人院。社会的这种办法,我们不能说它有什么错误。
在社会方面看,“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的要求,是应该制裁的。这种要求,宋明道学家谓之欲,或私欲,或人欲。他们说欲是恶的。这是一定不错的,因为所谓欲者,照定义是超过道德的规律的要求,照定义它即是恶的。所以说欲是恶,实等于说,凡是不道德的即是不道德的。但后来反道学的人,如戴东原等常说,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是不可,亦不应该压抑的,而宋明道学家却专爱压抑之。所以宋明道学家是“以理*人”,太不讲人道。这种辩论,不是误解了宋明道学家所谓欲的意义,即是陷入上所说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于以上说中和,是就一个人的本身说,或是就一个社会中的各个人对于社会及别个人的关系说。若就一个社会中的各种人对于社会及别种人的关系说,则亦有中和可说。此所说社会中的各种人,指社会中的各种职业的人说。例如当学校教员的人、做生意的人,等等,皆此所谓各种人。
旧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各行的人,即此所谓各种人。此各种人中,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的权利及职分,及对于别种人的权利及职分。在普通的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社会中的各种人亦是如此。他们对于要权利总易偏于太过;对于尽职分,总易偏于不及。此所谓过或不及,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各种人要他们的权利,有一个界限,过了这界限即与社会中的别种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或妨碍。这个限度,即是中,合乎这个限度的,即是得中,即是中节,超乎这个限度的,即是太过。
每种人尽他们的职分,亦有一个界限,如不到这个界限,则即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这一种事的需要。这个限度即是中,合乎这个限度的即是得中,即是中节,不及这个限度的,即是不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各种人,要权利、尽职分,皆合乎中,则此社会,即得到和。一个社会,不是只一种人所能组织成的,它需要许多种不同的人,它需要“异”。这些异,就其是异说,是“相反”。但它们都合在一起,方能组织成社会。就其合在一起说,是“相成”。它们的相成,靠它们的要权利、尽职分,都合乎中,以构成一个和。
或可说:这一种说法,是社会上统治阶级所用以压制被压迫阶级者。照资本家的说法,资本阶级及劳工阶级,都是社会,至少是社会的经济方面所必需的。这两个阶级,应该互相帮助,而不应互相仇视。从前亚里士多德,对于希腊的奴隶制度,亦有类此辩护。他说:有些人是天生只能做工具的,有些人是天生能用工具的。能用工具的做主人,只能做工具的做奴隶,这是最合乎天然的。在中国,孟子对于当时的贵族政治,亦有类此的辩论。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照这个“通义”推下去,则社会中有一类的人永远是“治于人”而“食人”者,有一类的人永远是“治人”而“食于人”者。前者是被统治阶级,后者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永远用这一套理论,麻醉被统治者,使他们于被统治外,还要心悦诚服地赞颂统治者的圣德神功。现在我们讲这一套理论,恐怕对于统治阶级,有“助纣为虐”的嫌疑。
于此我们说,我们所谓各种人,并不是指阶级说。在有阶级的社会制度里,其政治的或经济的制度,使有些人,子子孙孙都在某阶级里,使又有些人,子子孙孙都在另一阶级里。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世代是奴隶,主人世代是主人。在贵族政治里,平民世代是平民,贵族世代是贵族。即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在政治法律方面看,对于劳工之成为资本家,固然没有限制,但在经济方面看,则劳工之成为资本家,若不是完全的不可能,亦是仅次于不可能。一个人当了劳工,他子孙还是当劳工的机会,不是百分之百亦是百分之九十九。但我们于上文所说,社会上的各种人,则不是如此。一个人如已当了三十年的教员,大概他不大容易改行。但是他的儿子则是可以随便入别的什么行。对于一个社会说,这些各种人必须有。一个社会必须这些各种人构成。这些各种人,要权利、尽职分,都必须合乎中,以得到和。任何社会都多少是如此,都应该完全如此,不管一个社会是什么种的社会。有阶级的社会是如此,无阶级的社会亦是如此。
因为中和的道理是通用于任何的社会,所以有阶级的社会亦引用它以维持其阶级制度。但这引用是错误的。因照这个道理,社会所必需要的是各种人,而不是各阶级。一个社会之是有阶级的社会,是客观的“势”所决定。在此种势下,有些种人,固必须成为某阶级,但如此种势已去,一个社会可以成为无阶级的社会时,而为某阶级之某种人,仍欲维持其阶级,则此种人所要之权利,即是太过,不合乎中。他们要权利太过,超过了中,则不但不能得到和,而且有害于和。
例如执掌政权的人,本亦是社会上的一种人。但在某种“势”下,这种人成了世袭的,因此即成了一种阶级。在这种势下,这种制度,是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但如此种势已去,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世袭的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而在此阶级里的人,仍要维持他们的权利,则他们的要权利即为太过。社会中的别种人,对于他们的太过的要求,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制裁。这种制裁,如果是以暴力出之,即所谓革命。照以上所说,我们可知,我们于此篇所说的道理,不能为所谓统治阶级所引用,以麻醉被统治的阶级。事实上确有人如此的引用,但如此的引用是错误的。
“致中和”应用在政治社会哲学方面,即是民治主义。《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一个民治主义的社会里,人的生活,即有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说;“此民治主义之所以为大也。”在民治主义的社会里,在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的范围里,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的自由。这个范围的界限,即是我们于上文所说中的界限。不到这个界限者谓之不及,超过这个界限者谓之太过,合乎这个界限者谓之得中,谓之中节。就社会中的各种人说,亦是如此。社会中各个人,及各种人,行为俱中节,则社会即是一大和。大和即是旧说所谓太和。这种社会所宝贵的是异而不是同。合许多中节的异,以成一大和。这个大和,是社会的理想境界。人类的社会,是向着这个理想改进的。
还有所谓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如果国际主义成功了,则各民族的特色,必定都不能存在。这“以为”是错误的。如果真正的国际主义成功了,在所谓大同世界中,各民族的异,不但依旧存在,而且大家还要特别尊重其存在。在所谓大同世界中,各个人的异、各民族的异都存在,而且大家都还特别尊重其存在。不过这许多的异,都是中节的异。合这许多中节的异,以成一大和。这大和即所谓大同世界。
大同并不是同,而是所谓太和。这已是一很高的境界了。但于此境界之上,还有宋明道学家所谓“万物各得其所”或“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境界。此境界亦是一太和。不过此太和不仅包括所有的人,而且包括所有的物。物得其所是幸福的。例如一人有快乐幸福,我们说他是“得其所哉”。这是“得其所”的确切意义。万物“各”得“其”所,“各”字“其”字表示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和而不同”的意思。这种境界,是“致中和”的极则。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本文摘自《冯友兰随笔:理想人生》,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