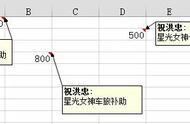秋天的怀念
作者:雪樱
1
秋日的午后,我漫步在交校路上,阳光很软,风也很轻,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路两旁的健身器材上,有人在打盹,有人在甩腿,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偶尔有汽车疾驰而过,也不会影响到眼前的静谧,美好得叫人几分忧伤。
每一座城市,都有几条以大学命名的街道,比如,“山大路”“济大路”“山师东路”,等等。交校路因山东交通学院﹙前身是济南汽车机械学校﹚而得名,虽不起眼,却历史渊源深厚。它与学校同年出生,至今已经走过66年。听老人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从八里桥延伸到交校路,得益于校友的回报。“交—校—路”,每当来了快递或有人问起,我都会用标准的济普话说:“交通的‘交’,学校的‘校’,是交通学院所在的这条路。”每一次重复,就要翻动一次过往,使我在心里产生轻微的隔阂感和厌弃感:是这条路被时代淡忘了,还是它垂垂老去了?

每年秋天开学,是这条路上最热闹的时候。送孩子的大军浩浩荡荡,很是壮观。上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手扛肩提,拎着蛇皮袋子,慢慢地,“黄面的”、“红夏利”、桑塔纳、捷达车,再到今天的私家车、网约车,新生报到的细微场景,映照出时代变迁的生动缩影。报到那几日,沉寂一个暑假的交校路变得喧闹起来,便民商店、小吃摊位、水果店、打印店、修鞋的、换锁配钥匙的,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不时有学生接二连三进出,买生活用品,或出去逛逛,他们对周围充满好奇,打量着这个离象牙塔最近的小世界。
我出生在家属大院,上幼儿园、小学、初中,交校路都是必经之路,它见证着我从懵懂孩童到少先队员、从共青团员再到青年党员的成长之路。这条路就像一条射线,把我从这里发射出去,去追求梦想与爱情,去经历生老病痛,去看整个大千世界。走过三十七年的道路,我最放不下的还是这里,如福克纳说的“邮票大小的地方”。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我仍然眷念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和踏过这街道的灵魂。”我最眷念的也是这条街道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2
记得小时候,交校路没有现在的宽敞,学校校门正对着家属大院。后来参观校史馆时,我有幸看到最老校门的照片,大门为苏式风格,上方的红五角星格外耀眼,见证着那个年代的苦难与辉煌。放学后书包往传达室一扔,我和小伙伴就钻进校园里玩个痛快。那时候,路两旁有两家手推车商亭,卖日用百货,也能打公用电话。到了周末,街上有卖气球的、套圈游戏的、捏泥人的、卖小鸡的,还有爆爆米花的,那种最古老的小推车,带有化肥袋子,附近的居民从家里用瓷碗端着玉米或大米来排队加工,四周围满了孩子,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用双手捂紧耳朵。伴随“嘭”的一声巨响,孩子们松开手一拥而上,上前捧一把热乎乎的爆米花,如雪白,似奶香,吧唧吧唧吃得香甜,连撒在地上的爆米花也都被捡起来。

除了一所大学,这条路上还有一所小学、一所职专,因此,人来车往,熙攘热闹,高峰时段经常堵成一锅粥。我上小学时,校门口路西,有个摆地摊的高个男,他是泰安人,卖旧书,也租书、租碟,他话很少,有些结巴,但书很全,吸引不少师生,还有农民工。几年前,有位毕业留校工作的男老师,他跟我说起,当年读书时在校门口地摊上,有本英汉词典一块五角钱,他没舍得买,事后很是后悔,也许就是这家书摊。
路东有个卖百货的姑娘,她浓眉大眼,待人热情,哪个同学没带钱,也敢赊给你冰棍、零食、粘画。百货摊与旧书摊对着,每有城管来撵,姑娘都帮着高个男打圆场,他满脸羞怯,不知怎样感谢。时间久了,街上的人热心牵线,他们恋爱了,很快结婚生子,摊位也合二为一,主营百货,也修车、配锁。
就像他们的爱情,日久生情,水到渠成,交校路上的故事,也是如此,缓慢如水,静水流深。记忆最深刻的是,冬天的晚上,下了晚自习,学生结伴蜂拥而出,百货摊、烤地瓜、糖葫芦,忙得热火朝天。汽灯高高悬挂,照得街上一片亮堂,这边称花生、瓜子、山楂条,那边买橘子、苹果、香蕉,老板娘裹着军大衣,略显臃肿,她脸上的冻疮,却暴露无遗,让人想到张爱玲笔下“碎牛肉的颜色”。称重、装袋、找零,最后伸进布袋里,抓上两把花生,道一声:“好吃再来!”对方回应:“谢谢老板!”糖葫芦是现做现卖,油锅里的糖浆“嗞啦嗞啦”响着,摊贩动作娴熟,边熬糖边张罗生意,很多学生都围着等候,有说有笑的;刚出炉的烤地瓜,热气腾腾,有些人接过来就捧着吃起来,“哧哈哧哈”,瓜瓤金黄,烫嘴香甜。
烤地瓜的香气、糖葫芦的甜味、各种的果香,杂糅在一起,和着学生们的欢笑声,顷刻投入到漆黑如墨的夜色中,转眼间,没了踪影,只有高空中几颗星星无声地东张西望。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小女孩从家里蹦跳着跑出来,头戴“兔子耳朵”的毛线帽子,身着红色棉袄,去街上百货摊前买大大泡泡糖,或是干脆面,或是花生糖,然后在街上与小伙伴玩耍,玩够了才回家。
那个小女孩,正是我。

多年后,我读到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和“呼愁”,既感慨,又迷茫。他写道:“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有洋气的东西。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帕慕克苦苦探寻“呼愁”的意义,他的追寻之路,何尝不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情感联结和灵魂共振呢?我转而问自己,如果说交校路是我的“后街”,那么我的“呼愁”以什么形式呈现呢?
后来,学校校门改在东面,这条路上的日常也随之发生变化。取缔摊贩,规范秩序,然而,到了晚上,路两旁的小吃摊依然人气十足,麻辣烫、白吉馍、拉面、过桥米线、臭豆腐、炒米饭、菜煎饼,以至于蔓延到了对面胡同里的大排档;喝醉酒的丑态、过生日的嗨唱、情侣间的恩爱、聚餐后的放纵……都在这条路上演绎出别样的色彩,霓虹灯下,那些歇斯底里,那些爱恨情仇,也都被它一一接纳。
2005年,学校主校区迁至长清大学城,留下部分学院。这条路变得黯然失色,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改造提升,文化墙粉刷一新,健身器材一应俱全,便民市场开门营业,让摊贩不再打游击,但是,有些东西终究是回不来了。当街道空间被打上“文明”的烙印,失去的比拥有的要多得多。
3
这个秋天,我穿过交校路,去学校理发。秋阳从高处兜洒,打在树梢上、行人的脸上、整洁的路面上。路南的女修鞋匠,正在埋头走线,机器发出“哒哒哒”的声响,使我不禁想到过去,那位头发花白、戴眼镜的老修鞋匠,连外国人也竖大拇指的修鞋匠,是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不远处的交通书店,因为是周末,没有开门。梧桐树荫下有位老伯,他坐在马扎上闭目养神,台阶上的收音机响着,传出刘兰芳说评书的浑厚嗓音。只见他一手托着敞着盖儿的茶杯,香气袅袅,听得入了迷。是啊,他就像是一尊佛,时光打这里经过,停滞不前,令人久久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