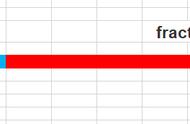落神台上,司命星君拱手施礼,说道:“不知道神女对小老儿的安排可还满意?”
由于这次是最后一世,他特地来给我送行。
我点了点头,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七苦倒是都尝了一遍。
“难为你了。这一世又是什么故事?”
“神女在人间的最后一世尤为重要,遵照天规,小老儿无权编写此次的命书,一切全凭天命。”
“天命?”我喃喃道。脑海中忽然闪过阿澈的影子。
天界和冥界不同,无需喝孟婆汤,跳下落神台下凡到人间,会自动失去在天界的记忆,之后又会带着人间前世的记忆回来,依次累积。
这十一世里,我们拥有各自的人生,基本没有交集,我却似乎隐隐见过他几面。
虽然是我让司命星君把我们分开,但当回首前世想到和他擦身而过那几瞬,我难免感慨,竟有几分惦念。
不知道经历这么多,他变得如何了,心智更为成熟了吗?
在我为长公主的那一世里,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缠绵病榻,因此未能婚配,蒙一个红衣术士赠药才彻底痊愈。不久父皇驾崩,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摄政生涯。
我疑心那红衣术士就是赤严,但没有证据。
不知以后在人间还有没有机会遇到他。
罢了,既来之则安之。
我毫不犹豫,跳下了落神台。
并不晓得身后的司命星君抬头看了看漫天的璀璨星河,长长地叹了口气。
(二)

第十二世的我,是个侠女,名叫清铃。
我住在青城山上,和青城派比邻而居。与他们这样上百号人的大派相比,我们在武林中颇不起眼,很多人都不知道青城山上居然还有一个叫素心门的破落小派。
我无父无母,是被师父在山林里捡回来的。
师父说,我从小就爱笑,笑声清脆如银铃,因此起了这么个名字。
师父名叫尘静,她身体不好,到后来说句话都要咳嗽半天,所以我的武功也学得七零八落,连青城派的小弟子也打不过。
后来师父死了,素心门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年我十六岁。
师父临终前,把一本破烂不堪的书递给我,说这是素心门的独门功法,让我以后自己修习。
我看着书上的油污和墨迹,欲哭无泪。
师父说,女子行走江湖太危险,从小就让我女扮男装。渐渐地,我时常忘了自己是个女子,习惯了一直以男子自居。

我安葬了师父之后,决定离开青城山,去外面闯一闯。因为这里四周都是比我功夫好的青城弟子,每日遭他们白眼欺负,实在太憋屈了。
说不定外面有什么出路,万一机缘巧合能学到真正的厉害功夫也未可知。
我拿着师父留下的三两银子两串铜钱,揣着素心功法,收拾了几件旧衣服,打了个小包裹就出了山,一路走进了容城。
容城很大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路边小贩们吆喝个不停。师父早年带我来过两回,差点迷路。
要在这里生存,光靠那几两银子是不够的。我想着自己除了有点三脚猫功夫身无长物,寻思能做点什么呢。
要不卖艺?
我刚在一棵大槐树底下找到一块空地,还没站稳,哗啦啦来了一个杂技班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一顿布置就表演起来。
他们卖力演了半天,又是胸口碎大石,又是钻火圈,又是叠罗汉,又是口吞利刃……才收到十几个铜钱。
当收钱的盘子递到我跟前,我丢下一串铜钱,落荒而逃。
看来,卖艺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天色已晚,我的肚子开始打鼓,在街头看到一家名为富贵楼的小酒馆,便走了进去,点了两个包子,一碗面条。
隔壁桌坐着几个中年汉子,正在兴致勃勃谈论武林中最近发生的事。几个月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位神秘的白衣剑客,他武功高强,到处找人比武单挑,已经连续打败了十八个门派。并且刚刚向青城派下了战书,不日就将到来。
“时间就定在七日后的九月初五,到时咱们也去看看热闹!”
“李大哥,这位白衣剑客叫什么名字啊?”
“他自称白衣。”
“白衣?”我心想,这么随意一听就是假名字,不过师父说高人都爱如此行事。这人武功如此厉害,我要能拜他为师就好了。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结账时我发现,银子不见了。
一定是刚才街上人多被人偷了。估计在我掏铜钱的时候,就被贼盯上了。
店小二才不管我是不是遭了贼,非说我吃霸王餐,找来掌柜,对我不依不饶要送官。
我无奈只能和掌柜说:“要不我在你们这里免费干几天活,抵了饭钱?”
掌柜双手叉腰跳了起来:“呸!你想得美!你在这里干活才几个钱,我们还要管吃管住,晦气的赔钱货!”
我忽然想起我有个长处,师父说我烧鱼很好吃,于是我赶紧自告奋勇,除了端茶倒水我还能给店里贡献一道招牌菜。掌柜半信半疑,勉强同意让我试试。
我把烧好的一盘鱼端上来让掌柜品尝,忽然一双筷子伸过来,夹走了一块鱼肉。
“这鱼味道不错,你来给我做厨子吧。”
(三)

说这话的人大约二十多岁,一袭白衣,长身玉立,俊逸出尘,笑意吟吟,眉眼尽显不羁。
我想起刚才酒客们的话。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白衣剑客?
白衣男子道:“我这几天住在容城,这位小兄弟既然缺钱,来给我做几天仆从如何?专门负责打扫做饭即可。”
他豪气地拿出一锭沉甸甸的银子递给掌柜:“这是小兄弟的饭钱,不用找了”。
掌柜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乐得合不拢口,满口道谢。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白衣男子出了富贵楼。不知道为什么,我本能地觉得他对我没有恶意。
“适才多谢恩人相助,敢问恩人尊姓大名?”
他哈哈笑了起来,眼中带着几分促狭:”我叫白衣。刚到容城不久,饮食着实不惯。你烧的鱼很好吃,请你做我几天仆从,我付你酬劳,大家两不相欠。”
我把名字改了一下,告诉他我叫青岭。
他住在附近的悦来客栈,客栈里有厨房,客人可以自己买菜做饭。
“店里只有一间房了,我们都是男子,委屈你和我同住如何?”
我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我想,既然我是仆从,到了晚上我睡地上好了。
不知他从哪里抱来一床棉被铺在地上,然后对我说:“这房间床铺太软,我睡着很不舒服。这几晚你睡床,我睡地上。”
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男子同屋,我多少有点惴惴不安。但白衣却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他酣睡的面庞上,如一块洁白的美玉。
我暗想:他长得可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