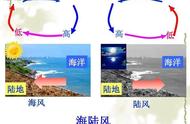在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中,生于高原长于高原的作家杨志军,以有力笔触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接续奋斗的历程,以诗性的语言、宏阔的视角,描绘了青藏高原上汉藏两个家庭相濡以沫的交融,彰显了藏族牧民生活样貌的变迁,以及青藏高原由传统走向现代沧桑巨变的恢宏画卷。


▲《雪山大地》 资料图片
领 读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首次发表于《中国作家》2022年第11期,2023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讲述了以父亲、母亲为主体的三代人建设和献身青海牧区、汉藏融为一家的故事。
1
小说以“我”为视角,父亲和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放弃了在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先后来到艰苦的青海牧区工作,为牧区的教育卫生事业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
父亲的一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难曲折、悲壮辉煌相伴而行。1950年代,作为科长的父亲到沁多草原蹲点、了解牧区情况时,被当地极有威望的原部落头人角巴赋予了一个藏族名字——强巴,强巴是角巴阿爸和爷爷的名字,从此父亲不仅拥有了一个尊贵的藏族名字,也逐渐和这里的群众建立了血浓于水、生死与共的情感。
在一次突发的草原大洪水中,牧人桑杰的妻子赛毛为了救父亲被洪水冲走。父亲蹲点结束时,带走了桑杰家聋哑却聪慧的儿子才让,将他带去西宁交给姥姥、姥爷、母亲照顾,并给他治病。此后升任沁多县副县长的父亲因承担瘟牛肉一事的责任被撤职,在重新选择工作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当学校校长。彼时,沁多草原不仅没有学校,牧人们也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父亲历经千辛万苦,骑马走遍了整个沁多草原,在角巴的帮助下成立了草原上的第一所小学和中学,为青海牧区培养了第一批藏族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成为了建设牧区的中坚力量。
在困难时期,沁多草原不仅接纳了迁来的西宁保育院,还在“文革”中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文革”中被撤职的父亲用牧区的牛羊肉换建材帮助牧区建立麻风病医院,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改革开放后,父亲先是创办了沁多贸易公司,后来为了日益荒芜、沙化的草原生态恢复,出任书中的阿尼玛卿州州长,建立沁多城,在雪山大地的注视下走完了为牧区奉献的一生。
母亲本是西宁大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但为了草原,她放弃舒适的生活,与父亲一起,建立了沁多第一家医院,又到生别离山里建起麻风病医疗所,最终因被传染麻风病而殉职。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又串联起姥姥、姥爷在西宁城里与沁多牧区孩子们亲如一家的故事。年轻一代的“我”、梅朵先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来到牧区,才让在美国读完博士后也选择回到了草原,为沁多城的建设呕心沥血、英年早逝。
而在父亲和母亲为牧区奉献一生的故事中,角巴这个草原人民尊敬爱戴的老人,成为他们在牧区扎根的重要依托和扶助者。角巴的妻子姜毛在上世纪60年代一直在照顾保育院的孤儿,新年终于能回家团聚,却在返程途中失去了音信,被狼群袭击而去世。为了帮助父亲办学校,角巴献出自己家的帐房,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父亲的工作,最后为了说服生态恶化的草原牧民搬到城市,在翻越雪山时,陷入了深不见底的雪渊,“被雪山大地收走了”。桑杰这个曾经的草原流浪孤儿是沁多草原的另一个领头人,也始终支持着父亲的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经商所得的全部积蓄。这些人物与主角共同构成雪山大地奉献者群像,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也艰难地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
2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代洪流中,父亲创办沁多学校、成立沁多贸易公司,母亲创办沁多县医院和麻风病医疗所,成为小说中最具华彩的章节。父亲和母亲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情怀的梦想的实现,离不开草原人民的支持与帮助,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辉煌篇章。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家庭和角巴、桑杰一家,和许多沁多学校毕业的孩子们也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是什么把汉藏融为一家?是什么使大家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在小说中,作者深情地写到:“如何才能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藏汉混搭的家,真是说不清楚啦。它有感情、习俗、婚姻、血液的交融,还有声气呼吸的交融,而一切交融都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向善而生。”
是的,“向善而生”,但此“善”并非仅指向个体的“美”与“善”,而是 “大美”“大爱”与“大善”:是人与人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浓于水;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对这片土地的挚爱;是父亲与母亲这些“外来者”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是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正是这些“大爱”与“大善”,铸就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图景与未来蓝图。
从青海牧区到省城西宁,三代人的故事贯穿起从草原到城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姥姥、姥爷以爱温暖着来自牧区的孩子,他们在西宁的家成为了每一个来自沁多草原的孩子的“家”;父亲母亲一代人以他们一生的努力和坚守,在广袤的草原上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草原之城——沁多城;“我”和梅朵、才让一代仍然在建设和守护着这座城市;而更年轻的一代继续谱写新的篇章。从沁多草原到沁多城,从一片荒芜的处女地到一座美丽的现代城市,从日渐荒芜、退化的草原到草原生态的恢复,这是青海牧区艰难曲折的发展历史,也是新中国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的复兴之路的缩影。
3
《雪山大地》也是一部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话题有关的著作。在小说中,父亲和一匹名为日尕的骏马的故事荡气回肠。日尕精通人性、骁勇刚毅,在它的身上几乎囊括了一匹骏马、一个知己、一个英雄的品格。它跟随父亲大半生,从沁多草原到阿尼玛卿州、到省城西宁,驰骋奔走,最后以传奇的方式消失,带领群马离开沁多草原,一起成就了恢复草原生态的梦想。人与动物、人与草原的关系,其实也是人与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人们信仰的雪山大地,不仅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家园,更被赋予了神性的守护意义。
在雪山大地的注视下,人们虔诚地信仰着“爱”与“善”,也传递着“爱”与“善”——来到城市的牧民依然坚持“为所有人祈福,自己的幸福才会到来”的信仰;医术高明的藏医来到生别离山,和母亲一行共同为麻风病的治疗献计献策;父亲、角巴为雪山大地下的牧民们奔走一生,最后在纯洁、伟岸的雪山大地中安息。
正如父亲自己编写、带着学生们齐声朗诵的诗句:“我生地球,仰观宇宙,大地为母,苍天为父,悠悠远古,漫漫前路,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山河俊秀,处处温柔,四海五洲,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爱爱相守”,才能“家国无忧”。因此,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在这个意义上,既是一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叙事,也是一部汉藏一家亲的感人奋斗史。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人故事
按下时代背影的“快门”
向上滑动阅览
谈及《雪山大地》的创作初衷,杨志军坦言,他最初想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一户汉族人和草原牧民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相濡以沫的交往。“但一动笔就发现,这不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父亲作为一位从洛阳来到西安读书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西宁,在一家马车店里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当时还在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报名上了第一*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后来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在那些年月里,年年都有“西进”的人,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建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个公司、第一处定居点、第一座城镇。“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演绎成荒丘的生命,并在多少年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在《雪山大地》里,作者更多探索的是人性的美和善良。“我想展示,人是怎么样才能叫做‘人’。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去生活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群体、一整代人都在那样生活。对于善、美的人格刻画,我觉得我写得还远远不够,我所写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1995年,杨志军因工作从青海调往山东青岛,并定居于此。此后,大陆性文化与海洋性文化共同交织于杨志军的创作之中,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风貌。
“这些年,我的写作往往是交叉着写,一会写写青藏高原,一会写写青岛的海洋。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40年,这是我的第一故乡;我在青岛生活了28年,今后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是我的第二故乡。从某种意义上,我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对故乡的皈依,我深深眷恋着故乡的一草一木。”
杨志军最怀念那种骑着马在草原奔跑,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亲密无间并不完全是家人之间的,甚至是与每个不认识的牧民。杨志军说,《雪山大地》是向时代背影按下的“快门” ,“如果我不按下这个‘快门’,可能连这张‘照片’也没有了。但我毕竟还可以用文学创作来复现从前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文字的魅力,让历史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
(本报综合报道)
静读思悟
献给高原建设者的赞歌
向上滑动阅览
合上书页,我想高呼扎西德勒,想去草原策马奔腾,到牧民家品尝盛满爱的酥油茶和糌粑,更对“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有了深刻理解。
《雪山大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献给高原建设者的赞歌。
怎样去用生命践行一个知识分子在高原的使命?作者杨志军在书中给出了答案。是父亲公而忘私、为民请命、两袖清风,是母亲一身风骨、仁心仁术、悬壶济世。他们心怀悲悯,打破隔阂;他们信念坚定,矢志不渝。诚如书中所言:“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点亮你,熄灭你,一辈子追随你,这还不够,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所有后代。”年轻一代的才让、江洋、央金、梅朵,继承父辈的事业,赓续父辈的基因,甘愿将青春挥洒在祖国需要的地方,造福千秋万代。
“爱与太阳跟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从人心的蓝白红绿黄上流过,风唱着扎西德勒从爱的空间流过”……我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的巧妙设计,每一章以一首诗歌作为题记,像是永不失联的爱的宣言,又或是诚心竭力的天地祈愿。它们表面看似脱节,内里却踏着爱的天梯飞跃而上,彰显着人们心中永不放弃的爱念。
沁多草原的美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小说中埋藏的一条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故事脉络,真实反映了父辈与牧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进程。翻阅书页,所呈现的理想主义的豪情与现实主义的激情裹挟着我,去观赏一望无垠的生命原野。
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永远是时代的命题,我庆幸并自豪有那么多像书中人物一般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探索着、奋斗着。这也激励着我。
(余思媛)
“雪山” 精神传万代
向上滑动阅览
溪河在雪山下流淌,夕阳为草原披上纱衣,这是一片令作家杨志军魂牵梦萦的土地,不论是成群的牛羊、巍峨的雪山,还是尚善尚美的牧人,都紧紧牵动他的心。即使已在山东安居乐业,他也会每年都到青海住一段日子,守望这片哺育他身体、滋养他灵魂的神圣高原。
《雪山大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品,这是一部歌颂青藏高原的壮丽史诗,更是一部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在青藏高原出生并长大的杨志军,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原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
父亲强巴是第一代草原建设者,和所有怀揣理想踏足偏远地区的干部一样,心怀祖国建设伟业,成为“难得消停的人”,一生在高原默默奋斗耕耘。作为外科医生的母亲,在父亲的协助下,建立起沁多县医院,深入麻风病人居住地,开展麻风病治疗,创建麻风病医疗所,不幸被感染后,仍然坚持为麻风病人治疗,最后不幸去世。
回望父亲、母亲那一代建设者,他们的人生之路是筚路蓝缕的无怨无悔,不图名利的诚意诚心。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时代的巨变、命运的起伏,足证改革之路的艰辛和曲折。然而,父母的选择将人生意义与家国理想、道德责任和理想激情紧密相连,展现了先行者群体的伟大品质。在父辈感召下,才让、江洋、梅朵等一代新人经历了“激情燃烧的成长岁月”,自觉成为继承者。父辈这代人的历史贡献,满足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为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绘制了蓝图远景,也扎紧了祖祖辈辈绵延流传的精神纽带。
好的作品从不片面地看待一个点,它会往各个方向发芽生枝。《雪山大地》中不只有令人赞颂的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更包含作者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
(刘雪)
“三交”的心灵旅程
向上滑动阅览
翻开小说,我跟着父亲走进了牧民桑杰家。父亲如同初入田野调查的学者,一开始桑杰一家要搬迁时拒绝了父亲的帮忙,表面上看是因为客套,实则因为父亲是汉族,与桑杰的习惯和信仰都存在差异。然而,父亲学着牧人的样子向阿尼玛卿雪山磕头后,立马就拉近了与桑杰一家的距离。因为父亲知道,遵循当地人的习俗、尊重他们的信仰才能更快地融入当地。然而,他的这次“蹲点调查”却是一辈子。正如小说中沁多县委*王石所说,“命换命就是这样,有人快快地给,有人慢慢地给,一给就是一辈子”。
母亲也和父亲一样,为了沁多草原上的牧民过上幸福生活,他们不断地尝试,从建学校到建医院,从离开家到离开家人,从献出时间到献出生命,他们的每一次想法与实践都牵动着草原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头牛乃至每一根草。父亲和母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边疆建设者的缩影。父亲、母亲是这样,沁多公社主任角巴和他的妻子姜毛是这样,新一代藏族儿女才让也是这样,把一生献给了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
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不仅全景式展现了高原牧区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变迁,也让全文中各处细节彼此照应。依托作者的亲身经历,这些话语如融化的雪水,自然又纯粹地流淌在我们眼前。在这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交融。
小说以“我”为视角,作为“移民”二代,以孩子这样一个当地人的视角来书写,使得书中写到民族交融的时候非常自然。“‘江洋’就‘江洋’吧,藏族人喜欢的自然我也喜欢。从此,在我的课本和作业本的封皮上,‘洋洋’便被涂改成了‘江洋’。”在牧人的扎西德勒之中,“我”爱上他们的洒脱与豪迈,爱上他们的朴实与知足,也爱上了他们为我取的名字,因为“江洋”寓意着江河海洋,在这样的称呼里,暗含了当地群众对父亲的敬重。
在作者杨志军的笔下,藏族聚居区不再是一种想象和传奇,他同样写出当地群众对现代化的渴望。当父亲不断给藏族人民带来新的生产技术,修建公路,建立起现代金融、商贸体系时,当母亲带来医术为当地群众驱除疫病,建起麻风病医疗所时,当地牧民慢慢适应了这些变化,并发自内心地认同了他们。
我相信,《雪山大地》不仅能带领读者在高原牧区完成一趟心灵旅程,也能用草原上的故事,用牧民们的经历,给我们带来启发——过去父亲和“我”在草原上学到的,今天我们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中,同样可以切身体会到。
(张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