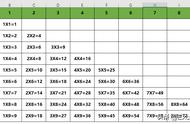《齐物三说》之说天籁
《齐物论》开头即以南郭子綦和颜成子游的对话,引出“天籁”之说。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天籁”到底指什么?据目之所见,大概有四种说法。
其一,认为“天籁”指风,以司马彪、宣颖、王先谦为代表。这种意见比较正统,历代学者形容道体,经常以流动多变之物为喻,比如以水为喻就很常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就有人以为是孔子在形容道体,孟子同样也有用水作喻的文字,那么以风作喻也未尝不可。司马彪曰:“吹万者,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这里没有明确说天籁指风,但天气一说,与风无异。宣颖则进一步点出“风”,他说:“待风鸣者地籁也,而风之使窍鸣者即天籁也。”待风鸣者应为众窍,故而众窍即是地籁,这种看法是从子游的回答“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推出的,认为比竹是人籁,众窍是地籁,那么风就是天籁。而王先谦更是直言:“要风所吹万不同,而使之鸣者仍使其自止,众声之鸣不能无所待,怒者其谁,使人言下自领,下文所谓真君也。”王先谦能点出“使”与“无所待”二义,本来应该于大旨是有所会意的,但念头一差,谬以千里,刘咸炘先生批评说:“王氏之风、窍之相待,乃又别指一物为主,则更出乎其所谓天籁者之外,尤为支误,众声固皆有待,止是彼此互待,非有别一主者。”
其二,认为“天籁”非别有他物,仍在“人籁”“地籁”中,但解说之辞往往迷离惝恍,难以捉摸,以郭象等为代表。郭象曰:“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即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抛开有无之说不论,郭象以“自然”释“天”,极具妙理,同时也避免了指实为“风”的胶柱鼓瑟之病。郭象之说虽别有理致,但可惜的是,没有贴合《庄子》文本进行阐述,灵光一现,皮骨分离。
其三,这种说法以郭象之说为基础,但能稍稍贴合《庄子》文本进行阐述,以刘咸炘为代表。刘咸炘说:“盖所谓天籁者,即众窍比竹之所以然,不可知者也。地籁由众窍与风而成,人籁由人生与比竹而成,彼我相会,乃成声,缺一不可。若谓声生于窍,则无风虽有窍无声,若谓声生于风,则无窍虽有风无声,是相待也。风非为窍而有,窍非为风而有,是不相待也。相待止相会耳,相待则彼此皆不为主,唯一之主使者谁邪?不相待则各自成,然其所以成风与窍,谁造之?为何而造?未有风,窍止是无,无又何能造何能使邪?相会则谁使之会?为何而会?是皆不可知,故谓之自然。”这种看法是在郭象“自然”思想的基础之上,能联系上文《逍遥游》“无待”之旨,指出物之相待而成,没有“造”之者,没有“使”之者,皆其自成。刘咸炘先生指出的“地籁由众窍与风而成,人籁由人生与比竹而成,彼我相会,乃成声”,是理解“天籁”的极为关键的一环。
其四,认为天籁指人的言语,以刘武为代表。刘武说:“心动而为情,情宣于口而为言,天籁也。”
现在,笔者将在刘咸炘先生所论的基础之上,再紧密贴合《庄子》文本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点出“丧其耦”之意,其耦既丧,其独乃出,能独方能成其大,此层意思与《逍遥游》无待、无己之意遥为呼应。
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颜成子游之问,过去人多有忽略,仅得槁木死灰之意,不能深致,钟泰先生指出“如”字,杨立华教授指出“使”字,最当注意。此问关系后文子綦之答,子綦在肯定其“不亦善乎,而问之也”的同时,又批评其“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那么颜成子游之问,哪里是值得肯定的?哪里又是需要批评的呢?这是我们在细读文章时不得不返回来审视子游之问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此意在《庄子》一书中屡次出现,而且都持肯定态度,是庄生大旨所在,比如钟泰先生指出:“《达生篇》言佝偻者之承蜩,曰:“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此形如槁木之解也。《应帝王篇》言神巫季咸之相壶子,壶子示之以地文,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死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此心如死灰之解。”另外,《大宗师篇》所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更是与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意合若符节。颜成子游能见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境,自然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子游之问的不足在哪里?应该就是杨立华先生指出的“使”字,在子游之问,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境是有另外的存在“使”之而到的,这不合“自然”之旨,故而在子綦回答“敢问天籁”时,就指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里的“使”字是和子游之问里的“使”字是遥相呼应的,“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自已自取都是自,没有其他使之,以“怒者其谁邪”反问,使其言下自领“自然”之意,这里的“怒”字其实就是“使”的意思。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既善子游之问,又指出其有不足,引出人籁、地籁和天籁,注意两个“不闻”,子游复问,文章逐层推进。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段文字辨别三籁,而以地籁为详,人籁一点而过,天籁以反问出之,使人自领其意,因此,对地籁的准确把握是理解天籁的基础。“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这句过于简略,误人甚深,如上述司马彪、宣颖、王先谦等的第一类理解都是煞定此句,把地籁与众窍,人籁与比竹等同起来。很明显的是,在子綦对地籁的描述里,除了众窍,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只有风与众窍相待,方能成地籁,地籁不能离开风与众窍而存在,所以司马彪、宣颖、王先谦等人把地籁等同于众窍,而把风独立出来,指其为天籁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刘咸炘的以“相待”之意为基础的解说就比较符合情理。以此类推,地籁是地噫之风与众窍相待而成,人籁是人吹之气与比竹相待而成,那么什么是“籁”呢?“籁”的本质又是什么?问到这里,笔者认为“天籁”就是指籁的本质,着一“天”字加以区别修饰,而不是在“人籁”“地籁”之外,别有一种籁称为“天籁”,也就是郭象所说的“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风亦为气,比竹亦是窍,籁就是气与窍相待而成,而其本质又不是气与窍。因此,在探索籁的本质这一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悖论,要探索籁的本质必需决去气与窍的相待,可是决去了气与窍的相待,籁亦不存,无从探起。子綦在描述地籁时有两句话值得措意,一为“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一为“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里的“翏翏”“调调”“刁刁”三语,旧说皆不甚细,如《释文》:“翏翏,长风声。”郭象云:“调调、刁刁,皆动摇貌。”而“翏翏”前加一“独不闻”,“调调”“刁刁”前加一“独不见”,那就说明这些状态是极为细微的,常人不易觉察的,故而“翏翏”当为细微之声,“调调”“刁刁”当为细微之貌,释德清说“翏翏,长风初起之声也”、 “调调、刁刁,乃草木摇动之余也”,此意得之。另外,“独不闻” “独不见”二语也与子綦批评子游“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中的两个“不闻”遥相呼应,因此在地籁的描写中插入“独不闻” “独不见”,其指向正是在天籁。如此一来,探究籁的本质过程中的悖论就可以相对顺利解决,有所待则非本质,无所待则籁亦不存,不得已而言之,只能在众籁初作之时将消之际,约略见之,即文中所谓翏翏、调调、刁刁也,此三者皆细微之貌。翏翏者,初作之时也,调调刁刁者,将消之际也。在子綦完成了对三籁的阐述之后,文章便逐层推进到言“天”。下文的“天钧”、“天府”、“天倪”便是由“天籁”之天推演而来,所以,对“天籁”这一概念的阐述,是以籁见天,籁只是一个转手,而“天籁”本身又不可说,故而详说地籁,这是文章的脉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