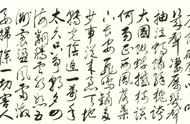他是赫赫有名的少年将军,自十二岁起跟随父亲浴血沙场,在金戈铁马的铿锵铮鸣声里,麻木了血流成河的凄惨与悲烈。
他唯独从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救下了他。
那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拥有一双狼一样狠厉的眸子,带着充满野性的恨意盯着他。
他亲自为他洗净一身血污,小心翼翼地帮他处理伤口,上药换药。
少年趁他弯腰时,用偷偷磨尖的竹筷猛的刺进他的胸膛。他的手一抖,撕裂了少年未愈的伤疤。
他蹙着眉头,为他仔细包扎好了伤口,方才,捂着胸口慢慢走出营帐。
少年开始高烧昏迷,他不分昼夜呵护照料。
有副将来报,这少年乃是匈奴一个将领的儿子,他父亲就在那次战役,倒在了他的银枪之下。
他淡淡地说,“知道了”,拧毛巾的手仍未停下。
副将急的直打转,“你这是养虎为患!况且被他人知晓了,恐怕是通敌大罪。”
他继续低头用白酒为少年擦拭着滚烫的心口。
他将少年带回府里,“从今天起,忘记你的匈奴名字,我叫子非,你叫子鱼。”
少年恨声道,“我也会记得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淡然一笑。
他亲自教他习剑学文,排兵布阵,礼仪教化。
少年闻鸡起舞,悬梁刺股,就因为他曾说过,君子报仇,也要坦荡,光明磊落。
许是少年适应了中原的水土,脱去了原有的野性,丹唇凤眸,竟然比那女子都风流妖娆几分。
他不断地给他惹祸,他拧着眉头无奈地望着逐渐长成的少年叹息摇头,目光里的宠溺温柔地荡漾,波光鳞鳞。
少年嘟着亮晶晶的红唇,挑衅地回瞪他,“就是不让你好过!”
他爽朗地笑,微敞的领口里,玉润的锁骨迤逦起伏,名叫子鱼的少年贪婪地盯着他的胸口,艰难地吞咽下口水,败的一塌糊涂。
将军子非有不少的倾慕者,经常会寻不同的理由登门,少年子鱼变着花样地捉弄那些大家闺秀,令她们狼狈而逃。
丞相亲自登门为子非说媒,他扮做勾栏女子,妖妖娆娆地登上丞相府,堵在大门口,哀哀啼哭,痛诉丞相喜新厌旧,欠了嫖资,还让她怀了骨肉。一时,丞相府门口被人群围的水泄不通。
少年也一战成名,京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寻常百姓,都知道了将军府里藏了一位绝色尤物。
有好男风者向子非将军重金讨要,反被子非一顿拳脚,打肿了嘴脸。
闹到金銮殿上,子鱼的恶迹也被重提,二人皆被杖责,军棍五十,皮开肉绽。
老夫人恼恨少年惹下祸端,又气又急,一拐杖狠狠地打下去,“子非对你掏心掏肺,你便是这般一再连累他?!”
少年趴在床上,不发一言。
“你只看到子非*了你的至亲,你可知道其中缘由?”一时间,老夫人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其实,你父亲并非匈奴人,他是我子家忠仆。化了姓名潜进匈奴内部,向外传递消息情报。首领怀疑有内奸,特意伪造了假情报泄露出来,引诱子非父亲陷入包围,全军覆没。然后软禁了包括你母亲在内的几个可疑将领家属。你父亲为了打消首领怀疑,救下你母亲,沙场上自愿死在子非枪下,暗里将你托付给了子非。谁料你母亲刚烈,竟也跟了去了。纵然我子家欠了你情,也该还清了。”
子鱼仍是默不做声。
夜半里,却悄然离开了子府。
他失魂落魄地费力挪动脚步,茫然四顾,竟不知何去何从。
直至朝阳初升,他站在城门口,留恋地回头,才发现,数年来,那个从马蹄下救出自己性命的少年将军,早已成为了遮风避雨的参天大树,自己就是那攀附的藤。
马蹄声疾,他闹市策马狂奔而至,马鞍上他的鲜血淋漓。
他委屈地扑进他的怀里,“我以后再也没有家了。”
将军子非紧紧地拥住他,“放心,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我依然会把你珍藏在心里。”
他揪起他的袖子狠狠地擦着鼻涕,“其实,我爹临走那天就告诉我,让我以后要听你的话,虽然我不知道内情,但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害你。”他无奈地看了一眼惨不忍睹的衣袖,“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算你害我,我甘之如贻。”

“可是,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赖在你身边的理由,不能无理取闹地赶走喜欢你的女人。”
子非轻拍他的背,哑然失笑,“你想要理由,其实只要一个就够了。”
他低头靠近子鱼的耳边,轻声呢喃,“我爱你。”
「完」
「一入腐门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