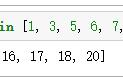作者:谭健
王兆军的长篇小说《蚂蚱》自去年问世以来,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视角,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各类专家的注目。有评论说,它通过描绘20世纪上半叶鲁南地区乡村生活图景,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多元;是对村庄的抢救式书写,写尽了人性的善恶和生命的挣扎;堪称形象的民俗志和地方志,是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这些评论各具灼见,但“语已尽焉,心犹未足”,窃以为这还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蚂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是最早有意识地清晰地揭示中国乡村社会底层逻辑和生存智慧的一部力作。

《蚂蚱》 王兆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丰厚或增益,而在于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涉笔或浅尝辄止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度,以乡村社会、农民为社会背景的长篇小说,现当代也不在少数。比如赛珍珠《大地》的农民魂灵,沈从文《边城》的田园牧歌,周立波《山乡巨变》的社会变迁,赵树理《三里湾》的山村风貌,陈忠实《白鹿原》的家族恩怨兴衰等,都从不同侧面或维度,描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世相百态和众多形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和生存智慧,进行如此深度剖析和冷静描写,揭示令人骇然心惊的中国乡村社会底层真相,从而破解中国底层社会演进迟缓的深层原因。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鲁南大地,蝗虫横行、匪患不断、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一个古老的乡村文明正处在徐徐落幕的“夕阳晚照”。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旧制度旧文化逐渐废弛,而新制度新文化尚未成型。作者将镜头瞄准这个遭受内外双重冲击的蚂蚱庙村,以“睿哲玄览”之目光,“湛然寂静”之禅定,“散点透视”之笔触,为读者客观描摹了在一个疾风骤雨的大时代,布衣麻履的底层逻辑与生存智慧,真实记录了旧中国底层生活最后一个原生态的真实样本,正像作者自己所言,“我抓住了那条尾巴”。我们确实要感谢作者抢救式书写,如果没有他在中国乡村社会长期沉潜并形成的深度认知,我们就不清楚民国前后中国农民在底层逻辑的轨道上,是如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艰难蹦跶的。
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一个具备差序格局的复杂系统,它以土地为主导,以生存为底线,以好用为方法,以致富为目的,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礼制习俗、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儒释道与乡土文化,构成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统一;积德行善与坑蒙拐骗,构成形而下的二元对立统一。这些相互抵牾又协和一致的逻辑秩序形成了一个底层逻辑链,自转自足又自噬,自主自洽又自闭。历史在蚂蚱庙村并非单纯的时间流逝,而是在底层逻辑链条上的性命销蚀,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解放,每一次社会动荡、外力的冲击,偶尔也能打破它的平衡,但它的内生修补再生功能太强大了,一阵动乱过去,很快又周而复始、运转如常。结束了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飓风,在蚂蚱庙村则变成蝴蝶翅膀扑啦一丝小风,“种地的照样劳苦,捐税未见减轻”。
这样的底层逻辑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就是在蚂蚱庙村经常耳闻目睹的:人是一阵风;坎垃头子也能擦腚;指头抹蜜饱不了人;凡事怎么好怎么做;干鞋难脱,湿鞋难拿;如果没有车,到处都是路,如果没有船,到处都是桥;咬破树皮能解痛;宁扶竹竿不扶井绳;老百姓懂什么……小说中由此塑造的上百号人物,不论是乡绅、农民还是土匪,或浓笔重彩或寥寥几笔,全部纷披着这样的生存智慧起舞,一个个生气拂面,伸手可触。如大练长的傲慢自大,贾三福的阴阳两面,赵建章的投机取巧,宋寡妇的以身破法,殷云舒的冷艳面世,徐和尚的皮里阳秋,谢芳春的善恶不明,吴兴邦的濒死长号,赵琪的不识时务为俊杰,无不隐含着自鸣得意的生存小聪明。总之,在天灾人祸的轮番冲击下,在民与官、民与匪、官与匪、本村与邻村、本土与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中,乡民们使尽浑身解数,拼尽全部气力,试图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终归还是活成一地鸡毛。这就是蚂蚱庙村的底层逻辑,也是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就像一个蒙着遮眼布的驴,自以为在不断前进,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民智也因此停滞不前。永远的生命守恒,破不了的逻辑怪圈。自给自足自闭的小农经济,只能产生自私自利的内卷与倾轧;文化上的直觉思维、感性思维,难以把这些生存智慧理性地提升到更高境界。
意象,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基本功,它是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符号,往往承载着作者深刻的人文思考和情感寄托,展现其独特的美学特征。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博尔赫斯的“花园”,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作品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元素。“蚂蚱庙”这个意象也属匠心独运,它借鉴了西方的超现实的元素、梦境、幻觉等手法,但更多地融入了中国式的神话、传说、志怪等元素。我们从宗申的呼风唤雨,周大的命运转换,向守德的善恶报应等,每每能看见《易经》的卦象蓍草,偶尔也能感受祝由术的神秘传奇。没有它,小说中的所有虚构、魔幻、超现实的情节和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在蚂蚱庙村,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追求和梦想,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走向。但人如草芥,命如蝼蚁,都像一只只蚂蚱,知晓自己的宿命,仍然奋力地在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逻辑链条上蹦达。可以说,蚂蚱庙这个文学意象包括双重意蕴,一是作为蚂蚱,它是个体生命的象征,既承载着人们挥之不去的苦难记忆,又包孕着人性中的贪婪和残忍,一生一世都在通过拼命蹦跶,来耗尽生命所固有的能量。
诡异的是,蚂蚱一旦聚众成势,又能铺天盖地,横扫大地,成为一种社会灾难。这时的蚂蚱就不再是那个蚂蚱,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原始意象和原型,集体无意识驱动着村民悄然嬗变,异化为蚂蚱的对象物——蚂蚱庙,成为蚂蚱的崇拜对象,从而主宰着蚂蚱庙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蚂蚱》独特的美学特征于是就显现了:蚂蚱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叙事元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构成一种心灵的投射,象征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和乡村的信仰体系,隐喻了乡村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不仅成为一个展现恃强与凌弱、生存与毁灭、尊贵与卑微的冲突与挣扎的场所,而且象征皇权、纲常、礼教、规则等隐形存在。乡民面对困境时的选择和行动,不只受到蚂蚱个人性格和经历的影响,更要受到蚂蚱庙的制约和牵引。蚂蚱庙村的每一次风波与动荡,每一次人性的挣扎与冲突,都与蚂蚱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瘸造,他由邪恶中残存的善念画出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作为一只蚂蚱面对困境时的无奈与选择,更多的是蚂蚱庙背后的“草蛇灰线”。小说最后的收官之笔封神,也都是在这个神秘场所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蚂蚱庙这个文学意象,其双重意蕴的交织、叠加与呼应,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丰富多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多层次多维度,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的主题和情感,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还能够传递作家的哲学思考和价值观念,深化我们对乡村社会底层逻辑与生存状态的认识和理解。
许多评论家论及,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有创新,比如散点透视的方法,章回体的结构,相对独立的故事等。所言不虚,当今长篇小说鲜有这样的艺术追求,有人说能感受到聊斋的况味,诚哉斯言!同时我也由此设想,作者如果在语言上像聊斋一样,用比较浅近的文言叙事,这部小说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此在”,以之区别众多的“彼在”,从而耀眼于现当代长篇小说之林。

来源: 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