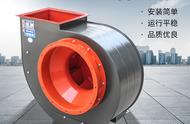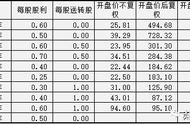应该or不应该
因为前面第一个问题论证了chuā和né进入小学语文教材,从正确性上来说完全不应存有任何异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两个读音是不是应该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在应不应该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反对chu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声音,他们的依据就是这个读音背后与之对应的是生僻字,不仅仅是儿童不常用,大人也不常用,对儿童而言实在太难,因此不应该进入教材。
这样一些观点的出现,实际上依然是对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不了解,仅凭个人经验做出的判断。须知,教材编写和使用既要考虑不同阶段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还要设定不同阶段的具体学习目标,还要考虑未来学生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关注的维度很多,不是单纯一个维度的问题。
就chuā和né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温儒敏先生的解释是:
这两课是学音节,会拼就行,不必一一对应字词。学生此时认字还少,也不能要求一一对应。
这个说法绝不是温主编为了掩饰问题而临时找到的一个借口,而是有明确的依据。请看部编教材一年级上册语文教师用书对这一课教学目标的相关说明。

教师用书对这一课的教学目标有极为明确的规定:学习正确认读和拼读相关音节,而不是把这些音节和背后的字一一联系起来。虽然有借助拼音正确认读认识词语和生字的要求,但这些生词生字都是常见的生字生词。
而某些网友非要说chuā背后的字过于生僻,超出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臆想。他们把这种主观臆想强加于这一课的教学目标之上,而这一课的教学目标中根本就没有诸如认识“歘”字这样的要求。
这种主观臆想所推理出来的结论正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特别痛恨的超标或者说超纲。因此,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然而这种超标或者超纲并不是教材教学目标中的现实规定。
通过主观臆想强加给教材某一教学目标,然后又据此批判教材脱离学生实际,超出学生理解水平,显然这是不可接受的,属于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主观臆想,是因为很多人的记忆中残留了学习拼音的一些印象,觉得一定要把拼音和相关的汉字组合在一起来学习,比如,e就和“鹅”联系在一起,ü就和“鱼”联系在一起,g就和“鸽”联系在一起,等等,甚至不仅配有文字,还要配有图画。

这个记忆没错,但我们所记住的更多是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另外一部分真实发生的情况,被我们从记忆中不经意之间抹掉了。
比如,我们要学韵母时,必然同时也要学到四声,于是老师就会让学生练习ā,á,ǎ,à。在回想这个时,可能还会和“啊”这样一个常用字联系起来。
但我们单独读ēi,éi,ěi,èi时,又和什么字联系起来了呢?恐怕就不容易想到了,因为“诶”或者“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过于生僻了,但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字生僻,于是就没有练习过ei的四声拼读吧。
在我的上一篇公众号文章后面,一位叫作三色猫的网友留言说:
练习拼读,就像弹琴的初级练习曲一样,训练表音符号和发音器官之间的协调。
我以为这个比方很到位。练习拼音仅仅是像弹钢琴一样,最初的简单指法练习,要反复训练,越熟练越好。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最简单的指法训练将来可以用来演奏诸如《命运交响曲》那样宏大的曲子,于是就由此推断这些指法练习对初学者太难,不适合学习。
拼音学习也是如此。拼音只是学习汉字的拐棍,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不一定在学习拼音时,要求每一个拼音都和汉字一一对应。但是为了熟练数量有限的读音,需要多拼各种读音,需要反复练习,哪怕这个读音与之对应的字是一个生僻字。
而且还有人混淆了“生僻字”和“生僻音”这两个概念。不是生僻音就一定对应生僻字,反过来,也不是生僻字就一定读生僻音。
比如,这样几个字:擤、熥、趿、齁、薅、搋,您能认识几个,读准几个?
但是如果我把这些字和它们经常组的词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原来这些字我们经常用。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字怎么写,但是这些字的读音则非常常见。
擤(xǐng)鼻涕 熥(tēng)馒头
趿(tā)拉鞋 齁(hōu)嗓子
薅(hāo)羊毛 皮搋(chuāi)子
这些生僻字都是普通话用字,而不是方言用字。我们会因为这些读音背后有这样一些生僻字,于是拒绝学习这样一些读音吗?
事实上,汉语拼音作为识字的工具,在汉字学习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必须要反复练习,不断熟练,也就是要反复训练表音符号和发音器官之间的协调能力,掌握了这个工具,才能更好地学习汉字。
对方言区的学生来说,发不同的音的难度不同,并不是说chuā就是一个很生僻很难发出的读音。
比如,大学时,和来自h,f不分的方言区同学开玩笑,就让他说“护肤霜”这个词,他要想说得字正腔圆,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还有l,n分不清的方言区,这样的人说他去了趟“河南”,你会误以为他是出国旅游,去了郁金香盛开的国度呢。
对普通话地区的学生来说,虽然学习这些拼音可能难度没那么大。但依然要让他们通过多见多读的方式,了解拼音,让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明白,原来汉字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拼音本身的数量,有一些读音只有极少的一些汉字与之对应,也有一些读音,虽然能读出来,但是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汉字。
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抨击说因为某些读音背后是生僻字,所以附带的这些信息对学生而言明显偏难时,实际上只是从个体的一般的经验出发,看到了问题不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可能存在的另外一面。
比如,“欻”这个字,如果学生问起来,老师给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会意字,两个火和欠(吹气)构成会意。想象一下,猛吹一口气,火欻地就烧得很旺,火苗上蹿。”或许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下子就激发了学生对汉字的兴趣。他们发现原来每个汉字背后都隐藏着这么多有趣味的东西,那岂不是收获更多。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我儿子在学习“金木水火土”这一课中的这几个生字时,我给他补充了这样几个对应的字:“鑫、森、淼、焱、垚”,除了这几个字之外,还顺带简单讲解了“品、众、晶、磊、矗、犇、骉、猋、羴、鱻、赑、毳、皛”等字。
这些字只有极少几个属于常用字,其他差不多都属于生僻字,但是我儿子在记忆这些字时饶有兴趣,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并没有觉得多难。通过这些字的学习,激发了他学习汉字的兴趣,他能够更好地体会会意字是怎么一回事,至少是明白了会意字中的一种造字方法。
所以,换一个思路来看,我们成人所定义的生僻字主要是从这些字的日常使用几率来判断,在《通用汉字字表》中就有主要依据使用频率来区分的一二三级字的分类。
但对儿童而言,并不一定生僻字就一定是难于理解的字。儿童的思维乃至记忆方式并不完全和成人相同。用成人的视角来断定某些东西对儿童一定偏难,他们的能力无法理解,这种判断有时候并不必然成立。

【注】该段文字出处为《周有光文集 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368页。
著名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在他的《拼音字母基础知识》一文中说:
普通话有多少个音节呢?音节的数目是活的,不是死的。可以用常用汉字写出来的有400多个音节。(如果分四声就是1000多个。)还有一些口语音节,没有常用汉字可以写出(例如chua),甚至根本没有汉字可以写出(例如pia)。普通话还需要不断吸收一些方言和外来语,由此也会增加音节的结构形式。
这样的表述和判断,体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高瞻远瞩。
恰好周有光先生在这段话里也提到了今天争论的焦点chua这个读音。但从周先生的表述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周先生反对chua进入小学教材的意思。他甚至还主张“普通话还需要不断吸收一些方言和外来语,由此也会增加音节的结构形式。”
如果片面地引用周先生的话,就可能会让大家误以为周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大家都反对chua这样的读音进入教材,轻则说这样的做法是扯虎皮拉大旗,重则说是断章取义,是非常不好的文风。
当然,也有人揪住温主编在回应中所说的“教材的音节教学采用的是‘穷尽式’,拼出的读音比较全,也比较多,修订时可以考虑精简一些,更适合学生学习”这句话不放。列举出诸如“duang,pia,biu”等读音说为什么既然是“穷尽式”,这些读音不放在教材中呢。
这明显是对温主编话语的曲解,“穷尽式”只是原则,但也只是列出的读音比较全,比较多而已,不是全部。那些不存在于普通话之中,也没有汉字与之对应的读音,一一罗列出来并没有实际意义。
从以上我的观点来看,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么说是完全站在了力挺温主编,力挺教材的立场上了。
实则不然,我只是从作为一线语文教师的角度来谈一些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但我是初中语文老师,并没有教过小学一年级拼音的丰富经验。
实际上,关于教材中拼音内容的安排,到底存在怎样的优点,怎样的缺点,与其听外行来谈论,不如听听常年教小学一、二年级拼音的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来说说,他们才是真专家,才更有经验。
写到这里,我想到韩寒的一篇文章:《我也曾对那种力量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