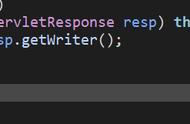程德培(图源:上海作家网)

叙述语言的功能与局限
一
伯特兰·罗素说,“在我看来,研究语法是能够弄清哲学问题的,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哲学家们普通所想象到的。虽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个语法上的区别当成一个真正的哲学差异,但语法上的区别往往成为哲学差异的初步证据,并且往往最有成效地成为发现哲学差异的一个来源。”借着罗素的这一说法,我也想把这些远远超出普通想法的差异移植到语言与小说的关系上来,因为同样,对语言的关注也能帮助我们认清小说叙述艺术的许多问题的。
在此之前,若要说到提高语言在文学中地位的活,那已是高得不能再高了,别的不说,单是高尔基那句把语言列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名言,就早已家喻户晓了。但是,语言究竟在什么层次上,在什么意义上,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哪些关系上表现出它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的?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问题。一般地说,我们所要强调的语言的重要性,诸如它的生动、形象、通畅、精练、鲜明等要求,即使是非文学的写作也是需要十分注意的。叙述语言不注重本体性的功能,尽管把语言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但一落到具体处,往往陷入乏味的老生常谈。当然文学中有许多问题是永恒之谜,谈起它,也非老生常谈不可。但是,同是老生常谈,情况是不同的,有的是一种平庸的饶舌,有的则是进入艺术境界的感悟。比如,同是“艺术创造的最高技巧乃是无技巧”的说法,出之大师之口和出之确实什么技巧也没有的作者之口,其价值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况且,对艺术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因为现代语言学几次革命性的进程,已经打破了“工具说”那一贯自信的面孔。我们可以暂且不论那些学术性专业性太强的索绪尔、雅各布森、罗兰·巴特、拉康等不同学说的本来面目,也可以暂且不论语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的功过以及由于心理学的科学进程给予语言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这里仅就新时期小说所提供的耐人寻味的现象,来观察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语言问题。
在此之前,笔者曾写过一篇关于丰富小说语言表现力的小文,从几位出色小说家的引人注目之处,感到了当代小说有一种有意丰富小说语言表现力的新变。因为在这种有意追求以前,小说语言的确是作为一种简陋且不起眼的工具存在的。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类似像《伤痕》那样的作品,从叙述语言艺术的角度讲,还是幼稚、不成熟、不够格的作品。应当承认,这种认识和七年前它作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的巨大影响相比,的确有了很大的差距。差距既说明了人们审美判断的角度、重心、标准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在七年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语言对作家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媒介。对伟大的小说家来说,总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让人们忘记语言这一媒介的存在,而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媒介的胜任,也许更重要的恰恰在于它的局限。当十九世纪的小说正处在自信的高峰状态时,作家们并不感到语言的麻烦,巴尔扎克从不怀疑他的《人间喜剧》从其所选择的词语中映现出来的可能性。然而随之高峰过后,语言的局限性便大摇大摆地登台了,它成了小说舞台不可忽略的角色。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个时代小说辉煌的一面时,也造成了那不被人注意的暗淡一面。很可能,那暗淡的一面恰恰给另一时代提供了夺目的机会。于是,萨特在他那篇著名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思考:“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我认为,新时期文学在数年间的前后之变,多少揭示了抑或隐含了世纪性小说观念突变的某些因素。比如对语言这一媒介的技巧性认识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或对语言这一媒介功能的过份自信到颇多怀疑和困惑,对文学语言的一般认识上升到对小说语言的本体性认识等等。

[法]让-保尔·萨特 :《什么是文学》
译者: 施康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我们曾经有过崇拜题材的时代,象淘金狂寻找金矿一样,渴望能找到爆炸性题材。这种热情曾一度支撑了许多作者,也支撑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品。当然,这种淘金狂最终是以失望居多的。而自从有了汪曾祺的《受戒》《异秉》对于小说的许多固有认识,都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冲击。为什么相隔几十年的题材会转而发出夺目的当·代亮光,在随之疑问而来的许多顿悟之中,语言便是突出一例。而与汪曾祺差不多的林斤澜,也是充当了多时的敲边鼓的角色后,才使其不显眼的艺术魅力发出经久的光亮,在回答这一疑虑的诸多因素中,语言依然是重头。而且汪、林等著名作家的创作所渗发开的潮头更不可忽视:何立伟的引人注目、阿城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贾平凹创作的高潮迭起、陈村的不断出击……都不同程度地为语言恢复了声誉。
题材的重要和语言的相对次要产生了对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之所以能以偏远山地生活的记录赢得文坛的击节,阿城之所以能在知青题材的高潮过后抛出《棋王》惊动文坛,也都是告诉了我们,题材已失落了它的皇冠地位,而连同这些作家的创作实绩一起登场的语言,却使得我们的批评不得不把力气用来保持贫困的尊严。问题在于,不管怎样保持住尊严,贫困毕竟还是贫困,要改变批评的贫困,唯一的途径仍在于正视贫困本身。
二
语言与经验的区别,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作家们似乎更关心的是语言作为符号与作为艺术对象的经验之间的联系,关心语言是如何通过我们称之为“比喻”“转喻”“隐喻”的途径,使一堆符号成为一堆意义。由于有了这种联系,才会有整个源远流长的小说历史,才会有整个小说理论所沿袭下来种种说法,诸如模仿、记录、反映等等。
对待语言与经验的联系,以往常常把语言的作用纯粹看作“媒介”与“工具”,仅仅承认语言对作品内涵承担传达的作用。依据传统的习惯看法,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语言作为媒介或工具是否与经验纯然无关,语言对于经验的传达是否没有局限与边界,或者说人们是否可以摆脱语言先获取意义呢?
我不知道,历史把这个问题最终是放在小说家还是批评家面前,究竟是哲学、语言学在推卸责任,抑或是文学界本身具有了某种超前意识?况且我们此刻面对的这个问题,完全可能是别人谈论已久的课题。
语言与经验的关系,我们的习惯划分是很清楚的。对于创作,一般都认为在运用语言之前,作家都有一个认识生活获取经验的前提。这一前提提示我们,语言对经验或意义来说,其地位是次要的或者再次要一等的。我们历来的批评采取还原式,分析作品往往离不开从题材到主题到人物最后到风格特色、语言技巧的程式,看待语言只局限于炼词炼字的一角,其原由也多少和这一前提有关。而“前提”的失足就在于它认定落笔之前是非语言阶段。这里且不论作家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时需要运用语言与别人交流,就是不说话,只要和社会发生联系,就不能脱离语言。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说与听、写与读的关系之中,而不是任何一个单面。我们说一个人听懂或读懂了一个词,其实也包涵这个词原存于他的语言之中,而不是他不知道的词中。人对词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他能相应地使用。狗则不同,它虽能接受某个符号,但绝不会使用这一符号。这正如李播说的,“我们学习了解一种概念,好象我们学习走路、跳舞、舞剑或奏一种乐器一样:这是一种习惯,即一种有组织的记忆。普通的用语,涵盖一种有组织潜在的知识,这是一种潜藏的资本,没有它,我们当陷于一种*,假造伪币或无价值的纸币的状况中。普通观念是智力秩序中的习惯。”
当然,真正做到使语言摆脱纯工具地位的,还是要数二十世纪的那场语言革命,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的二十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创造的东西。并不是好象我们有了意义,或经验,然后我们进一步替它穿上词汇的外衣,首先我们之所以有意义和经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语言使两者可以置于其中。”这里,我们不能在“语言革命”的背景及功过是非上走得太远。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调整一下我们原有的对于语言的狭隘意识。我们只要设问一下:为什么在数年前非常走运,被人们认为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时隔不久就失去其创作的潜力呢?我们也只要比较一下五、六年前轰动的作品与今日出色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在语言问题上的差异。当然,这种变化的功过程度究竟如何确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富有实证精神的推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这外在的变动之中,大致看到以往那种功能主义看待语言的态度已经受到了来之创作实践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有意思的,它至少是为我们重新塑造了语言这个角色。法国作家克洛特·西蒙为我们这样描写了这个角色:“词本身就是现实。如果词自然地表示它所命名的物体的形象或概念,那么它同时也使人想到许多其他的概念和形象。这些概念和形象在真实物体的可计算的时间和空间里相距甚远,但是词把它们顷刻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写作时会出现大量供选择的概念,当考虑这些概念时,它会严重地歪曲作者的原意。;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些使用语言的同时也被语言所使用。这样,很自然就有大量意思不象传统规则那样被‘表达’出,而是被创作出来了。”
笔者可能孤陋寡闻,自认为西蒙之言昭示了我们创作中长期以来的许多难解之处。
其一,就是长期以来,作家写的创作谈,对我们理解创作的有限性和所起的迷惑作用,除了心理学所认为那种人不可避免具有伪饰自身的根本弱点与人的意识层次对无意识层次无能为力外,还包括了语言在可供选择的时候,也大量地歪曲与再生了许多作者原本没有的含义。
其二,词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符号放在那里供作家选择,它除了具有音象形象的特征外,远在作家选择前就带着历史的沿袭与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一个词不仅具有和无数其他词相联系和相组合的功能,就是对本词的理解也是不乏多种可能,甚至包括歧义。何况,中国。字的歧义和组合的复杂比其他文字,从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三,不仅作家作为人的复杂性所构成的矛盾冲突决定着本文的审美层次,影响着作品的感染力,而且语言自身的活力也同时创造着本文的。这种活力一方面表现在语言作为作者表意的工具出现,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的含义及歧义的扩散传播反过来支配着作者:一方面语言是有秩序的,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组合的,而另一方面作为它反映的对象则又是混沌的,一方面语言的记录与书写是稳定的,而另一方面它的对象则在瞬间都会发生着千变万化,包括选择语言的主体都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着;一方面语言作为可供使用的符号放在那里,选择的人是有充分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代代相传的语言符号,又是任何单个自由意志非接受不可的……所有这些给予作品的影响,决不会低于人本冲突所起的作用。
讲到这里,很自然使我们联想起闻一多那句说及庄子语言的话:“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多少年过去了,把语言看作目的研究却几乎至今没有。
三
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语言表现的有限性说起。语言沟通了原先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概念。在这过程中究竟是语言带领人的思维向对象世界延伸,抑或是人的思维带领语言符号去开辟意义领域呢?这似乎是个难解的谜团。不过,当语言处在鼎盛时期,它确实会犯骄傲自大的毛病,误以为这个世界已被它所囊括,这个错误也或多或少地传染了那些自信的大师们。
什么时候,这个自信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感觉到也会有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难以言传”、“不可言传”被越来越多地重复使用,不仅隐示了非语言领域的存在,也同时解脱了文字自身的困境。问题在于,人们一旦脱离了语言,就根本无法证明非语言经验的存在。脱离语言的纯经验至多只能是一种假设,可又别忘了,既使是假设也要依赖语言的表述。我们无法实证假设的存在,当然也无法证明假设的纯属乌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寻求语言的有限性。现代小说为了表现绵延、表现“超时间性”的感觉、表现那与神秘经验无法分解的瞬间意识所付出的努力,所谓在意识中将时间延长或缩短的不间断性,经验与记忆中自然交替的互相贯穿、永恒性与短暂性、原始思维与死亡的时间观等等,都证明现代小说在追求语言表现力的成功拓展,表明了在从未开垦的处女地中获取了开垦的收获,反过来,收获的成功也反证了这块土地是属于未开垦的过去时态。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看语言与感觉的关系。我们知道,用语言表现感觉是极端困难的。如果要区分苹果与梨子滋味的不同,大概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对人的感觉来说,这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我们要认真地用语言来清楚地说明这两种不同的滋味,就会突然发现语言的表现竟变得如此无力,词作为选择的对象一下子陷于贫困之中。谈到这一点,自然使我联想到作家赵本夫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也同样地谈到了语言之于感觉的无能为力。同是一个“痒。字,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大概没有人会不知道它的所指。而我们只要看一下《辞海》对它的解释,语言的漏洞便显而易见了。什么是“痒”,按照《辞海》的说法是:“皮肤或黏膜受到轻微刺激时引起的想挠的感觉。”怪不得赵本夫在看了这条经典的解释以后,对语言表示了一个作家的无可奈何。
是的,人想要用语言解释自己的感觉经验是困难的。当你处在恐惧与危急之中,处在茫然无策、进退维谷之状时,处在人群的包围之中,感受一种强烈的孤独时,当你在一片寂静之中经受一种焦灼不安的折磨时,确实会感到语言表达的难以胜任。
然而,就犹如命运的不可捉摸一样,小说语言生来的一个艺术使命便是要表达艺术家不同凡响的感觉。我的理解,当今许多出众的作家之所以把丰富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作为关键之举,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准了小说作为叙述艺术的一个根本性难题。而当今在语言上棋高一着的作家如林斤澜、汪曾祺、阿城、贾平凹、何立伟诸位,同时又是在艺术感觉上堪称一流的。此两者兼容于一身的现象并非是偶然的。这些作家之所以能给我们以这种印象,其唯一的见证和媒介也只是构制他们作品的铅字。语言在读者与作者中间,除了负有传达作者心灵的使命外,它确实又·以一定铅字组成的语言结构,以渗透扩散运行的方式,确立独立的语言系统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文本的主体性。
现在,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称赞莫言作为艺术家的突出感觉,而且最近一段时期此等相类似的评论文章也不少见,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称赞其感觉的时候,是否也太千篇一律地将功劳归之于莫言的个人素质与经验,而语言的独立意义似乎消失了。小说艺术的全部问题如果全在于个人素质的话,那么语言便太可怜了。“意义就像我的商品一样,为我所有,语言只是一套代价券,它象金钱一样,使我们可以拿自己的意义商品同另一个同样也是意义私有者的人去交换。根据这种经验主义的理论,很难断定换来的东西是否货真价实,因为我们如果产生一个观念,给它贴上一个语词符号,再把整个儿掷给别人,这个人看到符号便在自己的语词分类系统里搜寻相应的观念,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在以我的方式找寻对等的符号观念呢?”这段话讲得太精彩了。如果我们的批评也是能这么反过来考虑一下的话,那么原有的认识观念、审美观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观,而且对莫言的研究,也会有摆脱类同的新局面。
以语言表现的薄弱之处,作为艺术媒介的主要使命,是否因为这一对立才最终导致叙述语言的艺术美,这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揭示了对立的奥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叙述语言的特性及功能。
任何一个从事言语行为的普通人,只要回顾一下每当语言面临着表述感觉的困境时,就会发现其出路无非两条:一是隐约含糊不清的表述,以求听者心领神会的理解;二是寻求相似事物的替代,比如苹果的滋味,可以寻找一个平时人们都熟悉的东西为例,指出苹果的滋味就象这种东西的滋味。当我们意识到后者的时候便会发现,生活中话语的出路和哲学家、语言学家所总结的语言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著名的雅各布森的观点,认为语言之所以把一个意思与另一个意思联系起来,不外乎由于意思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类似,或在时空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的互相接近。雅各布森分别把这两种方法称之为隐喻法与转喻法,因为这两个词,隐喻和转喻,是人们把意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缩影。”事实上这里讲的就是和我们刚才提到那两种转移法一样,无非就是一种意义被另一种意义所取代,抑或是整体被其部分所替换。
而这种归结移用到小说语言上来,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叙述语言的象征问题,它们相通的 一个核心之点正来之于语言在艺术领域中为追寻感觉经验而对自身的超越。从这一点上说,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性正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的内经验,它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及物理世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揭示的正是人的灵魂与心灵,用弗洛姆的说法便于脆把小说的语言称之为象征的语言。
这使我们想到总结新时期文学的巨大变化时,众多关于小说诗化、象征化、抽象化的论述(论述本身当然优劣混杂)。这一总括的相似性,正是无可辨驳地告诉了我们,小说创作开始正视自身的进步。遗憾的是,众多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作品含义升华的认识上,遗漏的恰恰是叙述语言的本质,这在一定意义正是小说艺术目的的关键。
四
从小说本体的角度看,小说语言的局限性与功能恐怕还集中于叙述时空,现实时空与公理时空的差异上:语言表达为顺序锁链的束缚,语言时间的线性特征与生活的原生状态、语言的停顿间隔与无缝隙的生活流,语言的理解性传达至少要贬低与忽略非语言方式的交流,象人类的脸孔所特具的传达感情与表达理想的能力等。这种种冲突自然揭示了小说发展史的动力因素,而冲突的无休止本身则也暴露了语言在小说中的地位,语言要充当小说的主角,使时间与空间成为配角,它就必然地要克服自身的薄弱环节,并且有力量有信心在根本冲突的表面呈现一种和谐的美态。这也就是小说语言为什么需要弥散力、弹性,无穷无尽的隐喻与借喻的原由所在。不然,语言便不能征服时空,弄不好反被时空所吞没,语言一旦被时空吞没,再有“意义。的事件硬塞进去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社会历史变化的时间要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时,小说便充当了训练人们去适应一个一成不变环境的角色,而且后者也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种训练。但是,这种变化与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到了今天则不同了,变化的周期远为一个人的生命期短得多。于是,小说的义务,便成了训练人们随时准备去适应日益变化了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焦灼的现代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离不开小说的;也由于这个变化,语言也重新塑造了自身,它表现出对正常思维的不恭敬、对常规时空的不驯服、对基本逻辑的叛离、对传统习惯的反悖……。关于这,我们只要读一下当代文坛的怪杰马原、残雪、扎西达娃等作家的作品,只要读一下颇具当代意识的韩少功、刘索拉、徐星等人的作品,便能略知其一、二了。
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语言的演变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概还得数人对自身思维认识的提高了。人的思维,一般来说有清醒时候的思维与睡眠时候的思维的区别,清醒状态的思想及感觉主要是对挑战产生反应,为求生存的人们必须对付控制我们的环境,以及保护自身免遭伤害而改变环境,这时候,人的思维过程属于时间和空间的逻辑法则;而睡眠状态与此不同,强调自由自在,可以不受外在现实的控制与反控制,不必再注意外在世界,我是思想与感觉的唯一系统。这两种意识与思维特征影响到语言表达,前者的基本标准是言语句法和逻辑——并以规范的文法、正确的语言为意识的最高级,是统一、明晰和有条理的一级;后者则是句法混乱的思想、写作和话语为意识的最低级,是艰涩与紊乱的又一级。
如果这种由于思维状态不同而决定的不同语言为两极的话,那么小说语言都不可能纯粹是哪一级的,它只能大致上倾向于哪一级,而且就是后一级的语言也是在一边打破句法、逻辑和条理的规范时,又和修辞、象征及意象联系在一起的。
再推进一步,如果说传统的小说语言表现基本上是倾向于前者的话,那么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意向就是追寻后者,拓展后者,力图兼容后者。这一点作为新时期小说的前后之变,也是有着大致规迹的。由于这一变化,当代小说在使用符号的形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例如,在写作中不使用标点符号,对这个问题议论比较多,褒贬不一,褒者以詹姆土·乔埃思根本不用标点符号为证,但贬者也振振有词,认为乔埃思的小说是根本上打破语法规范的,他的语言是根本点不上标点符号的,是成功地表现了意识的流动,而相反,我们的那些模仿者表面上看看没有标点符号,实际上标点符号是可以点上的,一句话,就是这种没有标点符号仅仅是为了没有标点符号而已。贬者是相当有力的,最起码的就是贬者揭穿了创作中的某些故做现代派状的现象。这一点笔者是很赞同的。但除此之外,也不排斥笔者的一点疑虑,即不用标点符号的作用除了表现无意识流动外,还有其他的审美作用,比如前不久在和一位作者谈及汉字不用标点符号的作用时,他就认为,汉字的排列是方块形的整齐排列,而阅读中标点符号占据的空间很象是一个个出气孔,标点符号不但造成了时间上的停顿,而且是透气的空白。而作者有时候要造成一种阅读上的逼迫感,拿掉标点符号会造成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氛围。老实说,我是很欣赏这位作者的见解的。事实上,不止于此,象陈村最近写的一篇短篇《我的前半生》一样,整篇小说不用标点符号,全由作者从小到大唱熟唱烂的歌名连缀而成,因为是大家都可以自由联想的歌名,所以不存在语法上的顺序问题,也不存在读得懂读不懂的问题,我以为这样的处理也未尝不可。
由此我还想到,小说语言对于人的睡眠状态思维的追寻,其途径和可能性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仅只无标点符号一种。在创作上,为了表明意识的方向和流变,叙述语言已经表现出多种方式,象常用破折号和省略号。福克纳使用的斜体字,弗吉尼·沃尔芙爱使用括弧等等,这些也都同乔埃思不用标点符号具有同样的创造价值。
当然,意识流的问题只是一例,叙述语言的功能与局限,以及在实际上的力图超越,事实上是多方面的,比如:人接近现实与语言接近现实的差异,人感觉事件与语言叙述事件的差异,视播艺术的普及怎样部分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同时将波及到语言自身等现象,都是我们要认真加以思考的。
陈村写过一个小小的短篇,题目叫做《我的前半生》,内文全部用我们这一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花样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酒干哪淌卖无酒干哪淌卖无……从题目到内文没有标点,文章一大抄,居然也有五千字之多。陈村说,抄就容易吗,难就难在组织拼贴的功夫。
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书城.2009年第1期,收录于《今天》第118期,以及黄子平著《远去的文学时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