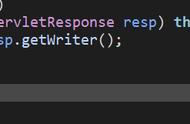五
小说是用于交流的,一部小说如果失去可供阅读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很难确证它的意义的存在,如谈它存在,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堆不可破译的密码罢了。由于意义的消失,当然也很难认定小说的存在了。所以,从交流的角度讲,语言这媒介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除了其胜任的一面外,同时也应该包括其障碍性的一面,确切地说,叙述语言也是一种障碍的媒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略有提及了。
这里要说的是,媒介双方的一些天然对抗:从表现上看,语言显然是服务于个性的,个人的特有意识受各个不同侧面支配,影响着语言,即所谓“文如其人”。而当今的发生修辞学,已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处,认为,每个人对生活中的某些主要事物都有特殊的经验和感受,因而不自觉地会赋予这些事物以一种特殊的价值,从而使它们起到一种特殊的象征作用,例如力量型的作家,语言风格干脆,喜欢用不带修饰成份的名词和动词,形容词不多但有力等。这些都是从表现的角度,从个性控制语言的角度来讲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从接受的角度出发,这种个性化的意识又要传播给众多的其他意识,不仅是传达,而且还要感染别人,引起别人的共鸣。这无疑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以前我们总引用越是具有个性的东西越具有共性的说法,笔者对其应用的“四海皆准”性略有怀疑,这里从略)
对信息的传播来说,个性是会增加可理解性的难度的。语言的媒介作用也是如此,越是突出个人意识也就越增加媒介的障碍。
所谓增强个人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增强语言的借喻能力。对一位真正的小说家来说,最初的创作念头,总是来自一些非常模糊的东西,得自似有所悟之状的;一句偶然说出来的话,或一段对话、一个事件,甚至可能一个同任何情景都没有联系的朦朦胧胧的闪念,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启示,它可以是一个偶而获得的图式,偶而传来的东西,偶而穿过的光束……这些偶而萌发的艺术起因,很可能与故事的框架、情节的显现与隐匿无关,但是又大致决定了小说节奏、情绪、氛围、音调、味道、紧张度的命运,也就是说必然要导致小说文句的命运。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语言叙述过程的第二个两难,即接受角度的明晰与决定小说文句命运的朦胧之冲突。
作为小说语言主要归结的隐喻与转喻,不只依赖于表现,而且也指出了观察者与象征化了的被观察对象之间的通道。通道有了,还要靠人的努力去走通它,这就涉及对小说的理解,小说语言的象征是必须通过思考的过程被翻译成物体的形象、感觉的形象、概念的形象。现代象征性思维理论已经指出,即使在最平凡的视觉行为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看到事物的相似之点。寻求不同事物的相似之点,就包含了象征的基本含义。指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小说可供理解的基础。
当然,艺术创造又与一般人的认识能力有所区别。同是运用象征思维的能力,艺术上的象征创造把网撒得更宽广,视野更开阔,联想更曲折,而一般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分类学的意义上。认识能力能使我们在小孩的爬行中联想到狗,从小孩的刚会走路中联想到熊;而象征创造却能在暴发户与涨潮之间看到共同之处,从月有阴晴圆缺看到与亲人的团聚,分离有相通之处,能把一座具体的城市与骄傲联系起来。此外,象征语言还.有一种通道,便是语言本身,语言的含义丰富,词的组合犹如魔方,往往导致多种可能,它会在不同内在形象发生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制造出创造性的误解。
总之,列举以上种种,并不能说是已经足以指出语言在叙述中的功能及局限,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陌生且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问题。为此,笔者这里愿做一个漏洞百出,愚笨鲁莽的先行者,目的在于引出智者的登场。
1986年9月于上海
收入《小说本体思考录》,上海文艺出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