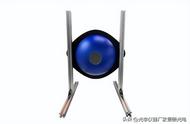人民网巴西3月25日电 (记者 陈效卫) 近日,中国、巴西两国出版界在里约成立合作选题研发中心,联袂推出图书品牌“SHU”,以促进当地翻译出版中国主题类读物和中巴两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作为“书”字的汉语拼音,“SHU”在进入巴西前,中国文化学者进行了精心“备课”,以确保其在巴西葡语(巴葡)中不仅有对应清晰的发音,而且不存在任何贬义与恶意联想,从而避免了因不“知彼”而带来传播中的“自伤”。
所谓“自伤”或“文化自伤”,是指在一种语言里原本是中性甚至偏褒的名词,其发音或含义在其他语言中却有着令人难以启齿的贬义,在交流中如原汁原味地表述,就会给人留下粗鄙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加速向世界舞台中心迈进,不可避免地遭遇各国文化。为避免“自伤”,我们需要入境问禁、知己知彼,进行跨文化的学习和改变。需要强调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因此文化交流涉及所有走出国门的单位和个人、产品和品牌,是国之大事,不可不察。
一、走出去,要视情“梳理打扮”
对上文提到例子“SHU”,有些读者也许颇不以为然:简单的几个拼音字母,到另一种语言中怎么就“自伤”了呢?实际上,这样的教训并不遥远。2006年11月中国重庆长安汽车在巴西圣保罗车展上首秀时,因其品牌“CHANA”在巴葡中与一个非常粗俗的词xana发音相同,从而沦为巴西街头巷尾的笑料。可以说,“CHANA”若不更名,任何一个正常的巴西人都不可能购买这种名字难于启齿的轿车。
“自伤”主要包括音和义两大类,以下重点以姓氏为例进行说明。
中文拼写、发音与外文相同或相似而导致误解
除了葡语,“自伤”还发生在其他语言中。笔者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差时,发现当地“华人酒店”中的“华人”被拼成了“HUA-QIAO”(华侨)。原来,汉语拼音“Huaren”(华人)发音与智利等多国西班牙语中的“guarén”非常接近,而后者指的是一种体型较大的老鼠。为避免食客望“鼠”却步,店主没有拘泥于汉字、拼音的一一对应,而是采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灵活巧妙地化解了两种语言的冲突。
在英语中,最常见的“自伤”例子是熊猫。熊猫英语译写的后部分(Panda)与英语的“拉皮条”“勾引”“煽动”(Pander)一词拼写相似、发音相同,所有带有“熊猫”字样的商店和品牌因此悉数“躺枪”。与我国直辖市上海(Shanghai)发音完全相同的拼写,在英语中却是动词“诱拐”“欺骗”之意。2016年12月在美国上映的《爱乐之城》,让“shanghai”为中国人所熟知。追本溯源,这个贬义词是美国人的黑锅,让上海人给背了。
在波兰语中,“琵琶”与一个非常不雅的单词发音一致;“沙滩”,则“撒旦”(Satan)发音高度一致。撒旦曾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负责在人间放置诱惑,后堕落为魔鬼,被视为与光明力量相对的邪恶、黑暗之源。
在俄语中,有的贬义已细化到单个音节。汉语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专名中的带有“hui”(辉、慧)的发音,无论是什么声调,与俄语的Хуй都惊人一致,听起来都会令人产生极其恶意的联想。
中国姓氏在英语中发音沦为“禁忌语”
以上情况也许只是个案,无关你我,但涉及姓氏“走出去”带来的“自伤”,很多中国人则难以超然物外,大姓尤其如此。以下主要以2017年人口统计前100名的姓氏在英语的发音为例进行说明。需要强调的是,这类“自伤”,与拼音字母大小写无关,与声调也无关,所有同音姓氏都会受到“株连”。
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来高居榜首的中国第1大姓——“李”。李姓汉语拼音为Li,但英美人士倾向于将元音字母i读长元音ai,拼读起来与“撒谎”(lie)毫无二致。如此以来,李先生(Mr.Li)就沦为“撒谎先生”(Mr.Lie)。一同“蒙冤”的还有第92大姓氏“黎”。而排名第98的“赖”拼写为Lai,发音与“撒谎”天然一致,对于英语的“栽赃”似已有口难辩。
第2大姓“王”、第57大姓“汪”和第29大姓“董”似乎有些风牛马不相及,但在贬的内涵上则系“近亲”,同属最严重的五星级禁忌语。看看外国小伙伴对这些姓氏发音的诡异眼神,就该“秒懂”了。具体含义,可查阅英语俚语词典等相关工具书。不明其义,自行面壁。
在汉语中本是动词“做弓”的第三大姓“张”,在英语中(zhang)同样是个动词,指考砸了,如“他英语期末考砸了”(He zhanged his Enlgish final)等。
第11大姓“徐”、第35大姓“许”和第36大姓“傅”几个看似不相关的姓氏,进入英语时却同时“躺枪”。众所周知,英语中的“Fuck ”是极其粗俗的骂人话,因而常使用其简化形式:第一个单词取首写字母,第二个则取其发音,这样整体就缩略为“Fu”,与“傅”的拼音完全相同。英语还常用X字母委婉地表示“Fuck”,这样Xu与Fu一样在英美人心中都成了禁忌语。
第54大姓“戴”(Dai)与英语“死”(die)发音一样。碰到这样的姓氏,老外会好奇地询问:好好一个大活人,为什么偏偏叫这个姓氏?如果姓戴的是位医生,病人自然会望而却步:谁愿意找“死医生”(Dr. Die)看病?如果名字再带有ing的发音,如英、颖、盈、萦、瑛、莹、樱、璎、营、迎、映、鹰、赢等,就更会坐实其恶意。戴英(Dai Ying)合拼连读为Dying,意味着“垂死”。钱钟书在讽刺《围城》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李梅亭时,就借用了这种合拼进行时:梅亭其实就是英文mating(交配)的音译。
对于第63大姓“石”、第80大姓“史”(Shi)等,如果名字叫婷、廷、汀(ting)等,同样会遭遇上述尴尬。石婷(Shi Ting),拼音连读就成了英语的“排便”(shiting),在自我介绍“我是石婷”(I'm Shi Ting)更是与进行时态“我在排便”(I'm shiting)高度一致。同样,名字含有“诗婷”发音的任何姓氏,都难以摆脱英美人士的“坏笑”。这一点,远比刘洪涛先生自我介绍“我是洪涛刘”(“红桃6”)要尴尬。
此外,第41大姓“苏”(Su)发音与含义是“起诉”“控告”的“sue”相近。第62大姓“方”(Fang)和第86大姓“万”(Wan)分别是“毒蛇的毒牙”和“苍白”之意。而第100大姓“文”(Wen)所指“粉瘤”系皮脂腺囊肿的俗称,虽属良性,但毕竟是不招人待见的疾病。
以上姓氏在英语中属“先天不足”,而有的姓氏“自伤”则是方言惹的祸。如“项”(相、向)姓在南方某些方言中读成“杭”(四声),在英语就成了“Hang”,拼写形式与“绞死”相同。
禁忌语有两个悖论:一是别人对你使用是咒骂,而自己使用则属自嘲。但问题是,包括姓名在内的专名很少自己使用,而且自嘲需要特定场合。二是知道的越多胆越小。但正是这种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胆小”,减少了自己“受伤”和对方尴尬,最终获得的是一种双赢。
不同文化背景导致褒贬大相径庭
与发音迥然不同,含义导致的“自伤”会同时大面积出现在多种语言文化中,更需慎之又慎,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
历史上,“龙”(dragon)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龙在中国文化中自古就被推崇为吉祥神兽和神明,是帝王的象征,中国人也自称是“龙的传人”。与“龙”有关的表述尤其是成语,大都充满吉祥意义。但在英语中,“龙”却沦为喷烟吐火、凶猛可怕的怪物,是邪恶、不幸的象征和贪婪、残暴、专制的化身。英语中有与龙有关的词语大都含贬义。如与上帝作对的恶魔撒旦被称为“大龙”(the Great Dragon)或“老龙”(the Old Dragon),基督圣徒还把*死龙作为荣耀,引以为豪。有鉴于此,以“龙”字为专名的商品和品牌在西方就容易引起恶感。至于有些人把“龙头企业”中的“龙头”想当然地直译为“龙的头”,更是让老外错讹茫然。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自伤”的典型是国产白象电池和蝴蝶缝纫机。这两个品牌在欧美销路长期受阻,就是因为“白象”和“蝴蝶”在英文中分别有“昂贵而无用”和“轻浮的女人”之意。几十年过去了,新生的“白象食品集团”“白象电机”等企业和品牌仍在不断“重复历史”。
目前,“走出去”的汉语教学,也带来了一点“自伤”。后裔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和寓言以及“二十四孝”等,体现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百折不挠和以孝为先的精神,但在当今背景下,也难免被当地人解读为破坏自然和方法失当。对于缺乏历史观的中小学生们,就更是如此。
总之,涉及中国文化的有些内容需视情“梳理打扮”。素面朝天走出去,“自伤”在所难免。
二、“蝌蝌啃蜡”这种饮料,你愿意喝吗?
重庆长安汽车参展的尴尬事已过去十几年了,几位巴西朋友在谈起此事时仍忍俊不禁。他们认为中国厂家在进军巴西市场时,需要做足功课,花功夫研究相关的葡语词汇,以免难堪发生。在“第一印象”中要避免“自伤”,就要做到预先知彼、实时更正。
一是入境问禁。入乡要随俗,入境更要问禁。无论自身多么“高大上”,如果犯了当地忌讳,更会留下负面印象,徒然留下“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哀叹。也许有人会说,当地专家、汉学家不是能明白无误地说清吗?他们毕竟是极少数,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教育所有当地人。而通过入乡随俗、入境问禁来“接地气”,不仅是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也是提升交流效率的捷径。这实际上与至圣默罕默德所说的“既然大山不能向我们走来,我们就向大山走去”(“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不谋而合。
入乡随俗、入境问禁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劳永逸。同一个汉语名词,在不同语言发音所带来的褒贬含义大相径庭。实际上,即使是同一语种,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葡萄牙葡语(葡葡)是“小伙子”的puto,到巴葡则成了“妓女的儿子”。当然,而对于有些国家使用的我们似乎能看懂的语言,同样不能想当然。如汉语“书信”对应的日语是“手纸”,这不是“自伤”,日语原本就是这样表述的。日语中手纸(厕纸),则借用了英语toilet paper,用日语假名拼写就是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同样,近年“新晋”的日本姓氏“我孙子”(あびこ)在日语中无论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官职,还是古代的打渔村落,抑或是日本从国外引进的火神名,都不存在任何贬义,在理解时不能想当然。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即使在国内,有关表述也要有所顾忌。如“上海航友宾馆”中的“航友”拼音“Hang You”在英语中是“吊死你”,懂英语的海外来客难免望而生畏。如果这个宾馆是在偏僻省份,且其拼写是在特别小的语种中含有贬义,则无须担忧。但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城市,该宾馆作为涉外星级宾馆地处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对面,且贬义又出现在实际上扮演着世界语角色的英语中,因此,拼音还是要设身处地。若改为“航空之友”,就可大大冲淡原有恶意。
二是向工具书和专家学习。文化走出去,既是慢功,也是硬功,甚至是无底洞。看看《英语委婉语大词典》等类似的工具书,就会明白语言陷阱多到防不胜防。
美国在审查车牌文字上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民族“大熔炉”,美国每年申请的数百万个个性车牌必须照顾到不同文化的感受。各州规定个人车牌所具有的特殊内容,必须文字健康并经政府部门批准。为此,审查者不仅要熟知本州详列的禁忌,经常上网查找,不断翻阅各类俚语词典,充分发挥想象力,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审视车牌上的文字组合,并在遇到外语难题时咨询语言学家团队,严防任何冒犯他人、伤害感情、有碍观瞻、违法犯禁以及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等辱骂的语言出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几年前华盛顿州一个标有“CABRON”车牌的车主在被起诉后称该词是“加利福尼亚铜”(“California Bronze”)的缩写,但审查者聘用的语言学家认为该词在西语的普通词义是“公羊”,但作为俚语则有“混蛋”等诸多贬义,因而车牌仍被吊销。在整个美国,每年有上千个个性车牌因此申请失败或被“下岗”。
车牌问题,在美国尚是“内宣”。针对不同国家的跨文化“外宣”,更需慎之又慎。
更正固然是好事,但在使用前经深思熟虑而淘汰那些贬义选项,更值得提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英文简称,就是个正面例子。该论坛的全称是“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在使用其简称“Belt and Road Forum”时若再进一步简称为“BARF”或“Barf”,就会“躺枪”。这个简称等同vomit、puke等,是“呕吐”之意。实际上,英语随便一个包含3到4个字母的简称,都可能是几十个全称的缩略,还原后就容易出现贬义。“Belt and Road Forum”的简称“BRF”,可上溯到80多个全称,迄未发现有贬义。“BARF”的全称虽然只有30多个,却出现了例外。
三是向当地民众学习。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无论学习哪种外语,学得最快的永远是脏话。对于本地语而言,更是如此。实际上,这也是民众“防身”之需:总不至于被人骂了还在说“谢谢”吧。
汉语在转化过程中,当地民众一个诡异眼神和一丝坏笑,都暗示出现了“情况”。长安汽车参展时,就是看到当地人窃窃私语、掩口而笑才发现了问题所在。上文提到的智利圣地亚哥饭店名的“华丽转身”,也是饭店老板敏于观察并虚心向当地民众请教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当地民众”,实际上也包括长于斯乃至生于斯的华侨华人。他们长期接触中外文化,对于语言转换中的贬义格外敏感。美国华侨华人修改“谢南多厄”的译写,就是典型一例。在《美国地名手册》收录的约4万个地名中,带“厄”的地名有百余个,最有名的当属美国东部的“谢南多厄国家公园”(Shenandoah National Park)。但其中的“厄”字具有“灾难”“受困”等贬义,与“多”字相连更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正因如此,当地华侨华人委婉地改成了“仙那度”或“仙那多”,不仅将所有晦气一扫而光,而且还增加了几分仙风,也令人怀恋起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堪称文化落地的创新之笔。只是当地华侨华人数量太少,没有象“旧金山”那样取代“圣弗兰西斯科”成为当地译写的主流。需要说明的是,翻译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但在贬义面前,这一传统当让位于“回避贬义”原则。
四是向老牌跨国公司学习。老牌跨国公司,长期与不同文化打交道,曾经沧海,经验丰富。汽车中的奔驰、宝马、保时捷,饮料中的可口可乐和雪碧,连锁店中的家乐福等,不仅表述地道、易拼易读,而且朗朗上口、含义吉祥。如可口可乐,不仅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而创造出了32种口味,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人以愉悦享受。上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刚走进中国时曾被译为“蝌蝌啃蜡”。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这款味道和名字“双重古怪”的饮料销售情况可想而知。后来,该饮料公司登报重金悬赏征求译名,最终南京大学著名校友蒋彝教授脱颖而出,从而成就了广告界迄今公认译得最好的品牌。
译名这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其价值难以估量。为确保中国产品名称能与东道国的语言和文化习惯“愉快相处”,有必要学习可口可乐的经验做法,在当地进行测试或邀请当地顾问对名称的褒贬进行评估。一旦发现“自伤”,必须及时予以“救治”。
“救治”的方法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用发音接近的字代替。
长安汽车最初浑然不知,弄清原委后及时改为在葡语中没有贬义的“长安”(Changan),从而得以被巴西人欣然接受。当然,也可以彻底改头换面。中国在英语国家的多家带有“熊猫”和“龙”字的中餐馆,过去多年来都改成了与原名并没有多少联系的新名。“救治”还可以用回避矛盾的方式解决矛盾。如对于缺乏辨正思维的外国中小学生,上文提到的神话和寓言最好从课本中删去,以免其以点代面,对中国文化产生质疑和偏见。
对于那些反复出现的“自伤”,需要建立标准。在俄罗斯,带有“辉”“慧”等字的中国人名,都会在拼音第二个字母后额外增加一个字母,以冲淡原有“恶意”。目前,这已成为共识、常态和标配。
“祖训”也要与时具进。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要求“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这一传统并不绝对。严格意义上讲,问世只有60年的汉语拼音也是一种更改甚至是革命。古人采用的是一种双拼制注音法,即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如“缓,胡管切”等。在中国急速“走出去”的今天,含有贬义的姓氏拼写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如“李”姓华侨华人在美国一般更改为Lee。这一更名摆脱了原有的“撒谎”贬义,也接上了地气。Lee姓在美国名人辈出,“轻骑兵”亨利·李和罗伯特·李父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两位分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时期的英雄,都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
“王”在国外拼为Wong,“张”写成了Chang或Chiang……表面上看是沿用了1958年前中国采用的威氏拼音,是某种程度上的约定俗成,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避免“自伤”。
其实,姓名“落地”时一旦发现“自伤”,外国人同样会进行更改。1999年5月太平洋总部司令、海军上将普里厄(Joseph Prueher)被提名出任驻华大使,我国多家媒体在报道中也使用了这个姓氏。但在12月9日抵京走马上任当天,普吕厄就让发言人正式宣布更名为“普理赫”。更改的原因不言而喻:“厄”有贬义,与“普”相结合,更容易引起恶意联想。同样,格鲁吉亚语中的“酒司令”发音与汉语中的“国骂”毫无二致,当地人在与中国人碰杯换盏时也学会了回避。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近代翻译家严复的这句名言,慨叹的是翻译之难。而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考虑到入乡随俗、兼顾到当地文化,译介难度就更大。这是文化交流之大事,需要慎之又慎、精之又精。两种文化只有“愉快相处”,才能达到“民心相通”,实现从符号层面向价值层面的转变。